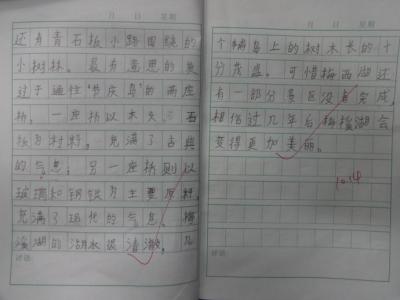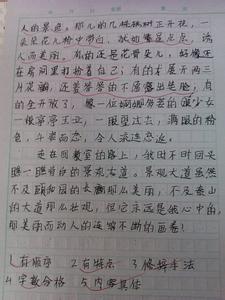你是地铁上的一个乘客。你在下午六点被散发着汗味和香水味的陌生人的身体挤压在车厢中央一个狭小的空隙里。你的两只手都够不到任何一只扶手吊环,于是你只好依靠双脚保持平衡。在你头顶上方空调正送出冷风,但你的后背却开始不断渗出汗珠。你的视线越过此起彼伏的头颅看见车窗外闪过一幅巨大的灯箱广告,画面上是一片宁静、碧蓝、似乎没有边际的海水。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这列地铁驶离此地,开往一处不知名的远方。它穿山越岭,走过许多陌生的城市。当车身终于停稳,你看见左侧的车窗里有一条平坦的海岸线,右侧的车门打开,海风扑面而来,你的眼前是一座几乎看不见人的海边小渔村。

你是渔村里的一位小学教员。你在一个宁静的午后坐在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吊扇的办公室里用双色铅笔批改学生的作业。你偶然抬头,发现办公室里现在只有你一个人。透过敞开的木窗你看见小操场上只有一个戴着草帽的校工正在阳光下弯着腰清除杂草。当你把目光投向更远处那条朦胧而闪烁的海平线,你忽然意识到那条海平线你已经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后面看了整整两年。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自己骑上自行车沿着校门口那条水泥路来到一公里外的海边,然后顶着腥味十足的海风登上一艘马达隆隆作响的机帆船。你站在船尾看着学校操场上的旗杆离你越来越远。当你越过那条海平线,你来到一座叫做纽约的城市。
你是纽约曼哈顿金融区一家连锁咖啡店里的服务员,但你的真正志向是成为一名作家。你在每周一晚上乘地铁去二十三街的一间酒吧坐在角落里听文学朗诵会,你在每周六的下午去东村第四街另一间文人出没的酒吧希望在那里碰到愿意阅读你小说手稿的出版商或者经纪人。现在,你正俯下身子手持一把笤帚清扫一位刚刚离去的顾客撒落在桌子下面的蛋糕屑,你身旁的座位上有三个身穿闪亮白衬衫的华尔街职员正在高声谈笑,他们谈到私人游艇、欧洲假期,还有意大利女人。你走到店门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你的手在另一只口袋里搜寻打火机时碰到了那封从昨晚开始一直塞在那里的寄自《纽约客》的退稿信。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自己拦住正从你眼前开过的那辆黄色计程车,告诉司机你要去肯尼迪机场。你在机场大厅掏出你那张还没有透支的信用卡,对柜台后面那个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女孩说你要去巴黎。
你是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区一位独居的老妇人。每天下午三点你穿戴整齐、略施淡妆,走出你那间位于六楼的小公寓。你手扶楼梯缓缓下楼,穿过静得出奇的小天井,推门来到阳光温暖的街上。你走过咖啡馆外面手持酒杯、面向大街翘腿而坐的优雅男女,走过门前聚集着外国游客的墙壁斑驳的老教堂,走过出售可丽饼和冰激凌的街边售货车,走过门脸不大的时装店和小画廊。你转入一条小街,推门走进 “不二价”超市。你手推购物车,在货架前认真地挑选蔬菜和奶酪,然后手提购物袋沿原路返回你的小公寓。在动手准备晚餐之前你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里看电视。你按动遥控器变换着频道,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你醒来的时候窗外和屋内都是一片昏黑,电视机里闪烁着微光。你看见屏幕上有三只大象和一只小象正晃动着鼻子缓慢而稳重地在草原上行走,在它们和远处的地平线之间只有一棵细长的小树,像一颗孤零零的钉子。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你五十年前的情人在门外按响你的门铃。你们带上红酒和水果坐上他那辆雪铁龙敞篷车,然后你们一路哼着约翰尼•哈里戴的歌开车去非洲。
你是南非首都开普敦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老板。每周二下午两点你会准时驾车离开你的酒店。你会沿着M6海滨公路一直向南开去,你的左边是散布着棕榈树和私人别墅的低矮的山岩,你的右侧是细浪拍打着岸边礁石的南大西洋。你会在十五分钟后抵达坎普斯海滩附近一家装潢别致的小旅馆。你会在那里停好车,直奔117房间。你会熟练地掏出门卡打开房门,然后你会在房间里看见一个躺在床上(有时是坐在椅子上)的裸体女人。你不能确定每次和你云雨的女人叫什么名字、芳龄几何,你不能确定你的朋友肖恩(这家旅馆的老板)是从哪里源源不断地为你弄来这么多小妞,你更不能确定那些肤色不同、身材各异的妙龄女子是否认得出你是开普敦那家著名酒店的老板(或许她们更加熟悉你那位身为国会议员、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老婆?)。但你从来不为这些不能确定的事耗费脑筋。现在,在一番剧烈运动之后,你习惯性地闭着眼睛仰面躺在床上,一只手懒懒地抚摸着身边那条褐色的长腿。这时你忽然听见开门的声音,这时你忽然闻到一种你熟悉的香水味道。你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声在尖声喊叫,你睁开眼睛,有几秒钟你竟然无法分清那张愤怒的脸此刻是出现在电视机里还是真的横在你的床头。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你根本没有开车驶上M6公路,根本没有停在这间旅馆门前,根本没有打开过这个房间的大门。你幻想你此时此刻正在一个离此地非常遥远的国家。于是你想到了印度。
你是印度德里旧城的一位街头流浪汉。你在一个圆月高悬的夜晚斜靠在路边的墙角左手夹着一支烟头右手握着一听罐装啤酒。你的头发和胡须粘连在一起,你从头到脚套着11件捡来的衬衫和5条捡来的裤子。你在每个白天弯着腰走街串巷仔细研究这座城市里每一只垃圾筒的内容,你在每个夜晚坐在你固定的角落里看着这座破旧的老城变得越来越安静。今晚你感到幸福,因为你刚刚在两条街以外的公共厕所里洗了一个凉水澡,因为你路过你朋友库什的角落时他扔给你一听还没有过期太久的灌装啤酒,也因为你听说抓乞丐的囚车已经从这条街上开走,至少今晚你不再需要担心被抓去坐上两年大牢。于是你感觉到一种放松,于是你哼起了小曲,于是你让自己的思绪飘散开去,于是你幻想去旅行。旅行,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但是此时此刻你实在想不出除了这个舒服的街角以外还有其它任何地方值得你挪动身躯。这时,你抬起头,看见了悬挂在街对面大楼顶上的那轮硕大无比的白色的月亮。你幻想去那里走上一趟。
你是人类历史上第十三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147个小时以前,你和另外三名宇航员乘坐“牛郎星”号登月舱平稳地降落在月球表面,你第一个走下扶梯,你的宇航靴激起的尘土像慢动作镜头一样缓缓地升起,又缓缓地落下。123个小时以前,你和你的同伴驾驶一辆月球车在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颠簸着前进,你意识到登月24小时以来你看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头顶上方永远是漆黑一片的无尽苍穹,脚下永远是像在海底世界一样沉睡着的尘土和碎石。84个小时以前,你躺在登月舱里的吊床上做梦,你梦见了你家门口A&P超市货架上那些颜色鲜红的番茄。47个小时以前,你在一座低矮的山坡上滑了一跤,尘土和石屑如丝巾一般飞舞,当你终于像从游泳池底爬起一样重新站直了身子,你又看到了低低地悬挂在黑色天幕上的那个只露出半个脸庞的蓝色的星球。24小时之前,你收到休斯顿总部的通知:停留在近月轨道上的“猎户”号指令舱出现电脑故障,总部的工程师正在全力远程抢修。5分钟之前,你收到最新通知:指令舱彻底瘫痪,无法按原计划在23小时之后完成与登月舱的对接。1分钟以前,你的助手罗斯通过对讲机告诉你:休斯顿将紧急发射一架小型火箭为你们提供补给,但登月舱上的氧气储备仅够维持31个小时。现在,你站在月球表面,手里握着一块矿石标本,身体一动不动。你忽然感觉这里如此荒芜、如此死静,如此丑陋不堪。你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回到远处那个蓝色星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你不在乎风景,你只想把自己包围在人群之中,让自己可以闻到人的味道。毫无缘由地,你想到了一列拥挤的地铁。
你是地铁上的一个乘客。你在下午六点被散发着汗味和香水味的陌生人的身体挤压在车厢中央一个狭小的空隙里。你的两只手都够不到任何一只扶手吊环,于是你只好依靠双脚保持平衡。在你头顶上方空调正送出冷风,但你的后背却开始不断渗出汗珠。你的视线越过此起彼伏的头颅看见车窗外闪过一幅巨大的灯箱广告,画面上是一片宁静、碧蓝、似乎没有边际的海水。
于是你幻想去旅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