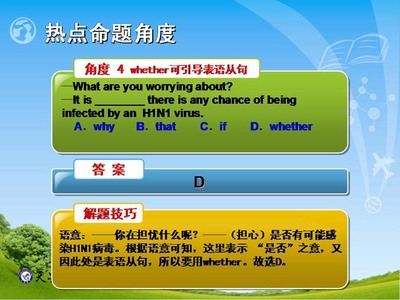——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一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从现在退回去大约四十年,也就是20世纪的6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那时候一方面是物质极度贫乏,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另一方面却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热情,饥饿的人民勒紧腰带跟着**进行共产主义实验。那时候我们虽然饿得半死,但我们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之中。而我们这些饿得半死的人还肩负着把你们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神圣责任。当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对外敞开了大门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在我的童年时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照相这码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据后来看到过的一些历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忆,来想象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担保我想象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那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烂程度是今天的中国孩子想象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她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没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人在险恶的环境里,也许会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不能适应的都死掉了,能够活过来的,就是优良的品种。所以,我大概也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那时候我们都有惊人的抗寒能力,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时,我们光着屁股,也没有感到冷得受不了。我对当时的我充满了敬佩之情,那时我真的不简单,比现在的我优秀许多倍。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我的一个小伙伴后来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那时我的牙齿也很好,但不如我那个当了电工的朋友的牙齿好,否则我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电工而不是一个作家。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阻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至于煤块吃到肚子里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里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不要以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那时候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两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百斤粮食,再加上到田野里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愈来愈少了。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当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开始回忆我童年时的孤独,就像面对着满桌子美食回忆饥饿一样。我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洼地里放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里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是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树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对我的父亲说:“他爹,咱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后来我长大了一些,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进入了**社会,我在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母亲痛苦地劝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我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发誓再也不说话,但一到了人前,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话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作家生涯时,我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亲经常骂我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欢说话的毛病。为此我把文坛上的许多人都得罪了,因为我最喜欢说的是真话。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梦想是很早就发生了的,那时候,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被打成**、开除学籍、下放回家的学生。我与他在一起劳动,起初他还忘不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大学生,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但是严酷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很快就把他那点知识分子的酸气改造得干干净净,他变成了一个与我一样的农民。在劳动的间隙里,我们饥肠辘辘,胃里泛着酸水。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谈论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者是听说过的美食讲出来让大家享受,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我开始创作时,的确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动机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许多中国作家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灵魂工程师”,更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改造社会。前边我已经说过,我创作的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于美食的渴望。当然在我成了名之后,我也学着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那些话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中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鸟叫什么调,什么作家写什么作品。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当然,随着我的肚子渐渐吃饱,我的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创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历史,也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我记得我最早的作品是写一篇挖河的小说,写一个民兵连长早晨起来,站在我们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祷,祝愿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那人就起身去村里开会,决定要他带队到外边去挖一条很大的河流。他的女朋友为了支持他去挖河,决定将婚期往后推迟三年。而一个老地主听说了这个消息,深夜里潜进生产队的饲养室,用铁锹把一匹即将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车的黑骡子的腿给铲断了。这就是阶级斗争,而且非常激烈。大家都如临大敌,纷纷动员起来,与阶级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来了。这样的故事今天是没人要的,但当时中国的文坛上全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这样写,就不可能发表。尽管我这样写了,也还是没有发表。因为我写得还不够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们的毛主席死了,中国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文学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变化是微弱而缓慢的,当时还有许多禁区,譬如不许写爱情,不许写**的错误,但文学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压抑不住的,作家们挖空心思,转弯抹角地想突破禁区。这个时期就是中国的伤痕文学。我是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那时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的禁区几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许多作家都介绍了过来,大家都在近乎发疯地模仿他们。我是一个躺在草地上长大的孩子,没上几天学,文学的理论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我凭着直感认识到,我不能学那些正在文坛上走红的人的样子,把西方作家的东西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我认为那是二流货色,成不了大气候。我想我必须写出属于我自己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不但跟外国的作家不一样,而且跟中国的作家也不一样。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恰恰相反,我是一个深受外国作家影响并且敢于坦率地承认自己受了外国作家影响的中国作家,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作为一个专门的题目来讲。但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上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投机,有可能成为终生伴侣,如果话不投机,然后就各奔前程。
截至目前,在美国已经出版了我三本书,一本是《红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还有一本就是刚刚面世的《酒国》。《红高粱家族》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官僚的痛恨。这三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www.aIhUaU.com爱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