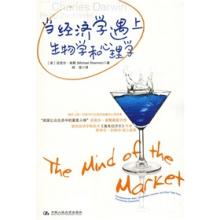新交的男朋友黄正宇手提着三个大袋子向我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我张大了嘴巴:你你你干什么?他说开门,我给你置办了点年货。我惊讶地打开超市的袋子,全是什么糖心莲子、猫耳朵、核桃糖、水果果冻,真是哭笑不得,把我当作小朋友了。但一瞬间又感动起来,就是这些最俗世的体验,成了最能够把一颗在尘世里颠沛流离的心安抚妥帖的事情。我决定以后还是在岭南定居,因为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这里的人都要天天饮早茶,享受着人间触手可及的清福——喝茶、听粤剧、逛花市等。可是当年,我却喜欢欧洲的西点,喜欢涂抹很多奶油,而后涂抹到谭的脸和身上……
从未那么长时间注视一个男人
第一次坐长途飞机,就被左右两个大胖男给裹挟着,我苦不堪言地跑到商务舱向空姐求救,英文不好,正在为说得不清楚而着急,一个30来岁的男人站起来,问了我几句话,就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在接下来的10个小时里,从来没有一个男子像他那样,被我用心注视了那么久,他醒了后,眼角余光看到我睁着眼,就对着我笑笑。我当时有如喝醉了酒,脸红耳赤,甚至在倒时差的时候,无论睁开眼还是闭上眼,都能想起他的容颜。
谭是长得很好的,我承认自己是外貌协会人士。后来,当我在巴黎艰苦地学习法语,艰难地在街头推广自己的作品时,熟悉的身影从旁边走过,我知道那是谭,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可是,他没认出我来。那时,一个是浊世佳公子,一个是落魄艺术者,这两种人能有什么交集呢,就像我身边那些欧洲贵族的 “贵二代”,他们的生活就是私人飞机、帆船、度假、party以及名画拍卖。我的生活可是实打实的一日三餐以及随时担心被房东加价。后来,我在海外论坛上遇到了tan,由于一个小小的话题,聊得很投机,基本就是半柏拉图的地步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快要被那个充满幽默感的男人给搞疯了。我们有时差,我要上课,他要上班,每天能说话的时间都很短。于是我每天拍照片给他,并且希望彼此能赶紧见面,因为我不满足他在论坛上朦胧的侧面照片。
一度以为可以“不辞长作岭南人”
见到谭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tan就是谭,而谭则是那个在飞机上帮助过我的男人。被蒙在鼓里的我真是“新仇旧恨”都涌上心头,可是,他压根想不起来我是谁。那好吧,我就带着自己的小秘密去喜欢他。
谭很讲究,他的衬衣领口永远是很干净的,他的手指甲也永远修理得干净清爽。每次吃饭,他带去的地方都很奇特,不是在江边的小咖啡屋,就是在山边的粤菜馆,再或者是深山里的度假村。在纯白色带着暗纹织锦的床上,他喜欢让我坐在他身上,两手从我的上臂慢慢划下来,有时从胸脯外侧一路滑过腰线到臀围,嘴里不住叹息。我用鼻音问他“嗯”,他答“好美的线条”。我暗自喜乐,在假期随他回广州,一住就是三个月,那段时间我最爱说:“不辞长作岭南人。”
岭南没有鲜明的一年四季,雨水充足,阳光明媚,草木茂盛,把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滋润得相当顺滑。谭的妈妈和周围的人都一样,特别关心胃口,没有那么多的声色俱厉,要的就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满足,例如每周日的饮茶。一到周日,早上见面,往往以“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