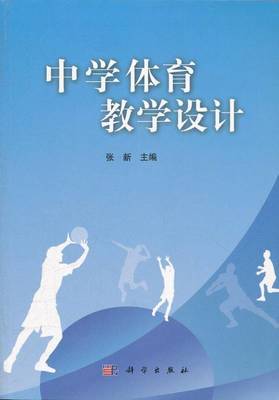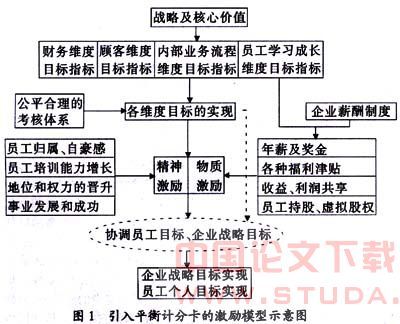一、接纳世界为什么以诚为基础
如前所述,君子之道的展开,也就是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上下通达)寓诸“庸”(发而为用、展现在世界之中)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庸之道表现为世界的接纳或天下的打开,从而使世界或天下得以作为一个命、性、道、教之间相互通达的“文-化”的境域而呈现出来。而给出世界的过程,也就是成己、成人与成物之相互通达的过程:在成己之际成人与成物。而己、人与物相互指引、彼此缘发之时,恰恰是世界的到来之际。所以,当下之给出世界,或与出世界,也就是,在当下之行为中成己、成人、成物。
当然,所谓“成”是指“成性”,“成”相对于“生”而言,是在生的基础上的成就。就天地之间的一切存在者之“性”的构成而言,它包含着“生”、“养”、 “成”三个维度,“生”是天的事情,而人物无与其功,“养”是由厚德载物的大地来承担的,但“成”却是人的事业,因而有所谓“天生”、“地养”、“人成” 之说: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
一切事物(包括人)之养育之功悉应归于大地,而其生均出于天而不系于人,其成则系于人而不出于天。如此,天、地、人始可谓之“三本”。在这个意义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表述的就是性的事业。就天地而言,我们可以说,“生之谓性”;但就人而论,则是“成之者性也”。成性的事业,与天地之生养,乃是一接续承继的过程,所成之性恰恰是天地所生、所养之性。天生我你为人,就此生性而言,我你之性均为人性;但就成性而言,我你是否人性,则并非已经预先决定与现成,而应由当下之行动对天地所生养之性的回答、回应来断定。同样,事物之性固由天地所生所养,但只有通过人成,它才得以纳入天地之间, 纳入作为存在者居所的世界,离开人的存在,北极熊与南极企鹅、夏虫与冰等根本就不能进入同一个世界,作为同一个世界的不同存在者而存在。
人之性、物之性与己之性,在我当下的行动中得以一同带出,得以一同显现,有其条件。这就是“诚”: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自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诚是当下地成己之性、成人之性、成物之性的条件,因而也是当下地给出世界的条件。这同时意味着,在诚中,发生的不再是如同在“素隐行怪”者那里存在着的成己、成人与成物的分离,恰恰相反,在诚中,己、人、物共属一体,这个一体性的维度就是世界。不仅如此,在诚中,智与仁的分离也得以克服,二者不再处于各自为政、相互拒绝的状态中。相反,盛德之至,上德不德,智之用事之时,仁也自行显示在智中;仁之用事之时,智也自行显示在仁中——二者虽然各自用事,然彼此浑溶无间,相互通达,一之于诚。换言之,当诚到来之时,智与仁的分别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正是成物之智与成己之仁以及成己、成人、成物的对立在诚中克服,所以,是诚给出了世界,也是诚使得人可以成为与天、地并立的三本之一,也就是说,不是其它,而是诚,才真正提供了人与天地相参的根本条件。
这样,就不难理解胡宏《知言》中如下的陈述:
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
成天下之性、立天下之有,也就是在当下与出万有、开通天下,此皆维系于诚。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中庸》对于人道的那种理解:“诚之者人之道也。”周敦颐在其《通书•诚下》中将此意转述为“诚则无事矣”,这意味着,除了“诚之”之外,打开人道的一切作为,还能有什么呢?无他,唯有“诚之”而已,只有在 “诚之”的过程中,才能打开人性自身,从而进一步地打开世界、接纳世界;而“诚之”本身就是人通向人自身的道路、人将自身提升到人性水平上的唯一方式,也是打开天道之诚的方式。这同时意味着,人的一切作为,只要不是围绕着诚而建立自身,那么,它就不可能打开人道与天道。诚虽系性之德,却可通达天下,因而,建基于诚的中庸,自然也就是“合内外之道”。
诚以成(己、人、物)性为其鹄的,而人之以诚成(己、人、物)性,又是继天地生养之性的过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换言之,成性(人通过修道所打开之性)其实又可以看作生性(天命之性)的自行开显。与此相应,人通过诚所给出的世界,人通过成己-成人-成物所给出的世界,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基于意志与欲望而建造的世界,不是任何形式的创世,而是世界之自行给出。尽管我们可以说作为“在世者”的人打开了世界,可以说世界唯有对人才得以敞开自身,也可以说各正性命的万物唯有通过人的在世才得以进入作为相互指引境域总体的世界,但人却无论如何都不是世界的制造或创造者,世界有其自身的存在。

正如卡尔•勒维特所说的那样,“世界不是一个单纯宇宙‘观念’(康德),一个唯一‘全景’(胡塞尔),一个世界‘筹划’(海德格尔),世界是它自身,是绝对独立的它自身,一个完全的实在。只有各种世界图画才能被筹划,世界本身绝不可能被筹划……(世界)本身绝不呈现为像其它客体那样的一个客体;它包围着每一事物,它深不可测。它是最伟大、最丰富的,同时,就像一个没有图画的画框一样,它是空洞的。” 世界的秩序不是取决于人的关切和恳求,在山是山、水是水、天空是天空、大地是大地的世界秩序中,世界本身表现为一种因超离了基于人的那种目的性关切而抵达的了无挂碍、空空或如如。这样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人的作品,毋宁可以视为来自天命的馈赠,换言之,它应该被作为礼物来接纳。而对于个人而言,他的生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而展开本身,就已经是在接纳这一礼物。生命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作为生命而展开自身呢?这其实也是在追问,在什么意义上,世界才能作为礼物而得以进入我们的生命?从馈赠或礼物的角度思考世界,这意味着,世界不是我们的附属物品,不是人类生产自身的目的、意志与欲望所使用的材料。人不能占有世界,但却无法离开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又是被抛的天命,无论我们接纳还是拒绝,世界都在抵达我们的存在。“物理世界可以不以人的存在作为参照物被思考,而人却不能离开世界被思考。我们来到世上,我们又离世而去。世界不属于我们;相反,我们却属于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应发现、打开、接纳世界,而不应占有、生产、创造世界。而对世界的真正接纳,要求世界作为天命馈赠之礼物而被打开,因而,与创造世界的那种生产劳动的主体不同,接纳世界的那种存在者,在打开世界时,也将其人生展开为礼乐的生活,而诚作为接纳世界的德性,也正是礼乐生活的德性。通过“诚之”的德性,人在其成己-成人-成物中给出世界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给出一个文化境域,在这个境域中,命、性、道、教相互通达,而诚正是命、性、道、教得以相互通达的条件。
曰“命”、曰“性”、曰“道”、曰“教”,无不受统于此一“诚”字。与此不察,其引人入迷津者不小。
由于命、性、道、教之间得以相互通达,因而,由诚而打开的人文境域同时也是天文的接续形式,是天命的人文,或通达天命的人文。在这里,文化本身成了天地生养万物的宇宙事业的一种推进,是对展开在天地之间的那个被命名为“自然”的流行着的天道过程的一种接收。 由此,人的“诚之”活动才是天道、地道与人道在人那里得以打开的方式。这样,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中庸》的那个著名的论题:“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二、“天道之诚”总是向着“诚之”者与“思诚”者开放
对于这句话,人们通常如是而理解,“诚”是天的存在方式,而以自觉地追求“诚”为目的的“诚之”,则是人的存在方式。这种流俗的理解,不仅将人道视为天道下贯、落实或分殊到人那里而形成的结果,而且,将诚的本源、本性在实质上分配给可以先行于人道而得以展开自身的天道,例如所谓的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这样, “诚之”的活动,就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对天道已然之诚的摹仿,而不是人的一种具有“原-始”意义上的存在方式;而且,在这种理解中,人的存在方式被限定在 “诚之”中,而被否定了进升到“诚”与“至诚”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中庸》中不仅一再出现,而且成为中庸之道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要求。因而,这种理解,不再是打开中庸、接纳中庸的方式,却构成了以某些现代的观念意识拒绝中庸的方式。
那么,“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获得真实的理解呢?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诚”在什么意义上才成为问题?或者,“诚”得以向我们显现的条件是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天道与人道在其对我们的显现中,孰者具有先行展现自身的优先性?而且,天道与人道的区分是在什么条件下确立的?又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这一区分本身的意义将会退隐?
自在的自然乃是向着文化世界中的生命显现的,身处自然之中的花草树木并不能发现在它们身上展现着自身的自然,同样,天道之诚在最为本质的意义上乃是对人敞开的,自在的世界并没有诚或不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诚者天之道”所表述的,乃是对人而言的天道(在人之天道),而不是脱离了人的存在而言的天道之本然(在天之天道)。对此,南宋学者陈淳与明代王夫之都有深刻的论述:
天道人道有数样分别。且以天道言之,“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贞而复元,循环不息,万古常然,无一息之闲,此皆理之真实处如此,即“诚者,天之道”。《章句》所谓“本然”者是也。以人道相对言之,“诚之”乃人分上事。天道流行,赋于人,而人受以为性,此天命之本然者,即诚也;人得天命之本然,无非真实,如孩提知爱,及长知敬,皆不思不学而能,此即在人之天道也。及其做工夫处,则尽己之忠,以实之信,凡求以尽其实者,即“诚之者,人之道”。章句所谓“当然” 者是也。又自圣贤论之,圣人生知安行,纯是天理,本末皆实,无一毫之妄,不待思勉,而自然中道,此亦天之道也。自大贤以上言之,气禀不能纯乎清明,道理未能浑然真实,故知有不实,则必择善;行有不实,则必固执。须是二者并进,乃能至于诚,此则所谓人之道也。自二十章以下,皆用此意分天道、人道而言也。前此十六章“诚之不可掩”是以天道言诚,上文“诚身”是以人道言诚。此则兼二者而并言之。“诚者”、“诚之者”,二“者”字正与“也”字,相应下二者,是指人说,当重看诚者,以成德言。故先不勉,而后不思即安行之仁、生知之知也。从容中道一句,是自然之勇,诚之者以进德之序言,故先择善而后固执,即学知之知,利行之仁,而勇在其中。此前皆言知仁勇,学者入德之事,此下兼言仁知勇,圣人成德之事。如下章尽性仁也,前知知也,无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载仁也,如天之覆帱知也,如日月代明四时错行勇也,却自此不勉不思始焉。
在天之德无有不诚,则不可谓天为诚。诚原与不诚相对,在人始可名之曰诚。
天地之道,可以在人之诚配,而天地则无不诚,而不可以诚言也。(自注:云“诚者天之道”,以在人之天言耳。)
由于天(自然)本无所谓不诚,因而,也无所谓诚。诚与不诚相对而言,可以“诚”来言说的存在者,同时也是可以“不诚”来言说的存在者,唯其如此,“诚”本身才不是一个已经存在或将要抵达的现成化结果或目标,而是一个开放着的过程本身。如此一来,可以述说“诚”的那种存在者,就是那个可以打开“诚”的存在者,也就是能够“诚之”、同样也可以“不诚”的存在者。事实上,只有人这种存在者才有“不诚”的可能性,但也只有它才有自觉的“诚之”的可能性,“诚之”的可能性永远伴随着“不诚”,如同“不诚”的可能性也始终伴随着“诚之”那样,不待“诚之”来打开的“诚”从来就没有发生,一旦抵达了“诚”由此而可从此摆脱 “不诚”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没有“不诚”,“诚之”的意义就无法安顿;同样,没有“诚之”与“不诚”,也就不能打开、照亮“诚”自身。在这个意义上, “不诚”、“诚”与“诚之”等等,勾勒了一种存在者的可能性,这种存在者在与诚的关联中,也就是在“诚之”、“诚”、“不诚”三者之间的张力中开启自身的存在,而“诚”也唯有通过这种存在者才得以打开自身。
由此,唯有对人这种存在者而言,天道才得以将其本性显现为诚,因而,在这一显现中,已经深深地镂刻着人的踪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天道之诚”就是人的“诚之”活动的一个结果,“天道之诚”就可以归结为人的“诚之”,或者说,人的“诚之”对于“天道之诚”就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不是的!人的“诚之”虽然可以在自身中打开“天道之诚”,但“天道之诚”并不因而就是“诚之”的作品,相反,“诚之”活动本身却又未尝不在始终受到“天道之诚”的指引,尽管指引着“诚之”活动的“天道之诚”一开始也许是“不言之诚”,尚没有被“诚之”者看作“诚”。当然,对生命而言,“天道之诚”对“诚之”的指引,也不是现成的,它开放在有准备的、倾听天道的生命之中。随着论述的展开,我们还将看到,“诚之”与“诚”标明了生命存在的两种不同的阶段与状态。随着“诚之”者的德进,“诚之”到“诚”的过渡也就得以可能,而在那个时候,“诚者天之道”述说的就不是生命之外的大自然,而恰恰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在那个时候,人的“诚之”本身就是“诚之自明”。
《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而不说“诚之者天之道”,这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的“诚之”的活动恰恰也是拒绝“天道之诚”(它表现在生命深处的天性之诚)的方式。例如,当一个社会或个人真诚地去掩饰内心的真诚的时候,诚之本身就表现在追求虚伪的那种真诚的方式中。尽管人们知道这种“诚之”恰恰是“不诚”的,但却真诚地去伪装自己,真诚地给自己戴上面具,真诚地去不诚,从而远离了天性之诚。一旦这样的“诚之”成了一个文化的过程,成了一种社会的风尚,那么,不能掩饰那种天性之诚,就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文明、没有长大成熟的表现。在这样的文化形式中,所谓的教育就是引导人们如何掩饰自己的真诚,并将这种掩饰提升到没有任何掩饰的程度。在这样的文化中,人文高度异化,与天文相互分离,道、教与命、性之间相互隔阂,不能相通,而生命也因此处在由于内外的不通而导致的分裂之中,不能自由地舒展自身。不仅如此,人们必伪装起来,隐藏起来,才能保全自身。王夫之在王莽那个时代发现了这种拒绝“天道之诚”的“诚之”,一种不再“伪以迹”而是“伪以诚”的“诚之”:http://www.aIhUaU.com/
呜呼!伪以迹,而公论自伸于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于是而天理、民彝澌灭矣。
那样一种与天道之诚相互脱离的“诚之”,恰恰是对那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诚”的压制,一旦这种压制占了上风,那么,我们就处在“天下无道”的状况中,而且,这个时代作为一种现象而发生的“文-化”,就不再向着命、性、道、教的相互通达而开放自身,而是在四者之间的阻隔与间距中确立自己。这样的文化在实质上是无“文”之“饰”,一种将人性装在其中的“套子”,一种将真实的面孔隐藏起来的“面具”。在这样的时代,赤裸裸的真诚总是让人恐惧、颤栗,真诚要想持续下去,必须藉此极端虚伪的风习,从中打开一条缝隙。为此,那些在骨子里真诚的人们,就会给人以虚伪的感觉,因为内容上的真诚必须藉着形式上的虚伪才能持续下去。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下,需要的不是“方以智”,而是“圆而神”的智慧,因而真诚也向他人表达自己、真诚地面向他人也就特别地困难。
只有当“诚之”进升至“思诚”的层次时,这种“伪以诚”的存在状况才会在“诚之”者那里瓦解。换言之,在“伪以诚”的存在境况中,返回到“诚”的可能性的途径,维系在“思诚”上。我们可以比较以下的两个不同的论述: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
显然,“诚之”是一个更具有涵盖性的表述,一切意义上的对“诚”的自觉追求本身,都是“诚之”,在这个意义上,“思诚”也是“诚之”的一种可能方式。然而,“诚之”却不能为“思诚”所涵盖,“思诚”业已将“诚之”的可能性限定在“思”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