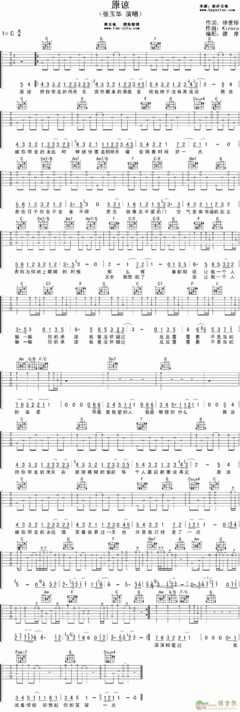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得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它那瘦骨嶙嶙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漩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暗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了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的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撇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约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指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约纳在赶车的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着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约纳抖动缰绳,吧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约纳的后脑壳喷气。
“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约纳笑着说,“凑合着戴吧……”
“喂,你少废话,赶车!莫非你要照这样走一路?是吗?要给你一个脖儿拐吗?……”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说。“昨天在杜克玛索夫家里,我跟瓦斯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说呢?”另一个高个子愤愤地说,“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
“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说的是实情……”
“要说这是实情,那么,虱子能咳嗽也是实情了。”
“嘻嘻!”约纳笑道。“这些老爷真快活!”
“呸,见你的鬼!……”驼子愤慨地说。“你到底赶不赶车,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车?你抽它一鞭子!唷,魔鬼!唷!使劲抽它!”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直骂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听见没有,老龙?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