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没有节奏的鸣笛声向冷清的站台袭来,匆匆的行人踏着整齐的步伐朝着各自的方向走去,人群在沸腾的喧闹声中画出了他迷茫的心。他被人海涌起的波浪推向现实的彼岸,成为了一朵枯黄的浪花。他卷起裤管,走进最深的寂寞,撕下潮水嘲笑他时的麻木表情。他在见到地上到处都是那个轻浮的笑意时,他更加愤怒了,失去理智的他把生活一口吞到嘴里,用已经被五谷杂粮磨钝的牙齿不停地咀嚼着。当他的牙齿被生活溢出的水汁染黄时,他脸上的肌肉已经累的筋疲力尽。他停止了乏味的咀嚼,端起时间,喝了一口死水,然后把没有嚼碎的生活连着它现实的欲望吐了出来。他的嘴里只剩下苦酒的酸味,红润的舌头完全失去了知觉,不能自由的舒展。他想说话,可是那些嘴里的话语却卡在了狭窄的咽喉,堵住了他通向这个世界的唯一通道。他衰老的意识驱赶着它的舌头,鞭笞舌头上早已失去知觉的唾液,唾液在受到外来力量侵入之前,就点燃了自己心中的那盏枯灯,焚烧着自己脆弱的身躯。他感到无助,被卡住的咽喉不能把体外污浊的空气传送给肺。他渐渐失望,开始放弃了自己。就在他准备永远闭上眼的那刻,她温柔的吻印上了他的嘴唇,一丝丝空气像把利剑一样划开了那些坚如磐石的话语。他感觉到她的温柔像清澈的溪水一样涓涓的流在他的经脉里,感觉到唇的温度像一声声深情地呼唤声一样唤醒了他沉睡的爱。他知道,她就是他一直等待爱的那个人。
她搂着他的腰,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路旁的风景礼貌的为他们的爱而让路。车到中途,吱呀声戛然而止,仿佛是命运故意的安排。她嘟着小嘴不情愿的跳下,他勾着她像座小山的鼻梁。他移开手后,他的手上还沾着她脸上胭脂的残香。他把那根手指放在鼻子前一嗅,情不自禁的打了几个喷嚏。他忘了他对香味过敏,他的鼻子只能做一个不能沾荤的和尚。他把那根手指握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一丝丝凉意从手心传来,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冷,需要厚厚的棉袄来抵挡潜藏在春天里的寒冷。他转身,正准备用自己的寒冷为她编织一个冷笑话时,她的身影消失在一辆高级轿车里。他对着轿车消失的方向望去,他看到她的鼻梁是那么高,他的手指攀不上。他想,是那鼻梁上缭绕的寒烟遮住了她俊俏的脸庞,还是那个与他手指长度成反比的海拔欺骗了他的真情。对她,他是如此的用心,无微不至。他小心翼翼的把她捧在手里,可是她还是从他的指间滑落,摔在现实的钢筋混泥土上,碎为他不愿看见的现实。他告诉自己,她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她和另一个男人开始了爱情。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就这样在他的爱情阵地上撤退,只留下他一个人用鲜艳的血液守卫他和她连个人的爱情。如今,两个人的寂寞,他独自承受。他安慰自己,她只是搭着那辆车回家找人来帮他,那个开车的司机是她的朋友。他相信,她还会乘着那辆车,再次坐上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可是自行车的轮胎破了,那个细小的孔需要具有粘性的物质来填补。他再次想起了她那像座小山的鼻梁,他拄着那根勾过鼻梁的手指,艰难地攀爬在陡峭的绝壁上。他听见山上有石块沙沙的滑落声,他抬起头,脸上的汗珠被他身上的疲惫串成了一串,有次序的坠落在没有退路的石壁上。当他快爬上山的最高处时,他看见她开着那辆高级轿车,载着他失落的爱,向山下驶去。他的心在刹那间碎裂,伴着他的心痛,他坠下了深不见底的深渊。被摔得体无完肤,他艰难的抬起头,看到自己正站在山的最高处,等待她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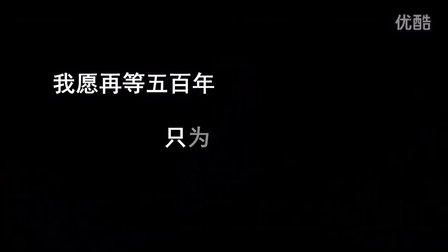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