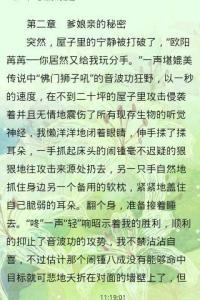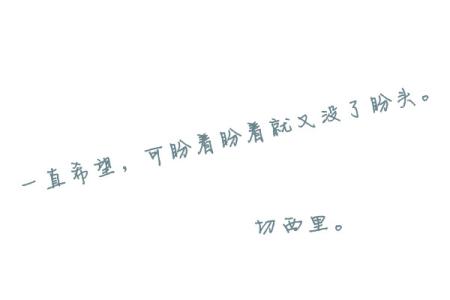天气已经变化,我的装扮也已经不再流行。
一阵冬风常常会带起一阵悱恻缠绵的细雨,落叶常常无端昏睡在发黑的土地上。
不是哀怨,那天边的色彩多年前曾经灿烂,它们迎来送往,全是金属的贵重与金黄;不是蜿蜒,昨日一颗流星坠地,惊醒了一帘幽梦,心绪无边,思念的人至今下落不明。
眼前的风景,不再容留视线。心,是那垛墙,厚重地立在冰寒料峭的码头。那条红艳艳的围巾,一直不记得随行李带走,风雪中的身影,一直孤单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天上常变幻出一些流动的感伤,脚底的荒原似乎也宽阔得望不到边。我数着童年时习惯的游戏在大地上游荡,看身后留下脚印,留下过往,也留下那些该记或该忘的前世今生。
也许并无目的,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开荒种地,与自己喜欢的人喜结良缘,然后在清闲的时候,认真地看着对方,等时间或空间慢慢将我们从青春带向暮年。
土地滋养鲜活的草,盛开美丽的花,也繁殖多愁善感的梦。在梦里,我经常能看见勇敢的少年,手拿皮鞭,放牧肥硕的牛羊,用笛声呼唤晚霞和黎明。
在风和日丽的早春,当地平线出现粉红的彩霞,我会留守在候鸟停留的海湾,目送过往的生命远航,然后独自遥望灯塔,看不时变幻的灯光,如何充实大海和天空。

在温暖湿润的雨后,当我的灵魂终于还原了干净的颜色,我会认认真真地大哭一场,表示我对重生的感动。
我曾在这里活动,我留给天空和大地的纪念都已发黄。我或许会永久地驻守在这里,用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容颜。
这个世界,我曾经来过;这个世界至今仍人来人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