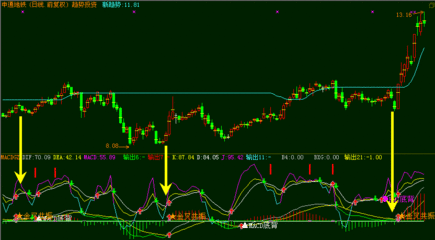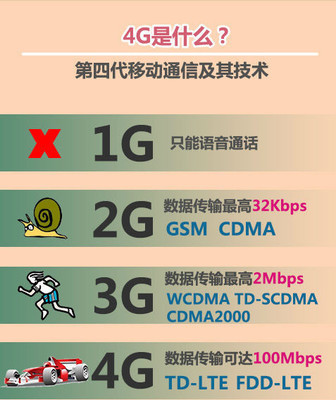简单的咒语。
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比如她。
如果还有交集,是凭着多年前挤过同一个被窝的情谊。初来乍到,第一个给予我帮助的她。离家住校,第一个陪我数星星的她。朋友渐多,第一个因我有了新朋友吃醋的她。生日将近,第一个为我精心制作礼物的她。成长始端,第一个告诉我女孩子是哪般破茧成蝶的她。生病休学,第一个让我寝食难安的她。病愈返校,第一个被我倾力照顾的她。那些清凉幼稚的还不知何为少女心事的小年纪里,是一起蓄长发的她,是一起爱上一本小说的她,是之前同寝之后同铺的她,是吃过同一碗饭的她,是一块饼干也要掰成两半共享的她,是周末以外一定形影不离的她。于彼此,是唯一亲爱的她的她。
时光究竟有哪一般摄于人心直至魂魄不整的力量,我的她,她的我,在如今已忆不出颜色的因素里分开后背道,伸手牵到新的她,用旧日里只对彼此展露的甜蜜笑容吐露的芬芳话语流露的秘密心事这样的可口甜点来招待。一丝不苟地复制上一集的一丝不苟在对方生活里刻下好看的姓名和唯两人可用的昵称。她们欢,她们悲,她们成长;我们笑,我们伤,我们也变得不怎么与从前一样。是色彩渐变的协奏曲,对于另一半的熟习和留存的联系从浓墨到淡妆,渐至毫不相干。
是写得大大方方的毫不相干。她状态里呈指数增长的陌生姓名,我号码簿里满满当当这一生与他不会有关联的朋友同学。那日,得知她将从她大学在的城市拜访老同学,只有一刹那心思动起,是否该告诉她,我也愿意陪陪她,仅是一刹那而已,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用最饱满的状态提醒我——与我无关——三两年里未曾联系的我怎么有资格成为她专程奔赴的目的地之一。
或者也该为表现某一种形式的礼貌,觉得到底问一问她这一路可否安好吧,翻一遍手机里的联系人,才想起不曾要过她的号码,原来已经陌生到这种不算普通朋友的地步。后来看她人人状态这一天的频繁更新,仿佛是浏览某个朋友的朋友淅沥不止的新鲜事。或许她在启程前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思想争斗,或许她的脑海中摩肩接踵的人群信息里根本打捞不到与我相关的只语片字。
终不似战火年代同出生共入死的共振频率的感情,无论相隔多么遥远,无论间隔中有多么疏于联系,无论疏于联系的岁月有多么漫长,无论再相见时各方有哪些变化让人措手不及,情谊入木三分,凝于血,伴于呼吸,困顿岁月的家常话在今日既是美好的童话伟大的神话。

然后,我们,庸俗却大力的交叉线。
如果时光愿意片刻手下留丁点儿情,便是老去的后来相互不遗忘第一面的音容笑貌。这是最好的结局。
比如他。
确定无法再继续任何对话,一个字两个词。
即使来时的路上有过怎样深情的对望,一个深夜两三个月。
新奇的心,懦弱的心,憧憬的心,任性的心。新生的世界尚未拓宽,进化的史诗仅拥有一顶帽子似的标题,处处荒凉静寂。流浪的一颗心靠近一点儿类似绿色便执意认作是上帝赐予了甘泉使大地在眨眼间翻天覆地。
一件白衬衫站在故事的开头。是在千回百转的梦里始终一尘不染的白色衬衫,是在谦和温良的某一人身上巧笑倩兮的白色衬衫,英挺轮廓,和气回声。开场的背景是未起露的秋夜,有流动在三年半前的黑得同样发着亮的夏夜的会说悄悄话的轻风。有谁可以拒绝认为那不是念念不忘的那年那天的平移变换,不过是沿着时间轴将一个图形富有预谋的平移变换。尽管渠未成,可庆水已到。正逢茶未凉,刚好人尚在。
霸道入侵的温暖挟持我启程。路线不定,结束语却在启幕之前。
连贯动作,点滴不落。知道我天冷手便凉的他,知道我偏爱红豆双皮奶的他,知道我天黑胆小的他,知道我何样情景心软的他,知道我厌恶烟味儿的他,知道我孩子样傻气的他。最是放心不下我的孩子样傻气的他。这样一个他。
这样一个他。形容清脆。
这样一个我。幻觉砌堆。
尚未成形的关系体谅不了晚秋的清冷,一旦成形的关系享受不到阳光的润泽。
只道是平移变换,不改形状,分毫不差方向,不见背景是崭新纸张,笔墨跟随着牵扯两模两样的底料清汤。心思浑浊昏黄,昏聩后清醒冷冽异常。不甚好看,在一个冬的夜晚霜华的始端。嘴脸的调色翻一翻。
转折点,下降的气压,过早的炽热,拔苗助长的荒唐,逼近零度的绝望。
这样一个他。只是他。只是存心写不对我的名字的他。
只是擅长逢场作戏的他。只是逢场作戏青睐我的单调长发的他。只是逢场作戏遇见我的狼狈浪潮的他。只是逢场作戏挑拣我的心情疮疤的他。只是逢场作戏讨要我的软弱好心的他。只是逢场作戏圈禁我的慌张无助的他。只是他。
这样一个他。不是他。不是那年夏天唤我傻瓜的他。
不是言辞浅浅温和的他。不是言辞浅浅来不及拥抱我的他。不是言辞浅浅未完成承诺的他。不是言辞浅浅忘了我的他。不是他。
被浪费的灼灼期盼。被记恨的灼灼欺瞒。
冰冷的心,灰色的心,渴切的心,坠落的心。辜负了指路的白衬衫,失宠的十一月怎么还担负得上早秋里晚风悠扬,味道腥酸,眼神涣散。感情抵不过欲望小小一场争战,抵不过旧人在梦乡规规矩矩捣乱。
然后,我们,多情冷漠各自求今后心安。
爱下去,也逃不过为良心奔丧。
走的路
吃的苦
怎么换良人同途
静待全世荒芜
也糊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