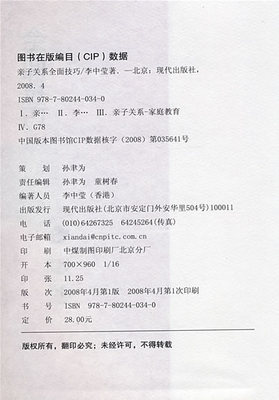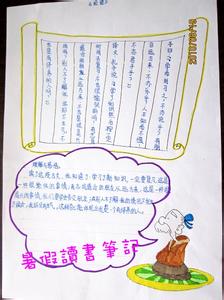坦白地说,读完整部《美妙的新世界》,让人不得不深思:文明和野蛮的真正界限究竟在哪里?

工业时代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众说纷纭。科技把神明揪下祭坛狠狠摔进了泥土,让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旷世惊呼,同时,蒸汽机和引擎却催生了一种新的信仰:在工业革命的时代,从流水线上走下的不只是源源涌进资本家口袋的财富,还有一种对科技力量的疯狂痴迷、崇拜。因此,在《美妙的新世界》里,汽车大王福特成为了新的神“福帝”,像旧时代的上帝一样被人们整日挂在嘴边。
科技缔造了新世界。在那里,连人的繁衍都成为了一种机械的程序,一个人的命运从受精卵形成的一刹那起便已决定,此后从出生到死亡,都再无悬念。一切变数,都被深入潜意识的“设定”抹成了零。人类被分成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伊普西隆五个等级,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印度的四大种姓——新世界,是一部像方程一样严谨的机器,每一个螺丝钉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毫不懈怠地运转,而且乐在其中——这是多少个专制王朝都梦寐以求而没能做到的,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八股取士力所不及的事情,科技做到了,而且做得近乎完美。
新世界的人们悲哀么?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是悲哀的。没有思想自由,生而不平等,仅有的两种娱乐形式就是做爱和吸毒,每天像《摩登时代》里那个小钳工一样在固定的位置完成固定的工作,这样的人已与工具毫无二致。那位西欧大总统穆斯塔法把“稳定”看得至高无上,而新世界的格局也的确不可动摇,这样的社会是远离了战争与动荡,但是,也从此与进步无缘。人类文明到此为止,只能在旧有的轨道上奔驰下去。我想,新世界的结局大概是这样的:最后一个人在唆麻梦里安静地死去,而空无一人的工厂仍在运转,忠诚地生产出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直到机器的最后一颗螺丝钉绣成灰尘之日……赫胥黎没有明说,但他眼中,人类的未来无疑是灰暗的。
应该注意到一点,我们对新世界的一切评论,都是以“我们不在新世界中”为前提的。假如我们把自己化身为赫胥黎笔下的角色,就会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对新世界的制度提出异议——若我们是低等的伽马、德尔塔、伊普西隆,胚胎时期的缺氧会让我们的智力无法理解“革命”的概念,更无从知晓“自由”“平等”为何物;若我们是高等的阿尔法、贝塔,那么,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新世界的不合理性,但新世界实在太安逸了,它是一个摇篮,却比坟墓更加可怕,绝大多数人都沉浸在肉欲与毒品造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因此,破坏新世界的制度,就相当于要切断所有人快乐的源泉,可想而知,大多数人是不会做出这种痛苦但明智的选择的。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度,都不乏向民众大声疾呼的智者,他们教导人们应该如此如此去做,可收效甚微。由此推理,即使新世界出现了一两个觉醒的高种姓人,也不会获得大众的响应——也许,他们最好的结局是像赫姆霍尔兹·华生一样,被流放到某一个偏远的岛屿,远离文明中心,背负着精神上的痛苦终老一生。
因此,我们面对新世界,只能发出一些无关痛痒的叹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看新世界的人,和看文革时代那些疯狂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会评论他们愚昧、无知,但身在其中的人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因为他们不可能站到我们的高度去看问题,我们也不可能降低到他们的水准去感同身受。许多事情正确与否,都得等到成为历史之后才能看得明白,这也许是另一种人性的悲哀吧。
《美妙的新世界》还向我们展现了新旧两种文明的碰撞。后半部书中,一个野蛮人闯进了文明世界,他恪守着古老的道德准则,喜爱“迂腐的”莎士比亚,渴望一场真正的爱情,而不是新世界中那种廉价的肉体欢乐。作者在叙述约翰的经历时,一直使用“野蛮人”这个称呼,但通过与他母亲琳达的对比,不难体会到深深的讽刺意味。新世界里没有真正的感情,只有从胚胎工厂出生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人,“爸爸”“妈妈”被视为污秽下流的词语;而在“野蛮人”的故乡保留地正好相反,那里残留着旧时代的风貌。新世界和保留地,都视自己为真正的文明,而把对方视作野蛮。在美妙的新世界里,野蛮人只感到痛苦,感到无法理解世界,也不被世界理解,因此,他最后选择了自缢,以寻求解脱。
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曾经令整个哲学界惶恐的问题:是否不存在绝对的道德标准?自量子力学确立后,整个宇宙变成了上帝手里的骰子,似乎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确定的了。有些人把科学的思考上升到哲学高度——既然我们连一个电子的运动都无法确定,那么,我们还能驾驭复杂的社会吗?似乎随着时代的前进,从前的真理都在被推翻、证伪,会不会有那样一个时代,今天的堕落全都变成美德,而古老的美德则成为罪恶的成因?显然,赫胥黎是一个为未来而忧虑的人,他的目光超越了时代,当所有人都在为技术进步而欢呼时,他却在思考科学可能带来的灾难。
我们需要更多的赫胥黎,我们需要“杞人忧天”的哲学家,因为我坚信,科学永远不可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当科学发展到极致,必然要求助于哲学,并上升为哲学。一句流行的话说,我们走得太快了,连灵魂都跟不上了。
文明与野蛮的真正界限在哪里?道德的标杆究竟是什么?未来的时代是否可以拥有与今天截然相反的价值观?赫胥黎抛出了一堆沉甸甸的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他也不可能给出答案。也许,没人能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