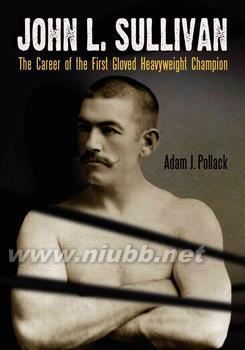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的首要的办公楼。
告别辛普森先生前,他问我下面要去哪里,我说要去哥伦比亚。去哥伦比亚干什么?他问。我说去密苏里大学看看。看什么?他又问。我支吾过去了,说就在校园里逛逛。
他反复追问,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我也不想细说,显得我比美国人还了解美国。
我想看密苏里大学呢,主要是想看它的新闻学院,那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成立于1908年。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在中国都很吃香。
民国初年就有中国人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了,其中之一是宁波人董显光,出国前在宁波的中学教过蒋介石英文,后来做过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台湾驻日本的大使、总统府资政。不过,我想他的最高成是他上个世纪20年代在天津创办了《庸报》,1928年东北王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身亡,正是董显光的《庸报》揭露出事件的幕后真凶是日本人。
我心仪的老一辈中国政治史学学者萧公权1920年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也是先到密大新闻学院学了一年。
新闻学院的图书馆。
设计室。
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生中在中国最成功、也最出名的,也许要算一个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准确地说,斯诺是密大新闻学院的肄业生。
斯诺在中国的地位,看看他生前在中国的待遇和身后的哀荣就可见一斑:六七十年代,中国闭关自守,对西方世界铁门紧闭,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得越雷池一步。大家还记得鲍大可吧?那个对中国一往情深、为美国培养到了大批中国学学者的著名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在中西隔绝的年代,他经常围着中国周边转,东南西北都到过,就是进不去大陆,他在香港隔海引颈而望,像个企望恋人垂青的小伙子。但是,斯诺却独步一时,获邀多次重访中国,甚至获得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同检阅游行群众的殊荣。
七十年代初斯诺在瑞士受癌症折磨的时候,中国特派了一支医疗队去瑞士给他看病。七十年代啊,我亲眼见过长沙郊区的农民用独轮车走很远的路推着生病的亲人到医院去看病。那种独轮车最常见的用途是把猪捆在车上往屠宰场送(我念的中学附近有个宰猪场)。
他死后,一半骨灰是洒在北大校园里的——北大的校园,精华部分,未名湖周围一圈,是原来燕京大学的家底,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沙滩搬过来,有优美传统和校园的燕京大学就被消灭了。扯远了。
八十年代,中国邮政还出过斯诺的纪念邮票。
给一个刚死几年的外国记者出邮票?他当然当得起这个待遇。想想他去延安访问的时间,想想他出《西行漫记》的时间,一切就都有合理的答案了。1936年,红军刚刚在狼狈不堪、牺牲惨重的大撤退后站稳脚跟,但依然顶着“赤匪”的帽子在那偏远贫穷的陕北挣扎,天上突然掉下个斯诺,西方记者,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愿意客观地向西方世界、向中国人报道这一群人的理想、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生活,在延安,还能找到比这更受欢迎的人吗?
1937年《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轰动一时。很多青年学生是看了《西行漫记》才投奔延安的。
大家熟知的那张毛主席在窑洞前戴着八角帽拍的照片,就是斯诺这次访问所摄。(后来,靠这张照片,他挣了不少钱。)
重庆时代周恩来的新闻秘书、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一任司长龚澎,我很喜欢的二战中随盟军在欧洲战场采访、名噪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萧乾,都是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
我把新闻学院四栋建筑的每一层楼、每个我能进去的房间都转了个遍,没有找到任何斯诺的痕迹,照片啊,塑像啊,题词啊,什么都没有。
在校园、新闻学院的楼群里逛的时候,碰到一位统计学教授、两位新闻学院的老师,问他们关于斯诺的事儿,他们完全不知道斯诺是谁。听我介绍斯诺,完全接不上茬。
照片上这位新闻学院的老师,教多媒体沟通,她叫“碧”,我忘了问她拼法,我猜也许是蜜蜂。她也不知道斯诺。
也许斯诺已经过时了吧。
时下与中国关系密切、在美国传媒界地位稳固的彼得.黑死乐(Peter Hessler),恰好也是密苏里人,而且是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所在的哥伦比亚出生、长大的。他1996年加入志愿组织和平队来中国,先在出榨菜的四川涪陵(也许是涪陵师专,我记不准了)一个学校教了两年英文,然后在中国当自由撰稿人,给美国很多重要的报纸、杂志如《纽约客》、《国家地理》、《华尔街日报》写稿。他出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在美国的“中国迷”中颇负盛名,其中有一本,我读过英文原版,似乎我在当当网上看到有中文版发售,书名可能是《寻路中国》。在书中,他对他的密苏里同乡斯诺不无微词:六七十年代,他让所有西方记者眼红,多次重访中国,足迹很广,还访问了数十个人民公社,但他在他的文章里、书里,对五六十年代之交饿死上千万(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三千万)的饥荒只字未提。这对有正义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的记者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耻辱。
黑死乐对斯诺的责备,让我想起另一位在中国成名的美国记者。他比斯诺成名晚,但也是因为报道中国事务而出名,他叫白修德。白修德在我们的抗战期间从哈佛大学毕业,不久就来中国,他在国民党的中宣部找到一份工作(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董显光那时应该是他的上司)。他很快发现,蒋介石的政府里的哈佛毕业生比后来的肯尼迪“人才政府”里的哈佛毕业生还多。他开始也很敬佩蒋介石,但很快就觉得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毫无用处。让他得出结论的也是一场饥荒。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冬天,那时候他已改任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他到河南实地采访,看到、听说饥民在吃树皮、吃自己的孩子、吃军队收容的弃儿。在同地方官员谈过话以后,他就像今天美国的政治性民意测验者一样,详细地作了笔记。他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在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军队在河南干的勾当就是大量征收军粮,数额超过了土地的产量。
白修德的最可靠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
他意识到,在重庆,蒋介石的政府里谁也不了解河南发生的事情有多大规模。河南的各级官员为了掩盖灾情真相,在送往重庆的报告中都是轻描淡写的,蒋介石最多也只知道缺乏粮食,为此他拨出了很小的一笔专款。
白修德在《探索历史》里记叙了他当时的状况:“当我想带着这些见闻去面晤蒋介石的时候,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我几乎像发疯一样地奔走呼号:‘老百姓正在饿死!老百姓正在饿死!’”
结果他违反了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没有把他的报道先发给中宣部的检查部门,而是直接在洛阳用电报发回了美国。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见到了蒋介石,向他做了报告。蒋介石表示感谢,说白修德是比他“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和当时在中国的大部分美国记者一样,白修德那时候极为钦佩周恩来,为周的风采和才干倾倒。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和他的同志,有理想,有热情,才华横溢,过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奋不顾身要推翻压迫穷人的旧世界,这样的人,在哪里不受景仰?在美国记者眼里,他代表着腐朽的旧中国里一小群最有朝气和希望的人。斯诺大概没想到,这样的人物有一天对惨绝人寰的灾难也会一声不吭、而且参与隐瞒真相吧?有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周密安排,不管新闻记者揭露真相的决心有多大,不管他采访本领有多高,他也看不到真相。这样一来,遭殃的就只有老百姓了。

其实说起来,密大新闻学院里处处看得见中国的印记。
门口一对石狮子是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送的。新闻学院有个历史陈列馆,门楣上的牌匾是解放前《申报》的密大新闻学院校友汪英宾手书、敬赠的牌匾。汪是《申报》全盛时期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史撰述人,文革中被打成“美国特务”,死在了我的一个支部同志的家乡——新疆库尔勒。
我在新闻学院图书馆里还看到一张放大陈列的获奖照片,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拍的中国大学生。
我觉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不会有太大的市场。
我参观完密苏里大学,向西骑车,往斯诺的家乡堪萨斯城方向走。我投宿在独立城(Independence),那是杜鲁门的家乡。对中国人来说,杜鲁门是个值得一说的密苏里人。用咱们过去对他的评价来说,他是个“反共老手”。实事求是地看,他有优秀美国农民的性格:朴素、率直、刚强,勇于承担责任。他当参议院主席的时候,在全国选民中声誉日隆、有意问鼎白宫的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朗格,连罗斯福总统都惧怕三分,只有他不怕,他敢对朗格冷嘲热讽。美国总统都怕工会,他不怕,1946年势力很大的铁路工会、矿工工会都被他斗倒,他的一位助手说:“他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当地响。”他任内,冷战刚刚开始,苏联对美国的态度,非常粗鲁,大名鼎鼎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尤其态度冷酷、野蛮,西方外交界对他简直又气又怕,但又不敢撕破脸皮跟他来硬的,但只有杜鲁门对他很不客气。有一次,莫洛托夫气急了,说:“我有生以来,从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杜鲁门冷冰冰地回答:“如果你们履行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在一旁的美国驻苏联大使看在眼里,啥也没说,心里痛快得不得了。
不过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密苏里人最值得提起事情是,他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把他从朝鲜战场调回了美国。否则,按麦克阿瑟的计划,中国就有可能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了:麦克阿瑟准备投50颗原子弹到中国,集中在东北的志愿军后方基地和供应中心。投50颗原子弹也不能征服中国,这是肯定的,但是,会死很多人就是了。麦克阿瑟在美国军界、老百姓中的声望非常高,但是杜鲁门作为三军总司令连麦克阿瑟本人都没通知,先给新闻界通了消息:麦帅被撤职了。
这么强硬的总统,他怕记者。
杜鲁门对别人的指责向来不大往心里去,但是你不能碰他的宝贝女儿和太太。他女儿是歌唱家,有次演唱会后,《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休姆写了篇乐评,说,总统的女儿“唱得不太好”。杜鲁门看了这期《邮报》后立刻给休姆写了封亲笔信:
“我刚看完你对玛格丽特音乐会的蹩脚评论……看来你是个事业很不如意的老头……我希望有朝一日会遇到你。到时,小心你的鼻梁会断,你将要用很多鲜牛排来贴你淤黑的眼睛,说不定下面还要戴上个护身腹带。”
信末,总统亲笔签名。
报界传出爸爸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信函后,做女儿的感到特没面子,都哭了。她对媒体说:“我绝对肯定我父亲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的。”休姆在他第二篇乐评里,第一句就说:“假如我可以斗胆发表意见的话……”
最后,杜鲁门向媒体赔了个不是:“我感情脆弱,有时控制不了自己……”
如果政客们都像密苏里人这样怕记者,老百姓也许更可能会少蒙受一些不白之冤,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死得不明不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