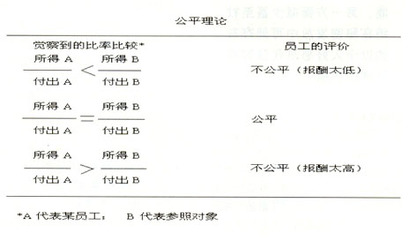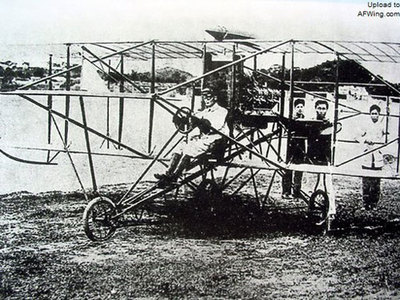哈贝马斯为何在中国受到追捧
丁子江
《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14日10 版)
《哈贝马斯:当代新思的潮引领者》,陈勋武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一版。
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东西方思想家评传系列”之一的《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著者为研究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的专家陈勋武教授。陈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对哈贝马斯哲学的教研工作,并与这位当代的思想大师有着深厚的友谊与密切的学术来往。可以说,这部力作就是他们师生之间的“哲学对谈录”。
这部著作包括:引言,第一章“重建现代性与普遍理性理念的思想家”,第二章“引导民主、正义与宪政思潮的大师”,第三章“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与包容政治理念的旗手”,以及结束语“后形上学式思维粹语”,条分缕析,才思敏捷,构成了强有力的论述链条。它集中地介绍和讨论了哈贝马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有主要著作与主要哲学理念。
早在2008年,我就拜读过陈教授的《哈贝马斯评传》(中山大学出版社)。这本新著堪称那本旧著的姐妹篇。正如著者所指出的,旧著主要介绍哈贝马斯2005年之前的生活与思想,但对哈贝马斯2005年以后的生活、思想与成就基本上没有涉及。新著弥补了这一空白。另外,新著不仅对哈贝马斯思想作了深入研究,而且突出哈贝马斯对我们时代精神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我们时代精神中的核心理念包括理性、现代性、民主、法治、全球正义、世界主义、人权、反人类罪、宽容与文化多元主义等理念所做的贡献。
作为本丛书的主编,我对哈贝马斯的思想也相当感兴趣,在多年教研中经常涉及到这位一代大哲。在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时,就选过哈贝马斯哲学研讨课,授课教授是著名哲学家施拉格(CalvinSchrag),他也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在施拉格教授指导下,我们五六名研究生用了整整一个学期专门研读了当时出版不久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一书。为了更好地了解批判理论等社会哲学学派,我于1987-1988年还在哈贝马斯在美国担任荣誉教授的西北大学哲学系研修了一年(哈贝马斯经常在这里作长期访问,他就是在这里得到2004年京都奖的通知)。2005年3月,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一次研讨会上聆听了哈贝马斯题为“在特定环境中宗教的公共作用”(ThePublicRoleofReligioninSecularContext)的精彩讲演。此外,因慕名哈贝马斯作为其领袖人物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我还于2006年夏顺访过法兰克福大学,但可惜无缘见到这位大哲。
二
陈教授在《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中提到,哈贝马斯曾于2001年4月访问中国,并以“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与国家”(Nation-StatesunderthePressureofGlobalization)为主题,作了一系列演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就像陈教授所引用一段报道所描述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听众太多,许多人甚至在狭长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据说是社科院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学术活动。在清华大学,莘莘学子不顾劳累,东奔西走,为的只是能在易地后的报告厅里争取到一席之地,哪怕是站席也行。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场面都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几乎爆棚,面对滚滚人流,校方无奈之下,只有求助武警维持秩序,把报告厅变成进不得出不得的“围城”。
哈贝马斯及其思想在中国受到追捧并非偶然,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是满足了正在进行关键性社会转型理论的紧迫需要。从内容上,哈贝马斯在中国的七大演讲的课题诸如人权理念的文化间体性、亚洲价值与现代性的关系、哲学的实践性、民主的正当模式、全球化及其挑战、世界主义、欧洲问题等等都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紧迫需要探讨的理论课题。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与在这些课题上的首席权威哈贝马斯的对话具有重大意义。在其社会政治经济学中,哈贝马斯主张“去阶级化”、“去经济基础化”、“去意识形态化”;区分“早期资本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并将“阶级冲突论”软化为“文化冲突论”;鼓吹“民主协商政治”以及“主体间的对话与共识”;推广“协商伦理学”、“协商政治”(deliberativepolitik)以及“大众民主主义”。哈贝马斯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经过时,晚期资本主义已凭借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在经济繁荣和发展中,阶级社会的同一性逐渐解体,阶级意识逐渐淡泊;阶级妥协几乎让所有成员均变成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为一个人”;从此阶级冲突转为一种文化冲突,即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更确切地说,新冲突形成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以及社会化领域中。哈贝马斯主张,在道德、法律以及政治等三大领域都必须实行协商原则,这就要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全面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使其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一种民主参与,协商对话,从而获得共识的“言语领域”(discursivefield)。由于改革开放,在最近30年中国特定的国情下,除某些“左翼分子”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个“共识”或“最大公约数”,就是应该淡化甚至完全消解昔日那种强烈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即便因两极或多极分化而产生的贫富不均或对政治体制的歧见,也当作哈贝马斯所标榜的“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从社会管理者看,哈贝马斯的主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可以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和言语领域内,通过规范化了的理性交往,使社会各阶层得到良性互动的理解与协调。从民间老百姓看,对明君清官崇拜的传承,使得人们仍希冀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国家等上层建筑出面对冲突进行协调和均衡。
其次是与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思想特征以及治学方法有关。如《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所指出,哈贝马斯的思维方式是后本体论思维方式,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思想特征是本体论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理论探索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全方位性,这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最后是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由于动乱、战乱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自从1920~21年,罗素与杜威以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访华后的六七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世界著名的大哲学家或大思想家来过中国,也许于1955年访华的萨特例外,但当时他的主要身份作为剧作家而非哲学家。改革开放以后,在1980~90年代,哲学学术界也邀请了一些较为著名的哲学家,主要是科学或分析哲学家,如受洪潜先生邀请于1981年访华的亨普尔(G.G. Hempel, 1905-)和1982年访华的麦金内斯(B. F. F.McGuinness)等。1999年9月,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曾于1955年作为法国记者代表团成员来过中国)访华;2001年4月哈贝马斯访华;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访华;2004年7月美国哲学家罗蒂访华。以笔者见,其中哈贝马斯的访华似乎最受广泛的瞩目。不过陈教授同时也正确评述到:在哈贝马斯到达北京之前,北京一些媒体就大造舆论,把他的此次访华与上世纪罗素、杜威、萨特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并认为他的中国之行将大大地推动中国的学术活动。不过,首先从时间上,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与上世纪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就不能相提并论。从2001年4月15日到达,4月29日离开,哈贝马斯此次仅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其次,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发生在上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它们所宣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因此,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不仅仅是学术之行,而且是在一个特别时期的特别事件,而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确实仅仅是一次学术活动。再次,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发生在他们与中国的哲学同行已有某些学术合作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的中国之行是深化他们与中国的哲学同行的学术合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哈贝马斯的访华更大程度上是一次友好访问。
三
在读过陈教授有关哈贝马斯的这两部著作后,我对哈贝马斯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两本相得益彰的力作多维次地揭示了哈贝马斯生平及思想理念的主要脉络。他的哲学著作广涉而又专业,哲学思想博大而又精深,哲学体系庞杂而又巧妙。哈贝马斯以反潮流的勇气,对理性与真理的信仰与执着以及对话百家的精彩,独步当今哲坛,领尽学术风骚。迄今为止,哈贝马斯已撰写了二十多部论著以及数百篇各类文章。其论著全被译成英文。其中,《公共领域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知识与人类兴趣》(1968)、《交往行为理论》(1981)以及《对现代性的哲学辨论》(1985)被公认为哲学经典,而《交往行为理论》是真正划时代的巨著。1994年退休后的哈贝马斯,始终笔耕不停,出版了《对他者的包容》(1996)等著作。进入21世纪,他继续出版了《分裂的西方》、《宗教与自然主义之间》与《欧洲:平淡的工程》等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哈贝马斯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列为20世纪100名世界名人之一,并被当今许多哲学家尊为20世纪末期最伟大的哲学家。
哈贝马斯于1950年代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成名于德国哲学界。此后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他致力于重建人类理性信念,发展一个开放包容、具有普遍道德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为一个合理、人性化与民主的社会提供理论基础。在其庞大的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中,哈贝马斯广集康德、谢林、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霍克海默尔、阿道尔诺、马尔库塞等各种德国哲学的精华;博采韦伯、杜尔克姆、米德社会学的各种理论,维特根斯坦、奥斯丁、舍耳语言哲学,皮尔斯、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帕森社会学系统理论之真知灼见。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交往理性与合理性概念,为捍卫现代化理念、自由与正义信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人性化(human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合法化(legitimation)成为其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概念。
从陈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既对欧洲现代启蒙运动加以批判,又重建现代启蒙运动的理想。他将现代性视作“仍未竣工的工程”,并创造性地提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rationality)、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普遍实用性(universalpragmatics)、讲述伦理学(discourseethics)等理论。他一生都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作斗争,尽管美国“9·11”事件后他与德里达有过短暂的政治合作。陈勋武专门着重分辨了“后现代思维”与“后形而上思维”的区别。这对笔者很有启发。他指出,后形上学式思维不是后现代思维。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的规范性,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的规范性。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标准的普遍性,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标准的普遍性。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存在着一个合法性问题,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存在着一个合法性问题。但是,后形上学式思维也不是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是民主性思维,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是专制性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是开放、容他性的思维,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是封闭、排他性的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思维的规范性,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同体性、同一性。”在这个议题上,陈教授引导了一个更深入的争论焦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多加商榷。
读陈教授这部与当代哲学大师的“对谈录”,就等于参与了思想与智慧的撞击与融合,从而扩展我们的眼界与胸怀!最后,我想以《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现在,虽然己进入了古稀之年,哈贝马斯依然保持着学术上高昂的激情,对时代充分的关怀以及对真理、理性与民主不断的追求。他的哲学生命仍是一团不断燃烧的烈火,他的哲学思维仍是一曲继续发展的交响曲,他仍在为民主、正义、宪政、人权不断斗争着。故事仍在继续。”
可登陆中华读书报网: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5/14/nw.D110000zhdsb_20140514_3-10.htm
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了这篇文章:请登陆http://www.cssn.cn/shx/shx_bjtj/201405/t20140516_1167492.shtml
由于中华读书报是纸质版,容量有限,有大量删节。因此影响力网与网易论坛等刊登了较为详细原文如下:
丁子江:听陈勋武“对话”哈贝马斯
(原题:一部与思想大师的“哲学对谈录”--读陈勋武教授的力作《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该书于2014年5月由国内九州出版社引进出版)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东西方思想家评传系列》之一的《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著者为研究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的专家陈勋武教授。陈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对哈贝马斯哲学的教研工作,并与这位当代的思想大师有着友谊与个人之间的学术来往和讨论。拿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自从出道以来,50多岁的陈勋武教授与80多岁的大哲哈贝马斯一直有着忘年的“神交”。可以说这部力作就是两位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哲学对谈录”,这部《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以引言,第一章“重建现代性与普遍理性理念的思想家”,第二章“引导民主,正义与宪政思潮的大师”,第三章 “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与包容政治理念的旗手”以及结束语“后形上学式思维粹语”等篇幅,条分缕析,才思敏捷,构成了强有力的论述链条。
早在2008年,我就拜读过陈勋武教授的哲学专著《哈贝马斯评传》,此书由他的母校中山大学出版。这本新著《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堪称那本旧著的姐妹篇。正如著者所指出的,《哈贝马斯评传》主要介绍哈贝马斯2005年之前的生活与思想。但该书对哈贝马斯 2005年以后的生活,思想与成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弥补了这一空白。另外,《哈贝马斯评传》重在对哈贝马斯的生活历程与思想历程的介绍,而不对哈贝马斯思想深入研究与探讨,更不用说突出哈贝马斯对我们时代精神所作的贡献。《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补充了这些不足,不仅哈贝马斯思想深入研究,而且突出哈贝马斯对我们时代精神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我们时代精神中的核心理念包括理性理念,现代性理念,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全球正义理念,世界主义理念,人权理念,反人类罪理念,宽容理念与文化多元主义理念的贡献。“当然,在内容上,《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与《哈贝马斯评传》多处交插。毕竟,哈贝马斯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理性理念,现代性理念,民主理念,全球正义理念,世界主义理念,人权理念等。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评传》并没有展开讨论这些理念,而《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对这些理念逐一展开了讨论。”
一
作为本丛书的主编,我对哈贝马斯原本也相当感兴趣,也多少在多年教研中涉及到这位一代大哲。在美国普渡大学读博士时,就选过哈贝马斯哲学研讨课,授课教授是著有《存在与自由》(Existenceand Freedom)、《经验与在》(Experience and Being)、《理性的来源》(Resources ofRationality)、《后现代之后的自我与存在之外的上帝》(The Self after Postmodernity andGod as Otherwise than Being)等大作的著名哲学家施拉格(Calvin Schrag,George Ade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Philosophy),他也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在施拉格教授指导下,我们五六名研究生用了整整一个学期专门研读了当时出版不久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理论》(TheTheory of CommunicativeAction)一书。记得当时选课的人虽不多但讨论却非常热烈。据施拉格教授事后评价,我本人与另一位台湾同学蒋年丰比其他美国研究生更能理会这位当代德国大哲的真谛。
为了更好的了解批判理论等社会哲学学派,我于1987-1988年还在哈贝马斯唯一在美国担任荣誉教授的西北大学哲学系研修了一年(哈贝马斯经常在这里作长期访问,他就是在这里得到2004年京都奖的通知);2005年3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一次研讨会上聆听了哈贝马斯题为“在特定环境中宗教的公共作用(ThePublic Role of Religion in SecularContext)的精彩讲演;此外,因慕名哈贝马斯作为其领袖人物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我还于2006年夏顺访过法兰克福大学,但可惜无缘见到这位大哲。
说实在的,很多年来,哈贝马斯以及其他欧洲当代哲学在英美,尤其是美国哲学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剑桥哲学词典》(TheCambridge Dictionary ofPhilosophy)1998年版就没有哈贝马斯的条目,直到后来再版时才得以添加,而早在1970~80年代,这位大哲在欧洲就声名大躁了。本来,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物理学和数理逻辑的发展,与科学思潮相逆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类似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潮很难涉足学院哲学界,但当分析哲学的形式主义走向极端,越来越远离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时候,势必会产生危机而使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批判理论派得以盛行。起初,后者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而在学院哲学界则无足轻重。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以后,它甚至在学院哲学界也不断扩大了地盘,逐渐成为除分析哲学以外的第二大哲学势力。正如“北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学会”(SPEP)发起人之一的施拉格教授所说:“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哲学被两大主要类型统治着,一类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另一类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受到人们重视,但始终不及前二者。”这话或许过于自信和乐观,但美国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批判理论派运动的发展是不能否认的。
全美约有4000多所正规大学或学院,其中大约有300多个哲学系有研究项目,在这里面绝大多数是由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作为统治哲学,只有西北大学、普渡大学、宾西法利亚州立大学等20~30个作为多元派重镇的哲学系重视欧洲哲学或其他哲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就连欧洲哲学,包括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甚至是废话,至于东方哲学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在美国,形成了以分析派为主流的一方与以多元派包括欧洲哲学等杂牌军为旁支的一方之间的争斗。但在近年来,分析哲学与欧洲主要哲学流派也有所谓合流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语言问题上。
二
陈勋武教授在其旧著中回顾,哈贝马斯曾于2001年4月访问中国,并以“全球化压力下的民族与国家”(Nation-States underthe Pressure ofGlobalization)为主题,作了一系列演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就象陈教授在其旧著《哈贝马斯评传》所引用一段报道所描述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听众太多,许多人甚至在狭长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据说是社科院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学术活动;在清华大学,莘莘学子不顾劳累,东奔西走,为的只是能在易地后的报告厅里争取到一席之地,那怕是站席也行;在北大,在中国人民大学,场面都可以说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几乎爆棚.面对滚滚人流,校方无奈之下,只有求助武警维持秩序,把报告厅变成进不得出不得的“围城”。
哈贝马斯及其思想在中国受到欢迎的盛况并非偶然,这有着以下重要原因:
第一点是满足了正在进行关键性社会转型理论的紧迫需要。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哈贝马斯企图“全面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去阶级化”、“去经济基础化”、“去意识形态化”;区分“早期资本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并将“阶级冲突论”软化为“文化冲突论”;鼓吹“民主协商政治”以及“主体间的对话与共识”;推广“协商伦理学”、“协商政治”(deliberativepolitik)以及“大众民主主义”。哈贝马斯强调,古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经过时,而晚期资本主义已凭借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在经济繁荣和发展中,阶级社会的同一性逐渐解体,阶级意识逐渐淡泊;阶级妥协几乎让所有成员均变成参与者和当事人,“成为一个人”;从此阶级冲突转为一种文化冲突,即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更确切地说,新冲突形成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以及社会化领域中。哈贝马斯主张,在道德、法律以及政治等三大领域都必需实行协商原则,这就要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全面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使其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一种民主参与,协商对话,从而获得共识的“言语领域”(discursivefield)。哈贝马斯社会哲学的基石在于:1)他了解交往的需要;2〕他强调我们能够依靠从自己公民获得反馈的一个法律制度下的所有公民所达到正当性;3〕他认知到在个人与社区需要之间永恒的冲突;4)他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希望,即一个法律制度有潜力克服那些掌控其他社会制度的特定利益,并为所有制度确立正当性。对哈贝马斯而言,社会目的是通过发现协调各种利益的美好途径,而并非凭借发现将自身与他人利益分离的崇高道路得以实现的。
由于改革开放,在最近30年中国特定的国情下,除某些“左翼分子”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个“共识”或“最大公约数”,就是应该淡化甚至完全消解昔日那种强烈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即便因两极或多极分化而产生的贫富不均或对政治体制的歧见,也当作哈贝马斯所标榜的“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从社会管理者看,哈贝马斯的主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可以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和言语领域内,通过规范化了的理性交往,使社会各阶层得到良性互动的理解与协调;从民间老百姓看,对明君清官崇拜的传程,使得人们仍希冀哈贝马斯所界定的国家等上层建筑出面对冲突进行协调和均衡,其中也有一部分较为清醒的人则盼望有更多的“大众民主”;从各领域精英看,哈贝马斯的“协商政治”、“民主参与”等理念无疑有着迷人的吸引力。
第二点是与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思想特征以及治学方法有着某种契合。哈贝马斯还是一个喜欢拖大体系的“哲学狐狸”,尤其他强调思想方法与理论探索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全方位性。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界和思想界仍然欣赏那种由罗塔德所否定,而哈贝马斯所鼓吹的以“元论述”或“元叙述”使之合理的思想体系,如用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解放、劳动阶级的解放或财富的创造等“雄辩”,来表达真理正义的“现代社
第三点是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由于动乱、战乱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自从1920~21年,罗素与杜威以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访华后的六七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世界著名的大哲学家或大思想家来过中国,也许于1955年访华的萨特例外,但当时他的主要身份作为剧作家而非哲学家。改革开放以后,在1980~90年代,哲学学术界也邀请了一些较为著名的哲学家,主要是科学或分析哲学家,如受洪潜先生邀请于1981年访华的亨普尔(G.G. Hempel, 1905-)和1982年访华的麦金内斯(B. F. F.McGuinness)等。1999年9月,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曾于1955年作为法国记者代表团成员来过中国)访华;2001年4月哈贝马斯访华;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访华;2004年7月美国哲学家罗蒂访华。以笔者见,其中哈贝马斯的访华似乎最受广泛的瞩目。不过陈勋武教授同时也正确评述到:在哈贝马斯到达北京之前,北京一些媒体就大造舆论,把他的此次访华与上世纪罗素、杜威、萨特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并认为他的中国之行将大大地推动中国的学术活动,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首先,从时间上,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与上世纪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就不能相提并论。从2001年4月15日到达,4月29日离开,哈贝马斯此次仅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其次,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发生在上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它们所宣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因此,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不仅仅是学术之行,而且是在一个特别时期的特别事件,而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确实仅仅是一次学术活动。再次,罗素、杜威的中国之行发生在他们与中国的哲学同行已有某些学术合作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的中国之行是深化他们与中国的哲学同行的学术合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哈贝马斯的访华更大程度上是一次友好访问。
三
在读过陈勋武教授的姐妹篇《哈贝马斯评传》和《哈贝马斯:当代新思潮的引领者》后,我对哈贝马斯这位哲学大师及其思想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两本相得益彰的力作多维次地揭示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生平及思想理念的主要脉络。从中我们得知,青年时期的哈贝马斯就读过戈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以及波恩大学;担任过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他的哲学著作广涉而又专业,哲学思想博大而又精深,哲学体系庞杂而又巧妙。哈贝马斯以反潮流的勇气,对理性与真理的信仰与执着以及对话百家的精彩,独步当今哲坛,领尽学术风骚。目前为止,哈贝马斯已撰写了二十多部论著以及数百篇各类文章。其论著全被译成英文。其中,《理论与时间》(1963)、《技术与科学是意识形态》(1968)、《知识与人类兴趣》(1968),《交往行为理论》(1981)以及《对现代性的哲学辨论》(1985)被公认为划时代的哲学精典。1994年退休后的哈贝马斯,始终笔耕不停,出版了《对他者的包容》(1996)、《理性与宗教》(1998),直到2006年他还出版了新著《分裂的西方》。哈贝马斯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二十世纪100名世界名人之一,并被当今许多哲学家尊为二十世纪末期最伟大的哲学家。由于他平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对社会的贡献,1987年,哈贝马斯成为施维茨(AlbertSchweitzer)之后第一个获得丹麦桑宁奖 (Sonning Prize)的德国人,并获得2001年的德国出版社和平奖(the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Retailers’ Society),2003年西班牙王子的阿斯图里亚丝奖 (Spain's Prince of Astarias),2004年第20届京都奖(Kyoto Prize)以及2005年洪堡国际记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Memorial Prize)等。
哈贝马斯于1929年6月18日生于德国的杜舍都府州(Düsseldorf)。与同时期的许多德国哲学家一样,哈贝马斯经历了二战后德国的迷惘,阵痛与反思。其中,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纽伦堡审判事件给他留下了触及灵魂,刻骨铭心的记忆,影响他一生哲学探索的心路。哈贝马斯50年代以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成名于德国哲学界。此后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他致力于重建人类理性信念,发展一个开放包容,具有普遍道德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为一个合理,人性化与民主的社会提供理论基础。在其庞大的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中,哈贝马斯广集康德、谢林、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霍克海默尔、阿道尔诺、马尔库塞等各种德国哲学的精华;博采韦伯、杜尔克姆、米德社会学的各种理论,维特根斯坦、奥斯丁、舍耳语言哲学,皮尔斯、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帕森社会学系统理论之真知灼见。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交往理性与合理性概念,为捍卫现代化理念,自由与正义信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人性化(human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合法化 (legitimation)成为其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概念。
在这本新著中,陈勋武教授以更大的力度“探讨我们时代哲学的一座丰碑—约根-哈贝马斯。这是一座闪耀着我们时代思想光芒的丰碑。这是一座可以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朱子等同辉的丰碑。这是一座可以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儿,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等媲美的丰碑。这座丰碑有许多衔头。其中包括: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三十多所世界最著名学府名校的荣誉哲学博士与荣誉法学博士衔头,除诺贝尔奖之外的所有欧洲最高级别的各种人文科学成就奖,亚洲最高级别的人文科学成就奖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人文科学成就奖,德国哲学家与后阿多诺-海德格尔时代德国哲学的主要代表,欧洲哲学家与欧洲哲学的主要代表,第二代批判理论哲学的旗手,世界著名哲学家等等。”
四
从陈勋武教授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受到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阿道诺(T. Adorno)、马尔库兹(H.Marcuse)以及杜威等人的影响。他曾对“启蒙”加以辩护,将现代性视作“仍未竣工的工程”,在对美国实用主义进行了“德国式”的理解与加工后,又创造性提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rationality)、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democracy)、“普遍实用性”(universal pragmatics)、“讲述伦理学”(discourseethics)等理论;并深刻抨击了“狭义”理解上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他注重社会理论与认识论基础的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民主的分析,批判性社会进化情境中的法律作用,以及当代政治的考察;他还发展了体现在现代自由机构以及人类对交往、思考和追求理性利益所具有的能力中,揭示有关理性、解放以及理性批判的交往(rational-criticalcommunication)可能性的理论体系。因此,有人给他加上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在这本新著中,陈勋武教授专门着重分辨了“后现代思维”与“后形而上思维”的区别。这对笔者很有启发。他指出,后形上学式思维不是后现代思维。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的规范性,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的规范性。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标准的普遍性。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标准的普遍性。后现代思维反对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存在着一个合法性问题,而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各领域社会生活与认识存在着一个合法性问题。但是,后形上学式思维也不是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是民主性思维,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是专制性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是开放,容他性的思维,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是封闭,排他性的思维。后形上学式思维强调思维的规范性,而欧洲启蒙运动式的现代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同体性,同一性。”在这个议题上,可以说,陈勋武教授引导了一个更深入的争论焦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多加商榷。
对后现代主义可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现代不少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都具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一切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哲人,像杜尔克姆、韦伯、霍克海姆、班杰明、阿道尔诺、卢卡其、弗罗姆、萨特、马尔库兹和哈贝马斯等,皆是如此(但在思维特征上又可以是现代主义者或反现代主义者)。从狭义上说,是指以拉康、德里达、福柯和罗塔德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消解主义”等思潮。后现代主义在政治层面上,主要批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典批判”;在文化层面上,则批判抽象的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采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指示者与被指示者、潜性与显性(弗洛伊德)以及现象与本质(马克思)等模式。在哲学特征上,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自启蒙时期以来作为蒙昧主义和盲从主义对立物的、以个人自律为标志的理性主义,并以一种非理性主义取而代之。以笔者肤浅认识,哈贝马斯则属于与上述多数后现代主义不同的少数派,他继续强调理性,但以一种“非经典性”,并以一种将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加以变种后的“交往”关系中来谈理性。
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其批判对象是后现代主义。他与福柯、德里达、罗塔德等之间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哲学争辩是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显要的一章,而他与福柯、德里达、罗塔德之间的个人恩怨更是为这一场哲学战争增添了精彩。哈贝马斯宣称现代社会的科学、伦理和艺术变成自律的领域,换句话说,认识工具、伦理实践关系表达的理性结构操纵在专家手中。也有的学者认为,哈贝马斯在思维特征上可以是现代主义者,但在其批判对象及实质上又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尽管哈贝马斯批判“后现代主义”,从广义说,他本人的哲学特征也属于这个思潮。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最模糊的概念之一。原本“现代主义”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至少有四个基本含义:(1)社会性含义,表现为文明发展的现代阶段,以工业化、都市化、民主化为基本特征,来拒绝旧的权威、秩序、制度和社会形态;(2)宗教性含义,表现为任何在现代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的影响下,对基督教传统的质疑、革新、挑战和批判运动;(3)哲学性含义,表现为用现代自律批判性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来解释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生活;(4)艺术性含义,表现为以现代的创作手法,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印象主义等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来表现绘画、音乐、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建筑等。总之,现代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和反动,以唯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标新立异向固有的形式和既定的规范挑战。可以说,现代主义是现代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
后现代主义的开先河者罗塔德(J. F.Lyotard)以否定态度揭示了所谓现代主义的思维特征。据他称,现代主义是一种以元论述(Metadiscause)或元叙述(metanarratives)使之合理的思想体系,它借助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解放、劳动阶级的解放或财富的创造等“雄辩”(GrandNarratives)得以发展,而以伟大历史和科学的描述来表达真理正义的社会则可称为“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的条件:有关知识的报告》(The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Knowledge)一书中,罗塔德将“后现代”界定为“对元叙述的不信任”(incredulity towardsmetanarratives),而且问道:“在元叙述成为历史之后,合法性在那里?”他认为,哈贝马斯正在提出某种比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元叙述更宏大的叙述,一个更加一般和抽象的“解放的叙述”。而在“神话与启蒙的纠缠”(TheEntwinement of Myth and Enlightenment: Rereading Dialectic ofEnlightenment)一文中,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对元叙述的不信任”所引发的问题,就是只有当我们“对解释所有合理准则〔reasonable standard〕的败坏至少保留一种准则”时,揭露(unmasking)才有意义。
与哈贝马斯看法相左的罗蒂(R.Rorty)是一名具实用主义倾向的分析哲学家,其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对哲学界颇有影响。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领袖之一,罗蒂批判了从笛卡尔到尼采的一系列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具体创造了当代北美文化的那种社会工程的历史南辕北辙,尽管这种社会工程对文化有利有弊。在“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一文中,哈贝马斯指出,在美国的一些重要哲学系里,很长时期内杜威是一条“死狗”(eintoterHund);1979年,罗蒂将杜威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称之为“本世纪三位最重要哲学家”之一;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上述局面才得以改变。在“哈贝马斯与罗塔德论后现代”(Habermasand Lyotard OnPostmodernity)一文中,罗蒂站在更彻底的后现代立场上,在支持罗塔德的同时,批判了哈贝马斯。罗蒂指出,凡是被哈贝马斯当作“理论探索”的东西,都被崇尚怀疑的罗塔德看成“元叙述”。而任何对这种理论探索的摈弃,都被哈贝马斯视为多少是非理性主义的,因为它排斥了始终被用于为启蒙运动以来形形色色的改革(它们勾勒了西方民主政体的历史)提供正当性的理念;这种理念至今仍作批判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习惯。
对哈贝马斯而言,抛弃一个即便并非先验但至少作为宇宙论的立场,就等于背离称为自由主义政治学核心的社会希望。对罗蒂来说,哲学不可能在探索中界定永恒的认识论架构。哲学家的惟一作用在于:斥责那种为避免具有“有关具有观点”的观点时,而具有一种观点的看法。伟大哲学家的政治观不必比自己的哲学观更严肃认真。任何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道德状况以及哲学写作,纯粹为暂时性、偶然性的。于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不再是对文学生产的评估,也不再是理智历史、道德哲学、认识论和社会预言,而是一种新样式的重新组合。罗蒂把尼采、詹姆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杜威称作“形而上学的破坏者”,因为他们摧毁了奠定知识根本训练的哲学基石。使福柯与实用主义者相融合的原因,在于他们都主张:(1)并不存在本身非处于创造实践过程中而创造的那种标准;(2)并不存在本身非诉诸上述标准的那种理性准则;(3)并不存在本身非服从人们自己传统的那种严格论证。罗蒂本人继承实用主义的衣钵,拒绝把真理看成以哲学兴趣进行理论探讨的东西,而是将其看作不过是全部真实陈述所具有的物的名称而已。
罗蒂指明德里达的“原创性”(Originality)会产生某种悖论,如很难区别新创、原创与改善。原创性在现代条件下值得商榷,因为它使自我意识、反人性主义、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原作化(Textualization)等许多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难以从现代主义旧框架中解脱出来。人们有可能公正地拒斥元描述,但理论总是试图寻求“自动的确定化”而不能贯彻自身,因此它应是一种使自身开放的社会实践的任务。罗蒂站在培根的立场上,批判笛卡尔一类哲学家应加固论述的基础、知识分子应成为政治领袖的观点。尽管罗蒂在后现代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的论争中,与哈伯马斯“相视为敌”,但又与之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罗蒂与其他后现代主义同伙们如罗塔德等人也谈谈打打,不全志同道合。总的说来,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与他们的欧洲同道一样,坚持着一种非历史化、非个性化、非建构化、非描述化、非差异化、非整体化、非专门化、非理性化以及非政治化的思想倾向。
以工业化、商品化、竞争化再加上民主化为特征的现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也给社会本身带来了客观自然界的惩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人类本身的对抗、仇视、犯罪、争斗,甚至杀戮;也带来了来自人们内里的精神性和价值观的变态、反常、蜕化和解体。一些哲人把这一切都归结于现代主义带来的灾难。因此,他们寻求一种新途径来解决社会弊端和精神危机。于是,这种特征的思想探索便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在一定意义上,哈贝马斯就是寻求一种新途径来解决社会弊端和精神危机。
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并非是“自称”,而是“他称”,即许多当事者并不自认是“后现代主义”者,而是他人主观的归类。哈贝马斯也是如此。“后现代主义”并无确定的定义。詹克斯(C.Jencks)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悖论式的“二元论”或“双重性号码”,可将之看作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超越。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是最新阶段的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极端夸大了的变种。格林伯格(C.Greenberg)把后现代主义称为“人们所有热爱物的反题”,或可当成在工业主义前提下文化民主主义美学标准的“弱化”。
班纳德(W.D.Bannard)尖锐地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无目的的、无政府主义的、无定型的、兼容并包的、表现为“边际型结构”的思想倾向,其目的在于我行我素的“通俗性”。胡森斯(A.Huyssens)乐观地称后现代主义为西方社会的“文化改革”。威廉姆斯(R.Williams)把后现代主义视作“感情的结构”。意大利批评家塞维(B.Zevi)则干脆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古典主义的赝品”。还有人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于“虚无主义”、“折衷主义”、“多元主义”、“通俗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后工业主义”及“晚期资本主义”等。后现代主义以不确定性引来许多代名词,如“超现代主义”(Super-modernism)、“反现代主义”(Anti-modernism)、“非现代主义”(Non-modernism)及“晚现代主义”(Late-modernism)等。哈贝马斯当然无法消受上述所有的标签化“丸药”,但他至少符合其中几种,如“后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后工业主义”及“晚期资本主义”等。
后现代主义试图从三个来源寻求有效的思想武器:一是“以古代否定现代”、“托古改制”,表现为某种“怀旧”的心态,即从古希腊和传统思想来源上找出可改头换面的原始素材,并对其加工后用以批判现代主义;二是“以东方否定西方”、“东为西用”,表现为某种“猎奇”的心态,即从东方文化传统思想来源上找出某些相对有价值的东西,进行加工,之后同样用以批判现代主义;三是“以明天否定今天”、“诉求未来”,表现为某种“空想”的心态,即以某种超越现代社会思想条件的可能的具有理想价值的假想,来批判现代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反对传统空想主义的思维与论述方式)。在所有这三个方面,哈贝马斯似乎多少都有某种程度的涉及。哈贝马斯与东方哲学界有着在“公共领域的交往”,1997年11月,为了纪念京都大学建校100周年,他应邀在该校作了一系列讲演;2005年3月5日,他专程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格分校参加了“京都研讨会”。哈贝马斯与中国哲学界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划分后现代主义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仿造化”,二是“精神分裂化”。现代主义建立在个性化发明之上,而形而上学则为这种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的个性主体以“过去之物”的形态显现,但不外乎海市蜃楼,实乃神话的虚构。在当今社会,个性风格的发展已随风飘逝,只有“仿造品”才独领风骚。这种仿造的实践和对死去类型的模拟,可在许多“怀旧”的影片中重现。人们既不能注重现在,也难以在历史上安置自己,甚而整个社会也无法对付时间。后现代主义以拉康的“精神分裂”理论来解释时间的观念。所谓精神分裂,是一种语言失序。诸如暂时性、时间性、过去、现在、将来、记忆及个人认同等概念都是语言的效应,因为只有语言有过去时和将来时,故可在时间中移动。精神分裂者的经验表现为暂时的、非连续性的,故是一种孤立的、无关联的物质象征。一方面,精神分裂者具有更多的有关世界的当下经验;另一方面,它又不具有个性的认同。正为了防止这种语言失序,哈贝马斯力图将重建公共领域、重建交往理性、重建语用沟通性、重建对话和概念范式、重建社会共识性与重建超语境的规则性加以结合,从而为人类重建现代性与新型现代社会关系。哈贝马斯强调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构。在现代社会中,生活于群体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互性逐渐取代主客关系以及处于个性结构中的单一主体性,遵循真实性、规范性和诚挚性等三项规则,通过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通语用互动手段形成公共领域,并在其间从本我到超我,界定团体认同的自我归属,从而避免和克服现代社会的分裂性。实际上,这也是某种后现代式的“仿造化”过程,因为它最大的结果就是取消个性化、独创化和个体理性化。
五
陈勋武教授的论述启发我对哈伯马斯有了更全方位的认知,这位巨匠不仅在社会哲学方面,而且对科学哲学家也进行的对话,他在分析了图尔敏(StephenToulmin,1922-)的论证方法后列出下面几条:1)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是否适于一切或大多数合理论证的模式;2)有关论证评估的标准、规范或建议一旦确定,就立即变成合法的,这种合法性不是通过纯粹修辞或细节,也不是通过演绎范畴的有效性、明确性以及归纳的力量获得的;3)除了规范的演绎和归纳逻辑外,还要求具有一种完整的论证理论;4)有人认为,针对认识论、伦理学和语义学这些哲学分支的推论,应从理论上澄清论点和非规范性的逻辑批判;5)对所有论证类型的兴趣是和描述不同类型之间的区别以及忽略其区别的兴趣交结在一起的。
哈伯马斯认为:这些理由表明了图尔敏在《论证的用法》一书中阐述的立场,这一立场也成为了图尔敏科学史研究著作《人类理解论》的出发点。一方面,图尔敏批判绝对主义观念(absolutitischeAuffassung),认为它们把理论知识、道德-实践认识以及审美判断还原成了演绎论据或经验自明性。一旦逻辑推论意义上的论据具有强制性质,它们就无法揭示出任何带有本质特征的新内容。如果论据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它们则会立足于依靠诸多描述系统和不同理论体系,并能够阐释自明性和需求,但如此一来,它们还是没有提供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图尔敏同样也批判相对主义观念(relativistischeAuffassung),认为它们无法解释清楚更好的论据所具有的那种丝毫没有强制性质的强制,也认识不到有效性要求的普遍主义内涵,诸如命题的真实性以及规范的正确性等。哈伯马斯进一步指出:图尔敏认为,没有一种立场具有反思性;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立场能在自身范围内阐明其合理性。绝对主义者不可能用其他的第一原则来证明自己的第一原则,来捍卫第一原则教义的经典地位。与此同时,相对主义者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特殊论证立场之中,他们认为,他们的教义凌驾于其他一些领域的相对判断之上。
总得来说,后期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有下列转型:1〕对主体的分析从先验性转为实践性;2〕对理性的分析从工具性转为交往性;3)对理论作用的分析从“批判性”转为“建构性”;4〕对国家职能的分析从“压迫性”、“霸权性”转为“民主性”、“调解性”、“福利性”;5)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从“生产关系性”、“单一经济决定性”转为“主体互性”、“多元文化再生产性”;6)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从“斗争性”、“对抗性”、“异化性”、“分裂性”转为“差异性”、“妥协性”、“公共性”、“参与性”。
六
顺便向读者较为立体地介绍一下著者:陈勋武教授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并于1987年到殴洲求学,在瑞士列支敦士的欧美国际哲学学院获得硕士学位,论文导师为欧洲最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和哲学家,前意大利文化部部长,前欧洲共同体法厅法官之一拉赫-布逖尤尼(RoccoButtigone),硕士论文为《论意识形态》。1990年,陈勋武教授从当时的居住地瑞士日内瓦转到美国纽约,在美国佛旦汉(Fordham)大学(纽约)攻读哲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为《文化与理性》。该论文探究了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在理性概念形成中的重大作用。该论文着重讨论了批判哲学的理性概念,尤其是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在佛旦汉大学(纽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陈勋武教授转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做哲学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学者杜维明,集中于比较哲学与价值观研究。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哲学博士后研究后,陈勋武教授转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一年的访问学者,后到现在所任教的徳洲大学圣安东尼亚分校(Universityof Texas at San Antonio)任教,现为终身教授 (tenuredprofessor)。从2001年底至2003年底,陈勋武教授为北美中国哲学家学会会长,并曾任美国哲学家学会亚洲委员会委员。目前,他担任英文《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of East-WestJournal)副主编,中文《东西方研究学刊》副主编,以及国际东西方研究学会(IAES)秘书长的等职。
陈勋武教授的专业领域和研究兴趣为欧洲大陆哲学,中国哲学与社会政治哲学。先后发表的英文文章有:“儒家理性概念重思”,“正义为公平,对和谐和的总合”,“理性主义与平均主义:中国民主历程的阴阳辩证法”,“文化与理解:笛卡儿的困惑,加达默的回应和儒家的结论”,“理性与情感:契约主义与儒家”等等。2003年底,陈教授的第一本英文书《存在与真实》由Rodopi出版社出版,获得好评。该书不仅成功地比较研究了当代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古希腊哲学,中国古代儒道哲学的人生观,而且成功地揭示了近现代欧美文学巨著中的人生观,富有新意地提出了真实的人生如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副图画的命题。陈教授的第二部英文论著《正义,人道与社会宽容》由LexingtonBooks也于2007年出版。在徳洲大学圣安东尼亚校区,陈教授所教的课包括: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亚洲哲学、古希腊哲学、当代美国道德问题、艺术哲学、文学中的哲学、世界宗教等等。在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陈教授也是文学艺术音乐的热情爱好者,其文学兴趣包括中国古典文学、法国现代文学以及美国文学,他最喜欢的电影为“北非谍影”、“乱世佳人”、“长长的一天”、“巴顿将军”以及“三个火枪手”。此外,陈教授还是网球业余爱好者,也喜爱长跑等运动。
陈教授中英德文三种文字具佳,曾在欧美多所名校从事教研工作,多年专门讲授哈贝马斯及其批判理论学派,并与这位大哲有过近距离的学术接触,还建立了私人间的密切友谊,因而撰写此书游刃有余,当然出彩。哈贝马斯亲自将自己的一些照片赠给陈勋武教授作为《哈贝马斯评传》一书的出版之用。听说,哈贝马斯对这本有关他的评传在中国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笔者本人与陈勋武教授合作,于2011年起,主编出版了国际英文学术杂志《《东西方思想杂志》(Journal of East-WestThought),创刊号的主题为“国际正义、世界主义与普遍主义”。由于与陈教授特殊的学术联系,哈贝马斯将他的论文“国际法的宪法化与全球社会宪法的合法化问题”(Konstitutionalisierungdes Völkerrechts und die Legitimationsprobleme einer verfasstenWeltgesellschaft)交由我们的杂志发表,得到很大的反响。
最后,笔者也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陈教授旧著《哈贝马斯》的结语作为结语:“现在,虽然己进入古稀之年,但哈贝马斯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学术激情,充分的对时代的关怀以及不断的对真理,理性与民主的追求。他的哲学生命仍是一团不断燃烧的火,他的这学思维仍是一曲继续发展的交响曲,他仍在为民主、正义、宪政、人权不断斗争着。”
读陈教授这部与当代哲学大师的“对谈录”,就等于参与了思想与智慧的撞击与融合,从而扩展我们的眼界与胸怀!
丁子江
影响力网:http://21yingxiangli.com/renwenyuedu/shuping/2014-05-08/45826.html
网易论坛:http://bbs.sports.163.com/thread/localhw-409423017-1|2T8tB.html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