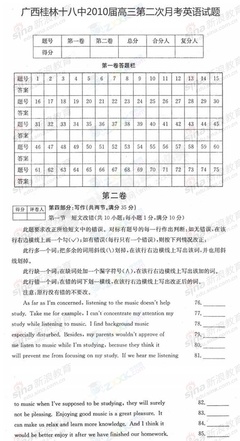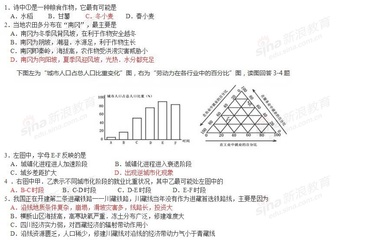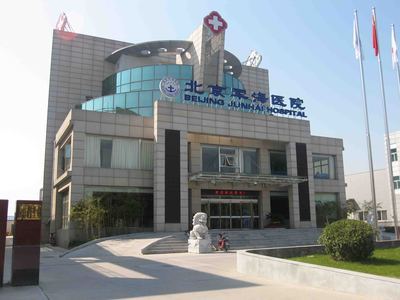
“霸上”与“鸿门宴”地理位置考实
王学理
一、“霸上”是秦汉都城东门的屯兵重地
“霸上”这一地名因近灞水,也称之为“灞上”。尽管取名的历史悠久,但最早的出现也不会超过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时期。因为他为彰显“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之功,便改滋水之名而为“灞水”,这当是“霸上”取名之源。
固然“关中之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左殽函,右陇蜀,阻三面而固守,独一面东制诸侯,形成为周、秦、汉、唐之都的外围防线。近而有霸上、细柳和棘门三地,则构成都城能够“固若金汤”赖以守备的军事据点。其中的“霸上”一地是咸阳和长安的东大门,对都城具有屏蔽拱卫的作用,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
“霸上”不但对保卫咸阳~长安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关中腹地东通燕齐、南尽吴楚地区的交通枢纽。所以,历来备受政治家、军事家的重视,都有重兵把守。据文献记载,历代发生在“霸上”的重大事件不绝于书:公元前207年楚将刘邦破武关、绕峣关、逾蒉山,攻入关中,先诸侯至霸上。后入咸阳,再还军霸上;汉初,刘邦率兵讨伐鲸布时,令太子监关中兵驻守霸上;吕后怒召赵王,孝惠帝自迎赵王于霸上;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派将军分三处在长安外围驻防以备胡,其中周亚夫屯兵细柳,徐悍驻棘门,刘礼居霸上;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周亚夫也是兵发霸上去平叛的;王莽派丞阳侯甄邯为大将军屯霸上;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麹允与公卿守长安,散骑常侍华辑以京兆、冯翊、弘农和上洛等四郡之兵屯霸上,终因寡不敌众,长安失守,愍帝出降,西晋亡;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桓温伐苻秦,进军霸上,逼近长安,但不渡灞水,关中郡县皆来降;“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几近土崩瓦解。苻坚二十年至二十一年(383至385年),鲜卑族的慕容冲起兵反秦,称帝建立西燕政权。从华阴西进,在霸上激战,乘胜攻占阿城,后入长安;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率八路大军攻伐后秦。后秦主姚泓屯兵霸上对抗,而王镇恶率水军从黄河入渭水,在渭桥登岸,破后秦军,后秦亡;刘裕南归,留下年仅12岁的次子义真等守长安。由于晋将之间自相残杀,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乘机由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红墩界镇北白城子村)南下,进陷咸阳,追义真至霸上,又在青泥关(北周改今蓝田峣关)大败晋军,于霸上设坛称帝;西魏文帝大统二年(536年),东魏高欢派司马子如、窦秦攻西魏。尽管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十有七八,但西魏宇文泰屯军霸上防御,才使东魏攻占长安的战略意图落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十二月十三日,黄巢称帝,国号“大齐”。后遭唐军反击而撤出长安,但随之又由霸上二返长安,竟歼灭唐军十之八九;清末,西捻军在灞桥(唐之霸上)设伏,全歼清军两万余人。……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霸上是首都长安东部的重要门户,谁一旦占据了这个地方,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至于人们把霸上作为迎来送往的礼宾之地者,著名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的。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大将王翦率兵六十万伐楚,秦始皇亲自送至霸上;淮南王刘安入朝,太尉武安侯(田蚡)迎之霸上;前秦对出征将士多送至霸上,如,送王猛伐燕(东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即370年)、送苻丕、送苻融等。霸上送别,唐人留下伤情之句,如“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李白《忆秦娥》)、“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李白《灞陵行送别》句)、“朝朝送别泣花钿,折尽春风杨柳烟”(鱼玄机《折杨柳》)、“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好风倘借低枝便,莫遣清丝扫路尘”(杨巨源《赋得灞桥柳留辞郑员外郎》)、“灞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韩琮《杨柳词》句)、“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依不胜春”(罗隐《柳》)。词人柳永触景生情,一曲《少年游》更是令人黯然神伤:“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二、“霸头”、“霸岸”和“霸上”并非一地
说到“霸上”,往往又冒出来个“霸头”、“霸岸”。几个历史名词纠缠不清,致使学者们众说纷纭,以至于对要讨论的问题也就原地打转或驻足不前。
《汉书·高帝纪》注引颜师古的话说:“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谓霸头。”在这里,他把“霸上”说成是“霸头”,也即是两者为一。(宋)程大昌在其《雍录》中竟把“芷阳”、“霸城”、“霸上”、“霸头”、“霸西”、“霸北”、“霸陵县”等地来了个“一锅熬”,统统放在白鹿原上。而且肯定地说“霸上云者,为其正岸霸水也。故既名霸上,亦名霸头也。”实际上,远非如此。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上有汉文帝“霸陵”,因此也称之为“霸陵原”。那么,“霸头”就应当是“霸陵原之端”的那块地方。因为白鹿原纵长约20公里,南接秦岭,茫茫苍苍,没有个断头。所以此“霸头”者指的当是原北端近霸河西岸的某地。称“霸头”者,历史上唯此颜氏一人。作为黄土原的北端,绝不是一个点,而是月牙形的地域。如果要具体一点指出“霸头”的所在,大概西安市灞桥区从纺织城到席王街道办的香王、安家村一带即是。
《水经注·渭水》:霸水“历白鹿原东,即灞水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是也,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在长安东南三十里”。北魏郦道元把灞水东的“芷阳坂”(即今之“洪庆原”)同灞水西的“白鹿原”混在一起。宋《太平寰宇记》说“灞岸在通化门东三十里,秦襄王葬于其阪,谓之霸上。”这里的“秦襄王”在“秦”字之后,不是缺了“昭”字,就是少了“襄”字。但这几位中不论是哪一位秦王,确实也都是葬在秦东陵(也即是考古工作者所谓的“芷阳陵区”)。唐通化门位于今西安东郊长乐西路的陕西西北火电工程有限公司东南角,其所言东30里的这个“霸上”就落在了今灞河之东、骊山西麓的芷阳阪(即洪庆原)这一广阔地域上。显然作者又把“灞岸”同“霸上”混为一谈。
“灞岸”一词多出于唐代诗文之中,而且是作为一个地名来对待的。既然是“岸”,必然是平行的两条线。但是,“灞岸”作为具体的名称实际上指的却是灞河。《新唐书·地理志》描述京城的形势时就有“京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左临灞岸,右抵沣水”的话。
“霸上”一地对卫护咸阳、长安都城的作用至为重要,其具体位置被郦道元、颜师古和程大昌等历史大家放在白鹿原上。近现代学者也多有沿袭此一说法的,(日)足立喜六说“灞桥左侧的高原是白鹿原,古代称之为‘灞上’”[1]。如果把“霸上”放在白鹿原上,但从战略着眼都同前述的历史事件挂不上钩。根据是:
其一,灞、浐二水源自秦岭,循白鹿原两侧北流,交汇后入渭。原长20余公里,最宽10多公里。地势高峻,东陡西缓,东北部从原顶到灞河谷地的落差几近300多米。“蓝武大道”位于灞河河谷的右岸(东),因此在车骑战的古代军事家既不会在白鹿原上设防,进击关中的军队即使攻破武关、经过峣关,也不可能爬上白鹿原直下咸阳、长安的。白鹿原高出西安200多米,陡峭的东侧加之外有灞河,就很自然地形成为都城东南的防线。
其二,白鹿原不具备守护京都东外围军事据点的条件,因为它只是一道屏障,还不是锁钥。在冷兵器时代,这里既不能有效地控扼“蓝武大道”,对“咸阳—函谷关”大道也鞭长莫及。到了火器时代,白鹿原固然成为军事制高点,但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则没有实际意义。
白鹿原上并不曾发生战争,尽管史载刘邦“引兵绕峣关,踰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汉书·高帝纪》),但秦蓝田县(在今县西三十里)是设在白鹿原上的。而这两次战事都是发生在灞河河谷的蓝——武大道上,并不是在白鹿原上。因为灞河与大道并行,又呈东南~西北的走向,所以前后两个战场正好处在蓝田县南北的两个方向。
三、在秦“驰道”与“灞水”的交叉点上探求“霸上”位置
控扼东方和东南的大道的咽喉地带不在白鹿原上,同样也不在“灞头”。因为那里尽管在灞河谷地的出口,当东南通武关的大道,仍然不是控扼都城东门的战略要地。
历史上重大的军事事件都发生在“霸上”,不只说明其地理位置的显赫,而且表现出战略意义的重要。战国到秦,以至西汉初年,一些重大的军事、外交、经济、人文活动多半发生在东方和东南方。从安全与人文着眼,“霸上”作为咸阳~长安都城东大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守住了“霸上”,就守住了京都,一旦失守京城就岌岌可危。那么,处于锁钥地位的“霸上”不可能把线状的“霸岸”当成据点。
历来对“霸上”的位置说法不一。除过前述在“白鹿原”的说法不能成立之外,“霸上”作为咸阳~长安东线的军事防守据点,其控制范围也较大,似乎可以涵盖芷阳阪。《水经·渭水注》:“(庄)襄王芷阳宫在霸上。”《陕西通志》也沿袭此说:“芷阳宫在霸上”。“上”作侧畔解,《论语·子罕》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话。那么,“霸上”的本意就是“霸水之侧”或“霸水之畔”。由这个意义出发,颜师古说“霸水上,故曰霸上”意即“霸水侧,故曰霸上”的话是对的。
要探求“霸上”的具体位置,通东方的大道要渡过“灞水”的津梁地带,就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自秦都咸阳渭河南岸新区成了京城重心之后,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第二年,由丞相李斯主持“东通燕齐,南尽吴楚”的“驰道”,使“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路面宽300秦尺(秦“六尺为步”),合今69.3米。路中心宽三丈,合今6.93米,从而成了一条高标准、高速度的主干道,大大地加强了首都咸阳同东方各大经济都会及江湖滨海地区的联系,对促进中国文化的统一具有积极的作用。汉都长安东出清明门,仍然走的是秦驰道。这条出函谷关的干道,发自咸阳~长安,向东过灞桥,这里当然就构成为有重兵驻守的咽喉地带。
秦汉时期灞桥的位置,当在浐、灞两水交汇后的下端。据考,约在今西安市未央辖区东部的袁洛村东南与灞桥区段家庒西北之间的灞河上,即今“浐灞生态区”的北部。在河东今有地名曰“桥梓口”或“桥子口”,我以为是“桥之口”之误,这表明它是秦汉灞桥东口不远处的一处古老地名。桥东10里是魏晋时的“霸城县”,再向东南当是秦芷阳邑、汉“霸陵县”的所在;桥西百步是“霸城观”,西去四里有秦子婴奉玺符来降的“轵道亭”,再正西“十三里”对的就是汉长安城的清明门(《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裴骃、《史记·高帝本纪·索隐》均引苏林语)。2002年,在段家村西北的灞河东岸河床上,发现汉代的水上建筑遗存,除过木构件之外,还出土有汉代砖瓦、陶井圈、陶片、汉五铢钱、铜箭头、铁器等文物,在粗绳纹砖上戳印有“亭”字的陶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应劭注:“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水经注》说“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其中除过郦道元所言三地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较为真实之外,他把“霸城”却当成了“霸上”,显然是错的。实际上,这两地是“霸城”在北,当秦汉灞桥遗址东北,地在谢王庄附近[2],今有新寺遗址;而“霸上”应当在前者之南,度量结果就落在秦汉灞桥遗址之东,当今西安市灞桥区西北的桥梓口附近[3]。从驰道与灞水的交叉点上探求“霸上”的位置而言,“霸水东西通得霸上之名”(《水经注·渭水》杨守敬疏)的话是对的[4]。
四、刘邦“鸿门宴”的逃归之路
公元前206年,项羽四十万大军驻新丰鸿门,邀驻军十万在霸上的刘邦与会。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和霸上的距离,是“相去四十里”。但在“鸿门宴”上演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一幕,却是惊人心弦的。为逃避杀机,刘邦“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史记》这段话仅仅从孤立的两个地点给出了两个数字:“四十里”和“二十里”。汉“四十里”合今16701.2米(417.53米/汉里×40)[5],即今33.4里。经实测,从“鸿门”到“霸上”两地的直线距离是19845米,即今39.69米。两者比较,地面测量的数字更接近“本纪”的真实。
从太史公用“相去”、“至吾军”等词语的区别上,结合驻军的常识,我们就会明白它有着指挥部(幕府)与营守地区的区别。刘邦军队已占有霸河东的芷阳地,所以他才有“至吾军不过二十里”的话。而且“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正是由芷阳地区走捷径才回到大本营的。
按人的正常速度步行,是10里/时。而刘邦骑着马,带领着手持短兵器的樊哙等四人作保护,快速脱离险境,为了保命,加快速度,离开鸿门进入自己的军事控制区顶多也不过一个小时。这对后面张良应付项羽的追问,才取得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注释
[1]a.足立喜六著、王双怀等译:《长安史迹研究》第12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1月版;b.马正林:《也论霸上的位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李健超:《被遗忘了的古迹——汉成帝昌陵、汉薄太后陵、汉霸陵城初步调查》,《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
[3]张永禄主编:《汉代长安词典》第2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4]a.李健超:《霸上与长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b.辛德勇有异议,见《论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5]新里据王莽尺度23.1厘米计算,见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又收入丘光明等:《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第24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版。
(2013.06.22~29)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