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男人,来一个,又跑一个,跑了又来新的。跑跑来来,也惯了。” 印度庙妓,来自一个传说。十六世纪时,一位南部君王,发现妻子与人通奸,盛怒下叫儿子把她的头颅砍掉了。这君王见儿子听他的话,问他要甚麽赏赐,儿子说想要母亲回来。可是,他母亲的头颅已不知哪里去了。那时,一个属於贱民的女子叶蓝玛(Yellamma)愿意献上她的头,作为接驳。从此,叶蓝玛和妹妹荷妮伽玛(Huligamma)得以归入印度众神的行列,成为女孩子献身作神仆的对象。 ...... 许多年代後,神仆变成妓女。 ...... 目前,在印度卡玛塔克邦(Kamataka)北部,有为数多达十万的庙妓。印度为人诟病的妆嫁制度,促使许多贫民将女儿献为庙妓。而且,没有儿子的父母,把女儿献出後,习俗上这女儿可以代替儿子供养他们。利益所在,许多父母便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 ...... 今年六月,又到了荷妮伽玛女神的节期,班加罗尔(Bangalore)的阳光依旧很毒,晒得河岸的粗沙闪闪刺眼。无数卡玛塔克邦的人,每年这个时候都蜂拥到来,很认真地在河里沐浴,很认真地到女庙参拜、求福。 我也曾经在这河里沐浴,而且,很庄重。 那天我沐浴过後,一件雪白的衣裳便披在我的身上。一轮诵经,击鼓唱颂後,我的前额给点上嫣红的朱砂。我的破衣就丢弃在地上。欢呼的声音把我簇拥著,我嗅著垂挂在发旁的鲜花的香味与祭司手中捧著的姜黄液的气味,一步一步迈向神庙,像迈向光明。我给灌了一口棕榈的酒,苦涩的滋味还在舌头徘徊,我已被引进庙里坛前端坐著。在女神面前,祭司给我挂上一串特制的红白相间的珠项链,宣布我成为女神的仆人,献祭礼就此结束。 我看见众人都在笑,我的家人也在笑,就如昨天晚上,父亲在惯常的醉酒中满怀高兴地对我说:“涂金玛,你嫁给女神後,一切蒙福,我们一家不用再捱饿受苦了。涂金玛,你要听话,听那庙里的人的吩咐,听你那男人的话。那男人,养活你,和我们一家大小,你一定要依从他的。这是你的福分。”我告诉父亲我很害怕。他责骂我,说我的银趾环、鼻环、手镯、金耳环、衣服、披肩全是那男人给我的。 事实上,我没听懂父亲说甚麽,只知道被选中嫁给女神是一种光荣,又知道我以後要跟一个男人睡觉。这是母亲多次告诉我的。 傍晚到了,在一片金黄色中,参加祭礼的人都走了,连母亲也走了。他们说要到外面吃祭礼中的山羊肉。母亲临走时,竟没看我一眼,像很满意地把我留下。十二年来,我首次被母亲撇下不顾,我很想呼喊她,但她已经走远了。 偌大的神庙静了下来,炎热的天气薰得人闷闷的。我悄悄左右窥望,几名僧侣正在收拾一切,空气静得令人心里发毛。在我惶惑的当儿,一名僧侣走过来,领我到庙後的一个庭院,庭院两旁尽是居所,大概有五、六个小房间。门,都是关著的,惟独一间敞开。僧侣把我领到门前,示意我自己进去。我犹豫地往里望,只见一个健硕的男人,满脸胡子,赤裸上身,躺在床上抽烟。我“呀”的一声惊呼出来,慌忙退後。那男人随即叫道:“进来,我的涂金玛,进来。”他的话算不得吆喝,但我的心却卜卜在跳,全身僵硬,只管用手死抓著门框。 他掷掉了烟头,立起身来,趋前拖著我的手,把我引进床缘。他很高大,我的头才到他的胸前,他的手臂像蟒蛇一般,紧紧缠著我。他用胡子擦我的脸,我不敢闪开,因为父亲曾叮咛:“你要依从你的男人,才有福分。”他那浓浓的眉毛压著双目,眼睛炯炯地望著我,望著我的身躯。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但母亲曾说:“不要怕,一切都是如此开始。你要依你的男人,才不会有灾祸。”我不敢反抗,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是要死了。那一夜,我的泪缓缓流下。但他压著我,像一座山。 天亮了,我一夜没睡,咽喉很乾。他起床後,洗过脸,走了。 每天夜里,他都会回来。临近黄昏,我就冀盼太阳不要下山,夜,不要来。每当我想起他那粗野的指头,就想到它随时会探进我的身里来;我的神经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停地在抽搐著。 我渴望黎明,像等待复活一样。不过,黎明到来,我又害怕碰见另一张脸,一张女人的脸。她和我的名字一样,也叫涂金玛。我们印度南部的女子常以女神命名。她就正正住在我的对面,她暗黑的脸容,阴阴沈沈,忧戚的眉头紧紧锁著,就像几条蚯蚓爬伏在上面。蓬松的发丝垂条下面,隐约露出一双冷峻的眼睛。她看你一眼,你就给她刺了一刀。 今早我一踏出房门,倒霉地又碰上她。她直视我良久,一把刀从我的头上劈下,吓得我双腿发软。直至她转了身,迳自向著通往庙後一条小巷的门走去,我才回复了知觉。据旁的人说,她来的时候,跟我初来时的年纪一样。她在这里差不多住了十三个年头,由较大的房间迁到小房间,小房间迁进更小的房间。现在,就住在最小的一个斗室,几乎只余一张床铺了。 我没有心情打探人家的闲事,因为我每天都要被种种烦琐的事情折腾著,为我的男人烧饭洗衣,还要应付经常来讨钱买酒的父亲。今天午後,我往外掏水回来,给一个莽莽撞撞的妇人碰倒地上。她回头看著我,看见我颈上红白相间的珠项链,破口就骂:“呸,贱货!”然後使劲地拍拍刚才跟我相碰的衣袖,不屑地赶快跑开了。我躺在地上,很想反驳她,又不知该说甚麽,只好向著远去的她吐一沫口水,捡一大把泥沙掷过去。然後,跑回我的神庙。 这一夜,他又回来了。三天没回来,今夜,他搂抱得更狠,像要把我整个人压碎。我的胸脯,我的内腿被捏弄得露出瘀血来。我奋力挣扎著,死命地把他推开。我们就像两头角斗的野兽。但毕竟他的力气大;他霍地坐直身子,瞪著眼一巴掌掴在我的脸上,随手把我揪住,又压下去。我感到阵阵晖眩,想吐。脸上热烫烫的,像要爆裂,迷迷糊糊中,过了一夜。 天亮了,我的头很痛,不能起床。半昏半醒中,看见他挽著一个小行李箱,走了。正午过後,我爬起床来,往镜子前照一照,手巴掌清晰可见,黑黑红红的,只消用指尖轻碰一下,都叫我痛得张开口来。我凝望著镜子,恍恍惚惚看见一双眼睛瞪著我,一双像对面涂金玛一般愤怒而森冷的眼睛,正盯著我。我定睛一看,这双眼睛竟是镶嵌在我的脸上。我害怕这双眼睛,我不要这双眼睛,我用手掩著脸,冲出门去。 这真是福气吗?我死也不相信。我含著恨坐在庭院中央的一棵大树下,月色透过树缝,洒满我的一身,我看见身上光光暗暗的影子,就像心底点点滴滴的血痕。 “他不会再回来,我肯定。” 这是另一个涂金玛的声音。不知甚麽时候,她站在我的身旁。我没有给她吓著,现在,我甚麽也不怕了。 “我的男人,来一个,又跑一个,跑了又来个新的。跑跑来来,也惯了。” 她是不是对我说话呢?她一直倚著树,望著天。 “这药很好,涂了就消肿了。” 她把一个黄白色的小瓶掷到我的身上,口里还在喃呢著甚麽。我听不清楚,但不像是嘲讽我。她眉头的蚯蚓仍在,眼神仍凶;但她的话柔细,像一阵无力的风。 她陪伴我直到天明。天刚亮,她的四名孩子都醒过来了,他们把垫在地面睡觉的席子卷起来,哗啦哗啦的,跑到庙外玩耍去了。 “你念过书没有?”我们坐在庙前的石椅上,涂金玛问我。 “没念过。你呢?” 她摇摇头,弯下身子捡起一块小石头,狠狠的掷得老远。她的蛮劲,想必是田间做苦力练就得来的。那只不过是每天十个到十五个卢比(几块钱人民币)的工资吧。 “他把我预备给孩子念书的钱偷光了,一去不回。他妈的,如果我碰上他,我一定打爆他的脑袋!” 她的凶相又跃动起来,眼睛变成一把刀,牙齿在磨曳著,嘴唇微微颤动,像随时会把人吃掉。 我不知所措,也不知怎样安慰她。我们静默著。忽然远处街角一阵喧闹声传来,只见一个小男孩被一群孩子抛得高高的,霍然摔落在一个垃圾池中。我吓得呆立著,身旁的涂金玛已箭一般跑了过去。我看见她抓著一个较高大的孩子,使命子般狠打下去,她搭在肩上的披肩失控地在空中向上向下飞扬。其他孩子慌忙散去,余下那高大的被打得俯伏地上,动弹不得。她抱起被摔下的小男孩,一步一步走过来,像一头雄狮护著它的小狮子。这是她最小的一个孩子。 黄昏过後,黑暗开始侵蚀庭院的每个角落。我看见一名僧侣站在对面涂金玛的门前,跟她说了几句。涂金玛立时脸色大变,一脚踢翻身旁的木架,一手拿起椅子,就往僧侣身上掷过去。她叉著腰高声咆哮:“不要再提这件事,我永远永远不会答应你!你给我滚,安麦斯永远不会嫁给女神,安麦斯是我的,我要把她嫁给一个平凡的人。是人,不是女神!去你的,你给我滚!滚!滚!......”那僧侣急急溜回庙里,她还力竭声嘶地骂个不休:“他妈的!绝子绝孙的女神!不嫁给女神!死也不嫁给女神!......” 她一面叫嚣,一面乱打周遭的东西。她的怒火燃烧了整个庭院,遍地的杂物像飘下来的灰烬。所有人都跑出来张望,但谁也不敢走近她。我很想趋前抚慰她,但旁人把我拉著,说不可走近她,因为她说了亵渎女神的话,跟她在一起,恐怕也会遭殃。他们还交头接耳说:“涂金玛留不住男人,就只怪她的臭脾气,不顺服。她是给女神降灾的。” 我迷迷惘惘躲在人们身後。直至人群散了,空寂的庭院只留下这个在躁暴後喘息的女人,拥著她的女儿,倒在大树下。今夜漫天星辉,可恨星月无情,永远像一个旁观者,在远处自顾自地朗照著。我倒了一盆清水,走近她俩的身旁,给她们好好洗个脸。涂金玛抬起头来,望著我,展现出和煦的眼神与胜利的微笑,把女儿拥得更紧。 资料及相片提供:香港世界宣明会《天国孩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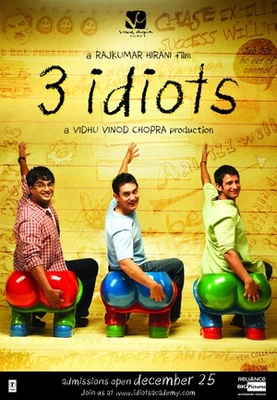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