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位特别的共产党人,他临死前的绝笔《多余的话》一度让瞿秋白背负了“叛徒”的罪名,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为什么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呢?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
当年目睹这一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瞿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
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瞿秋白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建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曾经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到了“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二)
回观瞿秋白的道路,研读其著作,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是瞿秋白自己认可的身份,也是他骨子里散发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的体现。身处巨变时代,革命是瞿秋白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革命大抵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开风气之先,首先在思想文化转变、重建过程中倡导、鼓吹和实践革命的理想。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和任务:面对现实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任务,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的内省、反叛精神,却时刻促使他们观照自身的灵魂,关注心灵的苦闷、彷徨、追求。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美的英雄,坚定的革命者。还有一种就是更多关注个人独立的精神空间,充满矛盾、犹疑和挣扎,在这里知识分子是追求与彷徨的混合体。鲁迅、茅盾、巴金等都书写了这一类知识分子。而瞿秋白,正是以自己的言和行为这个传统作出了个性化的注解。
丁玲的小说《韦护》以瞿秋白为写作原型,它栩栩如生刻画了其性格和气质。而“韦护”一名本身就暗藏玄机,是瞿秋白文化性格复杂性的一个侧面体现。据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所说,韦护是“屈维它”的谐音,“屈维它”是瞿秋白在《新青年》、《前锋》等杂志发表文章时所用过的笔名。韦护,就是佛教中韦陀菩萨的名字。瞿秋白以最是嫉恶如仇的韦陀命名,是希望自己能够奋生入世,拯救天下。佛学对瞿秋白文化性格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佛教所宣扬的以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为善行的教义,很容易引起具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瞿秋白的共鸣。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革命者的抱负、胸襟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气质和境界。就是这种境界,使他面临人生的种种坎坷,直至死亡时都能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他在狱中所写的几首词《浣溪沙》、《卜算子》、《偶成》等就具有浓郁的悲凉情愫,颇具佛家淡定、寂灭的意蕴,这些低徊婉转、悱恻凄怆的诗文隔着悠悠时空印证了瞿秋白至真至淳的性情,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同时,也道出了生命中禀性与理智、意愿与责任这些二元抉择中的两难情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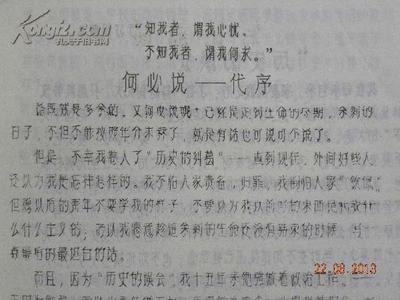
当然,佛学并不能真正调和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矛盾,比如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党性等,所以,在为信仰奋斗的过程中,瞿秋白无法排遣作为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孤独,也无法完成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转换。瞿秋白一直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有着对精神自由本能的追求。幼时良好的传统教育培养了瞿秋白的文人情趣、文人气质,他不仅工于诗词书画,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趣味:听戏、吹箫、治印等。最能体现瞿秋白浪漫情怀的莫过于他的两段婚姻佳话,尤其是“秋之白华”的故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段“三角恋情”演绎为一个浪漫美好的故事,瞿秋白的坦荡而热烈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本质上,瞿秋白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炽烈、浪漫奔放的诗人,当然,他充沛的情感是以革命作为底色的。
浪漫与革命,两者都是激情的象征,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知识分子的想象和预期中,它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骨子里充满浪漫精神的瞿秋白(们)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参与了革命实践,获得了革命家的身份认同,文化的构建与革命的行动获得了某种统一。但矛盾恰恰存在于此:浪漫的内核以个性、自由、反抗为本质,而革命却常常不需要、甚至完全排斥这些特性。他(们)不可避免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坚持革命信仰改造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抑制和背叛浪漫文人天然的个性需求。对此,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剖析:“他们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人类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毫无疑问会以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多余的话》却使他变得复杂、丰富了起来。死亡是人生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试金石,那一刹那流露的定是真实的性情。《多余的话》,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灵魂,瞿秋白解剖自己,审视自己,用这种方式拒绝无谓的崇敬和瞻仰。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瞿秋白表现出“走在希望的途中”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的跋涉中对自我信仰的坚执。正如他自己所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我们知道,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书生革命者”的困境》焦雨虹)
(三)
他的坦荡,他彻底剖析自己灵魂的态度都是罕见的,而他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英雄的认识的差异——即由神回归了人的认识观。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