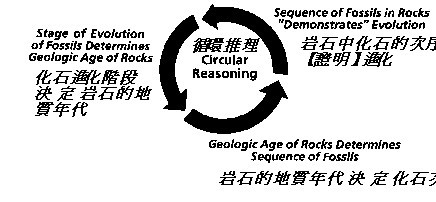作为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可能是何训田最为生活化的一次访谈。7月26日,在上海东湖路70号东湖宾馆里的大公馆咖啡馆,何训田依旧是那头标志性的长发,坐在对面就开始抽烟。三两个园丁在花园里浇花,从咖啡馆的落地玻璃窗看出去就像在拍年代剧。这里曾是戴笠和杜月笙的公馆,四周围绕着一些说不清楚的味道,比如木料在时间中慢慢释放的特殊气味,来自莫名国度的香薰,还有酒保在这个午后时光特意播的《卡萨布兰卡》。
何训田现在已经很少听音乐了。
按照媒体的普遍了解,何训田第一次听到小提琴是在12岁,在老家四川遂宁,他家隔壁就是基督教堂。他经常到教堂去练琴。他说这就是他对音乐空间认识的来源。1994年,他和音乐人朱哲琴合作的《阿姐鼓》是国际唱片史上在全球发行的第一张中文唱片。1995年,这张唱片在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出版发行,引起轰动。直到现在,他依旧不知道这张唱片的全球正版销量数据。
媒体说他没有手机、不带助理,常年写宗教音乐、孤独行走,是朵避世之花……实际上,他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还用诺基亚5310接了好几个电话,“我做的音乐根本不属于任何音乐类型,准确地说,就叫何训田音乐。”
他甚至说,他的梦中有种奇妙的咒语,能在他自觉危险的时候帮助他逃离。即将在9月推出的新作品《一訸上歌》,神秘、净澈、目空一切,据说就来自于他梦境中的美妙合唱。
摇滚格桑
根据网上公开公布的数据,《阿姐鼓》(SisterDrum)首批是在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后来在唱片公司的推广下,做到了全球81个国家和地区。何训田模糊的记忆里,《阿姐鼓》的正版销量大概有200万至300万之间,这个数据在盗版猖獗的现在,是个无比震惊的数字。《纽约时报》评价道:“《阿姐鼓》使中国人实现了让其音乐走向世界的理想。”和着随后在1996年推出的专辑《央金玛》(Voiceform theSky),何训田的音乐被更广泛地介绍到了世界。法新社兴奋异常地用“摇滚格桑”来形容何训田的音乐。
何训田,谐音何训天,把天和地(田地)都训了,口气很大。
采访何训田之前,还专门了解到他在音乐专业上的贡献,这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无法想象的。他在1981年提出“三时说”和“音乐维度论”,在其纲要中分别首次阐述了一些重要的音乐元理论。1982年创立了“RD作曲法”,被国际上称为中国当代第一位用自己的作曲技法创作的作曲家。俄罗斯音乐学家赫洛波娃教授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有了一个自己的音乐学派。“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独特的音乐,如此处理弦乐的手法。这音乐在欧洲没有,美国也没有,俄罗斯也没有。”
实际上,所谓的“RD作曲法”是在1986年作品《天籁》首演时才正式被试验成功的。“美国国际新音乐作曲家比赛委员会”授予《天籁》1988-1989年度唯一的“杰出音乐成就大奖”。想用简短的文字来解释清楚他的作曲理论是枉然的,只能这样说:是一种以全新的思维和结构方式创作出来的音乐。指挥家陈佐湟临上台时对乐队说:这只有凭良心演奏了。《天籁》一共只演出了三场,引起了国际音乐界的关注。
当然,何训田除了在国际上花香四溢,在国内的动作也不小。除了起点够高的《阿姐鼓》,民族管弦乐《达勃河随想曲》(1982)、多媒体音乐剧《迷哥》(2001)、专辑《波罗密多》(2002)、《七日谈》(2006)、《如来如去》(2008)、游戏配乐《神迹》都同样影响非凡。不过,在2009年3月29日,作为世界佛教论坛的献礼演出,何训田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吉祥颂》在无锡梵宫举行,他在全世界采集了几百个钟声和鸟声。钟声清净,穿透力强,干净又纯粹。“八百个和尚在合唱,很多和尚都掉眼泪了。那种震撼和空灵摄人心魄。”何训田说,要描述一个人的一生是极其困难的,只能用最简洁的方式,最后的演出文本上,他确定了三个关键词:此岸,走向彼岸,到达彼岸。
在这之前的2002年,何训田担任《雷锋夕照音乐大典》总策划、总导演和作曲,大典在雷峰塔重建开放日首演,杭州城万人空巷。后来谭盾的《少林音乐大典》开始出现。
少年纤夫
“我出生于四川遂宁,父母的工作都是与数学有关,兄弟姐妹六个里,我排行老四。”媒体习惯引用何训田这段极其规矩的自述。是因为要搞清他和音乐的关系,很难,同时也很有戏剧性。他第一次听到小提琴,是12岁,“四个空弦一拨出来,我当场着迷”。那时一把小提琴售价30元,简直是巨款,足以让一家人不吃不喝一个月。他悄悄瞒着父母,去嘉陵江上当纤夫。当时是每天结算工资,脱去鞋子赤脚踩在鹅卵石上,疼得几乎要跳起来。——这是世界上最残酷、最劳累的体力劳动。“纤夫们一天要吃9顿饭才能应付超负荷的体力支出,即使是这9顿饭,也是在此岸无路可走,纤夫们上船过河,到对岸继续去拉的间歇匆匆吞下。”而在何训田自己的叙述里,接下来的一幕无疑是催泪的:“纤夫端着滚烫的瓦罐(吃饭),马上舀起嘉陵江水倒在饭上降温,谁先吃完,谁就可以抢到纤绳最顶端的有利位置。因为那里最轻松,最少危险。”
“我是个脾气很犟的人。但身体上我犟不动啊,干了10多天我就不行了,收拾行李,就跑了,当时拿了20多块钱。剩下的钱还是朋友给我凑的,买到小提琴的那天,我感觉自己脱了胎换了骨。”他对故乡那把红色小提琴保持着强烈的精神眷恋。“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对那个的印象太过深刻。”何训田毫不避讳自己做少年纤夫的那段经历,他在那里遭遇到了江上力道铿锵的号子,成为他自我音乐教育的一部分。
何训田的少年行旅里还有一个意象不得不提。莱卡相机和一个牧师的孙子。少时何训田的家有个特点,旁边是个基督教堂,“我们家里是没有钟的,因为不需要钟,教堂里会敲钟。早上敲钟我们就醒,晚上敲钟我们就睡。有一次我翻那个土墙过去,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会面,他是教堂里牧师的孙子,当时我家没有相机,在他家我看见了莱卡相机!那时是五六十年代,第一次看到这种相机,我喜欢的不得了。之前见都没见过,那个样子很特殊,很好看,很有趣,那个快门声也很特别。还看见了辟斯顿的《和声学》、《作曲法》、《赋格曲》、《乐器法》、苏联的《基本乐理》一些书。”
何训田从小就爱做梦。做梦清醒的时候可以算数学题,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秘密,“我有一个咒语,但这个咒语是永远保密的(笑)。我在梦里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我念这个咒语,马上可以醒。所以妖魔鬼怪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念这个咒语……我对追来的妖魔鬼怪说不要追,追了也没用,我马上要念咒语了。”
“有一天我终于梦到了,梦到了小提琴,我就在梦里伸手把它抓住,马上开始念咒语,因为我头脑十分清醒,只要抱紧它念咒语,醒了它就是我的了。”但那是第一次,少年何训田感觉到他的这个咒语失灵了,感觉就有个力量把小提琴往外边儿拉,是咒语在拉,“另外一个力量把小提琴往我梦里边拉,我反复试这个咒语都没用,两股力量在抗争,最后实在没有力气了,我一松手,人就醒了。但小提琴留在了梦中。”
虽然他梦里的咒语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何训田最后离开四川时,把那把红色的小提琴送给了他的好朋友,牧师的孙子。
生活大师
何训田离开四川是在1992年,那时他已经很出名了。他选的地方是上海。
1982年何训田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后,根本没有经过聘助教、讲师的过程直接升为全国第一个破格的副教授,当时他已经在全国获得音乐类一等奖了,学生时代的何训田俨然已是大师。现在回过头去看,老何当时在故乡拉小提琴的理解和现在对音乐的理解,最基本的是一样的。“我这个人就是始终保持对音乐很真很纯的那个状态。”
现在正是何训田创作的黄金年龄。对四川保持着强烈精神反刍的何训田甚至之前在回答一个四川记者的问题时,“满怀深情地说了一句话: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给四川的。”当然,成都和上海带给他的都是转折性的东西,成都是个出发点,而上海比较特殊,“我想念成都的卤肉,烧酒,我喝酒以前还是可以的,兴致来的时候,‘两个小二‘(两瓶小瓶装二锅头)没问题,在成都有它独特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但是上海的习惯不同,上海似乎和所有中国的其他城市都不太相同,上海有一点偏向国外那种感觉。比较独立。”
老何六姐弟(三男三女)中有一半后来走上了艺术之路,两个作曲家,一个画家。何训田的二哥就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何训有,还有一个弟弟,老六,最小的。“老六荷译是个画家”。——除了何训田,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都在成都,与音乐那头的何训田遥相呼应。
老何对生活的要求近似于没有要求。他说自己住在“上海的农村“,一个大房子,里面装修得如同一座教堂,里面是他纯粹的包裹起来的乐园,也不用过问外界发生了什么。他对烹饪十分在行,不过他会觉得生活琐事会牵绊到自己的创作精力。“比如说,我一碗面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没有必要非得花一个小时整几个菜,有点儿可惜,也很浪费时间……不是说我对生活没有要求,我对它本身已经很满意了。”老何对房子、车之类的也没有太大兴趣,甚至对穿的衣服也不讲究。他至少有多年都没逛过街了,因为确实没那个时间。
记:你对物质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何:只要适合就行。我的要求就是满足我实验和创作音乐时的费用。
记:你和外界社会接触的方式很特别。
何:从小到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对我产生作用,但几乎全是反作用,看一个展览,听一个音乐会,被差的作品层层包围,但很有意义,告诉你千万不要像这样作。
记:《阿姐鼓》给我的感觉是一种东方情调:东方人,东方编剧,东方情怀。包括后来的《央金玛》,按照你当时的说法,《阿姐鼓》、《央金玛》是西藏地域性的,《七日谈》是东方地域性的,到后来就是无地域性,你以后你要走哪条路?
何:同时走多条路,非西方、非东方、非学院、非民间(四非)又是另一条路。“非非”(五非)又是再一条路。你必须不是原有的东西的时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1997年的《声音图案》是属于非区域那类,该作品是人类第一部献给所有物种的音乐。
记:但你不可能把作品永远停留在纸上,既然要做成一张唱片,就有一个商业性,唱片公司要生存,你担不担心唱片卖不出去?
何:不担心也不太关心。现在是唱片业最萧条的时候,演唱者不是靠唱片来赚钱,唱片仅仅是演唱会的广告。我没有演唱会,但唱片的发行量还不错。
记:你现在听不听音乐,听些什么音乐?
何:现在听音乐很少。
记:是因为没有时间,还是对音乐的兴趣产生了变化?
何:两个方面,第一,能听的音乐极少;第二,有价值的音乐通常不源于音乐。我们的艺术创作的现状仍然是模仿现代的西方和非现代的东方,美其名曰借鉴。我有一句话,是在八一年说的:作为一个创新者、一个有独立思维能力的创造者,学是为了不学,这才是学的真谛。不否认学院需要学,学院本来就是为了学者而开。但学的对象仅仅是一个参照物,不是自己,更不能占为己有,也占不了。绝不能把他人思想的结果作为自己的结果。真正的音乐家是善于将“非音乐”的心外大自然和“非音乐”的心内大宇宙转换为音乐。这是全球的问题,欧美也一样。真正的创新就是第一意识产生的东西。
记:最近正在做什么样的音乐产品或者说音乐实验?
何:最近有一个项目,叫做《一訸上歌》。“一訸”是梦境中的一个地方,“上歌”就是“圣歌”的意思。是第一部“前意识音乐”,是“前”不是“潜”。
记:那就是在享受梦境了?
何:我从小多梦,但非常遗憾没能在梦里听到过音乐。但有一次,我梦见了,感觉到就像是“上帝之声”,把我带到那个山谷里面,我看到有几十个人站在那个山上在唱歌,而且都是女孩,唱得很飘浮,像光一样层层向我耀来。当时我很清醒,觉得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醒了之后,我惊奇地告诉我朋友,说我昨天晚上梦里听到了一个从未听见过的非常特殊、感人的天外之音。
记:但是记不得了?
何:记下来了,就是我后来根据梦里的声音做的《一訸上歌》!《一訸上歌》今年就要出版,现在专辑封面还在考究之中。这些“创世纪”的声音令我都吃惊,所以我还在想这作品的署名,到底是该写我的名字还是写上帝的名字(笑)。
记:能透露这张神秘专辑的更多信息吗?
何:这个音乐跟我以前的很不一样。我在写的过程中是尽量把当时梦境中的声音记录下来,不可能很准确,尽量记住主要的。
记:听说作品还有一些“密语”?
何:呵呵,就是832。《一訸上歌》就是832(笑)。“832”就是表示这作品中一共有832句(吟唱),是由人类的声音发出832句非人类语意的圣歌。是32个声部的纯合唱,有32分钟长,中间不间断。
记:你的作品没有受过哪个作曲家或是文艺家的影响,但肯定有欣赏的作曲家或是艺术家,或者在你没有进入创作的时代,你会觉得他启蒙了你的音乐和感知。
何:有些艺术家会给我一种状态,让我着迷。比如莫扎特,心灵与作品相关,与俗世无关,他的心灵和作品是纯净、纯粹的,生活的逆境和尘埃污染不了他。我很欣赏人不抱怨的状态,抱怨的人是对社会不了解的人。还有,迈克尔·杰克逊还是可以的,他有创新的和独立意识,他新的发声方法、他新的舞蹈的语汇。还有荷兰画家埃塞尔等等,我赞成所有的独创思维。
记:你的这个专业当中凤毛麟角的几个人,在“世界级的音乐家”这个级别上的,你觉得什么是音乐?
何: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维。
记:但他最基础的构成,肯定是种声音。
何:那是当然,它本是就是听觉的一种艺术,作曲家的意义就是把所有合适的转换成听觉的东西,用他自身的体验去转换这种东西。
记:你有一天会不会做流行音乐,会不会改变自己?
何:已有的、已经出现在世的一切类别、风格的音乐我都不作,这是一直以来的基本原则。我自己的类别、风格已经够多了,已经作不完了。
记:你现在如何归类自己,新世纪音乐家、世界音乐家,还是什么?
何:都不是,我就是写自己音乐的一个音乐家。
记:我感觉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平和,可能也就没有不平和的时候。
何:其实我这一生非常非常的顺利,很顺,顺得完全就是……也或许是童年的磨难早已炼就成我,一切的不顺对于我都是顺的,把他人认为的险滩反视为平地的缘故吧。其实就是真的不顺来了也很正常,顺逆轮回是世界的常态,缺一不可。
记:那你现在的社会性事务还是要继续,你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工作状态如何?
何:刚刚完成北京国际音乐比赛的委约作品弦乐四重奏《香之舞叁》,此曲是进入第二轮的参赛团体必奏曲目,优胜团体将获得《中国作品奖》。来自世界各地的弦乐四重奏团体于今年九月中旬在北京竞技,中国有两个队进入。在学院我带作曲和作曲理论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时间相对灵活,很多时候可以呆在家里作我的研究。
记:你处在行政的位置上(何训田曾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肯定会觉得不太适应或者说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何: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任何事情一旦接手就要认真负责,这是我做事原则,所以在管理工作方面的一切发展很不错,作曲系欣欣向荣。我认为专业人员搞管理是一种自我牺牲,但有时也认为是“服兵役”样的每个人应尽之责。所以我在任职的第一天对大家说:这个主任应该像“值日”一样,半年一换,大家轮流值班,不然对任职者不公平。因为对行政管理工作没有兴趣的,任职期间就打了四次辞职报告。管理工作会占去自己的创作时间和精力,管理工作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没有加入管理工作之前,你会单纯、专注、无杂念的进入艺术的状态中……甚至相信世界上没有坏人……实际上连这个相不相信的念头都没有。
现在我的创作状态极好,思维通达,创意无量,刚刚经历了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时,连续半年不间断写作(不是构思,是不断的写)的“马拉松”,刷新了我连续工作的新纪录,我感觉,全通了!
采写:成都商报记者谢礼恒摄影记者杨刚
录音
整理:实习记者李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