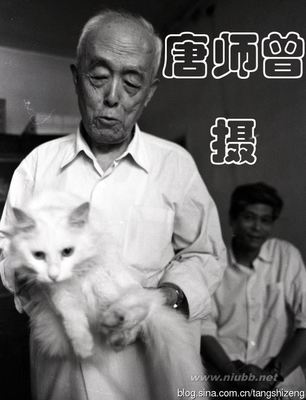任继愈。
两三次开会见过任继愈,未有近距离接触。
但经历过一件事,与他有直接关系——
1992年,我编辑出版了希腊作家卡赞扎基的长篇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
上市没几天,当年“两会”有委员质疑此书伤害教徒感情。
事情迅速扩大化,书要禁,人要深刻检查,责任领导也不例外。
我年轻气盛,不服,四处以顶撞的姿态做检查。
有趣的插曲是:每天接中宣部一位“局级调研员”的质问电话。
老太太也挺逗,经常质问几句为何还不通知书店下架图书之后,就开始和我谈文学。
《基督的最后诱惑》一书译者是董乐山、傅惟慈,他们身正不怕影子歪,
也与相关质疑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可惜,文人言轻,不起什么作用。

关键时刻,有人想到任继愈——学者,宗教方面权威人士,又有官方身份。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请任先生审读一下,看看此书到底有无大逆不道。
没想到,很快,四五天之后吧,一份三页纸的审读意见返回。大意是:
本书作者系希腊左派,一向与中国人民感情很深。
该书纯属小说创作,虽对基督作了一些人性化的描述,但主旨并未见有反基督之相。
对任当时的身份而言,这份意见写得既大胆又讲策略,对出版方非常有利。
我迅速将此审读意见层层上报,作协、出版署、中宣部……
有点像得了面挡箭牌。说来也怪,此事后来竟然真的就不了了之了。
那个局级调研员后来又打过电话,开门见山直接谈文学了。
季羡林。
与季羡林倒是多次见面,不过多是小时候陪家人去的,印象不深。
只记得他家一间大屋全是书柜书架,藏书量挺大。
还记得季很有礼貌,每次走时都送出门,车开出很远,回头看他还站湖边目送。
1999年,我当时供职的出版社要出十卷本“建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
各卷设主编一名,力求名头最权威。《散文卷》的主编定了季羡林。
大概是夏末的一天,我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与石湾、林非二位前辈一道,
又一次来到季家。可巧,客厅里,季正接待另一出版社的女编辑,
她同样是来请季主编什么书。
女编辑说:“……我们这书的编选工作想请您担纲主编。”
季听了连连摇头,说:“你这是个病句,担纲、主编二词重复了。”
见女编辑满脸通红,季又和蔼地找补一句:回去查查担纲是何意思吧。
那次聊天中,话题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诸种体裁,季突出惊人语:
“中国的现代白话诗,毫无成绩可言,不能算诗,仅有一首勉强可以算,戴望舒的《雨巷》。”
季说这话时,神情很激越,斩钉截铁,甚至有点怒气,令我一惊。
后来读过一篇季的文章,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不过因为是写文章,说得就比较含蓄:
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七十多年,“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
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