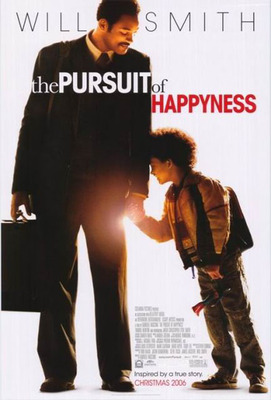许晓岚/文 鲍利辉/图
9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北京下着大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住在宣武门胡同里的那日松。当时,没有手机,也还没有BB机,碰到什么急事一般都直接找到了家里。
“走吧,带你去见吕楠。”他的一好哥儿们站在门口兴奋的说道,头发上尚且还滴着水。
时隔将近二十年,当那日松作为大理国际影会的策展人之一,坐在大理山水间的小石凳上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能够清晰的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他当时住在西单一个胡同里,其实跟我住的很近,就一个路口。那时的吕楠还留着长发,坐在一个破沙发上,头的正前方是一个昏暗的台灯。然后我们就聊了聊天。”
“臭味相投”成兄弟
碰到吕楠以前的那日松对摄影还提不起兴趣。人大中文系毕业的他原本一直以为自己应该去中青报这样的单位,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这是当年很多文艺青年的情结和理想。然而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说起来,被分配去了《大众摄影》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出路。至少是国家机关,有固定的工资。那几年,很多大学生都不那么容易找到工作。唯一让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对摄影并不来电。在九十年代一个中文系学生的眼睛里,摄影的力量远远不及电影和文学。“当时,做摄影的都是一些摄影干事,体力也比较好,摄影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仅仅是职业而已,为了宣传上用的。”那日松这样描述他曾经对摄影的误解和认识。
那几年的《大众摄影》的生活显得有点心猿意马,甚至中途两次想过要跳槽。只是都没有成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无意间从一本杂志上翻到了吕楠的照片。“当时就被震住了,觉得照片原来也可以这样拍。摄影真的可以达到像电影和文学这样的高度。至少这个叫吕楠的摄影师他做到了。”那日松这样描述那一刻的感觉。而也正是在这样电光火石的一刻,摄影从此和阅读,写作一样,变成了他不可离开的东西。
这个读着海明威和萨略的高傲青年,终于开始学着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审视摄影。
如果采访吕楠,那日松或者不是主要的话题,但是采访那日松,吕楠绝对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用那他的话来说,因为臭味相投才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两人的关系也可以用互相知道来形容。吕楠拍摄西藏题材的时候,常常三,四年都见不了面。但是,突然就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回来了,见面聊聊。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并不会使两人之间出现任何交流上的隔膜。很多话不用说,大家就会明白。“就比如说,我从来不会担心他在西藏的时候音讯全无,因为,我明白他是一个生存能力特别强的人。他可以应付的过来。而他对于我制作的照片也完全放心,因为他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也是这种默契,让我们两人一直走了那么多年。”
80年代的纯正气质
那日松身上有一种安静的气质,哪怕在大理影会这种热闹的环境中,也可以静静的坐上两个小时接受记者的采访。新华社的图片编辑陈小波与他聊天的时候,跟他提及了那些“英雄式的策展人”,他们富有朝气,纯正,充满许诺。这显然是旁观者对他报以的极高期许。而这种期待也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以及教育背景使之具备成为一个优秀策展人的能力。曾经热爱诗歌,朝气蓬勃的中文系学子,哪怕经历改革的浪潮,拜金的洗礼,社会的磨砺,那些理想主义的痕迹总是以某种倔强的姿态遗留下来,从而不露痕迹的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人。
在这个“文学青年”已经沦为骂人脏话的时代,那日松依然承认他曾经就是这样的人,以一种郑重的口气。中学的时候读顾城,大学看外国诗歌,影响最深的是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略萨的《城市与狗》。在接受采访时跟人说,四十五岁要退休,种种地,写写书。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典型的梦想和生活。只是,在通向梦想的道路上,有人选择的背叛,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选择了妥协。而今,四十出头的那日松面对记者对于未来的追问。仍然只是笑笑,“退休是一定的。但是退休并不是完全不做事,只是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还没找到方向。”
采访记录:
关于吕楠
许:我看过你的简历,其实你是误入了摄影这个行业。原本是做文字工作的,怎么后来就做摄影了呢?
那:就是因为工作的分配。当时有些特殊的原因,并不是你想去哪就能去哪的,好在我们都是由国家包了工作的,去《大众摄影》虽然不是我所喜欢的,但也算比较幸运。国家机关嘛,其实做了这个工作,有两次想过要跳槽。
许:听说你当时对摄影不来电?
那:就是没什么感觉,想离开这个行业。当时想过去中国青年报工作,但是最终都没能实现,所以留在这里干这个工作。我的观点就是做一件事儿就要做得像样,虽然不喜欢,但既然已经做了,就要把它做好。从那时候开始,就再没有跳槽的想法,老老实实地把这份工作做好。
许:那你有没有突然对摄影有点兴趣的那种感觉?一下觉得,对摄影有激情了。
那:说起来,应该是看到吕楠的照片的时候。我当时总觉得摄影是特别没文化的东西,摄影只能算是比较好的一种职业。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一本杂志,看到了吕楠的照片,突然发现中国摄影圈里有这么一种人,他把摄影的诠释达到了和文学电影一样的艺术高度,就突然觉得摄影还有点意思。
许:你是哪一年看到吕楠的照片的呢?
那:92年的时候,几天的时间,因为偶然的原因,两个人就变得认识了,我觉得应该是命运的安排吧。
许:你还记得跟吕楠见面的场景吗?
那:当时是因为我哥哥和他一个朋友要去朋友的家做客,然后我偶然的也就去他们家,就和他们的几个朋友开始聊天,说吕楠现在在干嘛,然后就问,“吕楠是谁阿”,然后我说是不是那个摄影的谁,他们说是,我说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之后过了两天,我就跟着我哥那朋友冒着大雨晚上11点去敲人家门,那时候没有电话,也不能预约,就直接奔人家家里了,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和吕楠家就差一个路口。
许:吕楠那会儿已经是光头了吗?
那:不是,那时候是长发,齐肩的长发。
许:你第一次见到吕楠都聊了些什么,聊到哲学了吗?
那:一个黑屋子,台灯下坐着一个人,好多人第一次看到吕楠都是这样的场景。我觉得跟他还能聊到一起,对摄影的认识和解释,我觉得真的能达到文学一样的高度,他的摄影也的确达到了那样的高度。之后就跟他成为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来,他很少跟摄影界有任何来往,展览邀请他,他也不参加,他的朋友也都是一些艺术家。
许:你们把艺术家和摄影家区分开来了吗?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摄影也是一门艺术。
那:其实摄影师和艺术家是不一样的。摄影师有职业性,他的身份更多是一种职业,或者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作为宣传的比较重要的一种工具。而不为任何人服务的这种人,才叫艺术家。吕楠就做到了这点,他从来没为任何人服务过。
许:我觉得艺术家在这个时代,可以摆脱政治力量的牵引,比如说吕楠,但多数人能摆脱经济力量的牵引吗?
那:我觉得这不能以你个人能够决定的,我一直认为不管摄影还是艺术都需要一定的天分,既然是需要天分,那么所有的天才和有天分的人是不用去关心钱的问题的。该活就活,该死就死了,比如说18岁死了,他也完成了他天才所完成的任务。60岁死也无所谓,他活着只是为艺术而活,并不是为了社会。
许:你能说说和吕楠交往的一些经历吗?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常我和他是三五年都见不着,他在拍西藏的时候。8年时间就见过他两三次。
许:那你们见面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呢?时间会带来隔阂吗?
那:觉得无所谓,虽然三年可能都没通过一次电话,因为我从来不担心他,他的生存能力我了解,是属于生命力巨强的那种人,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
许:你会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你跟吕楠之间的交往呢?
那:好朋友,相互能够知道的那种,我知道他想达到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帮他做这些展览,编辑画册这种,他也相信我能做到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几乎不用沟通,就能做到他所需要的效果。
关于纪实摄影
许:纪实摄影要是到吕楠这,该怎么往前走呢?
那:吕楠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纪实摄影。其实我都不承认纪实摄影,我也没有策划过纪实摄影的展览。纪实摄影在中国一个政治性的名词,在国外只有报道摄影和新闻摄影,到中国其实就是一种宣传摄影。文革时代的宣传,有的摄影师就会站出来反对这种不符合生活的东西,他们都不是新闻记者,但是他们可能都是一些摄影干事,身份相当于一个业余爱好者,他们没有话语权,但是主动给摄影师们提出了这些意见。纪实摄影这个词传出来在中国讨论了很多年,所以纪实摄影无所谓就是新闻摄影,可以统归于艺术创作的新闻性作品。其实很多摄影家拍的都是艺术纪实,就是一种思想性的东西,都是一些穷人矿工农民。他们的纪实事件,表现的是对社会的一种关怀,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小的情绪。但吕楠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摄影方式的影响,只是用了报道式的手法而已。他的这种方式只是想传达他表现艺术的一种影响。他也可能拍一些虚的东西,那都无所谓,对于他来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许:现在很多摄影师都会花几年去拍一个专题,那你觉得这个应该划入一个什么范畴呢?
那:他们都是艺术纪实,他们并不是想真去反映他们的生活,里面包含着个人的创作。
许: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往往会把自己的性格投射在他的作品里面,一些摄影家所拍出来的作品完全体现出了他人的一种状态,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那:我觉得无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拍摄方式,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抱有一种消灭自我的心态,其实一看照片就能看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摄影家拍摄的,他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像语言。
许:你所谓的影像语言是体现摄影师的一种性格吗?跟他摄影的风格等同还是不等同呢?
那:是合二为一的。
许:那么你觉得中国的观念摄影,包括这次来了一些国外的摄影师,你觉得中国同国外的观念摄影差距大吗?
那:差距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伪观念和伪纪实。

许:你的文章中也提过这种“伪”,能详细跟我们说说吗?
那:尤其是观念摄影的一种模仿的太多了。有的过于简单,我称之为创意摄影,跟广告公司的创意师一样,进行一些元素的组合,刻意去勾画出一个概念,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做的漂亮,观念并不是你强加上去的,好的摄影师是能让你一眼能把他的作品看懂。中国的观念摄影到后来也会变成一个商业性的符号,就是以后能够进画廊能卖钱,其实观念摄影已经没有了,大家谈的全是谁要拍观念摄影,谁就有希望。
许:公正的说,你是怎么去看待观念摄影的?
那:观念性就是思想性的,只要摄影有好的思想我都觉得是一个观念性作品,很多摄影都有观念,但那些观念是可以接受的,是高级的,对人有好作用的,保持着一种好思考。而牵强附会,强加在作品里的只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市场的这种观念就不行。现在说起观念摄影,别人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为了赚钱,为了一个可以销售的东西。
关于文学情结
许:看到过你和陈小波老师做了一个访谈,叫做《在路上》,听说你45岁想退休,这会儿你看你退得了休吗?
那:快了,现在43岁,还有2年,差不多。其实退休有两种概念,一个就是属于完全歇菜了,第二就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不再干任何强迫自己去干的事儿。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
许:你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属于简练,潇洒的那种。这和你大学时代的中文系背景有关吗?
那:还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喜欢看书,中学的时候读海子的诗,大学更多读的是外国的文学,中学的时候也会模仿写诗,挺好玩的,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有一些,还拿到去发表什么的,都是上中学的时候写的。
许:你那会儿有特别喜欢的文学作家吗?
那:小学的时候喜欢《水浒传》。中学读的更多的是中国的文学,上大学后基本读的是外国文学,大学毕业后就立志再不读中国的当代的文学类的书。再不读中国人写的小说,49年以前那些作家写的我还可以看一看。
许:你这个观点又跟吕楠很像,他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那:当我大学把海明威的什么读完之后,马尔克斯什么的读完之后就没法再读下去,太无聊了。
中国也有好的小说,49年以前的小说我还会读,看看一些汪曾祺的散文,喜欢看张承志的。
许:那你的阅读习惯现在还保持着吗?
那:到了90代的末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属于不读书的人了。
许:那你都在忙什么呢?
那: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编图片,编杂志,很难再静心的去读一本书了。所以吕楠这种人是很难得的,一本书都能读一百遍。马丁布伯的。如果有好的小说,我也会读很多遍。
许:那你读的最多的小说是哪一本呢?
那:读得最多的应该是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就是比较冷、硬,这对我影响比较大。后来我写不了长的东西,都是以最短的语言写完。还有就是略萨的《城市与狗》。
许:你自己以后还会不会写写小说?
那:应该不会,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化,有可能对文学还有一点点情节,有可能对文学彻底没有了兴趣,去喜欢另外的一件事,或者是去一个地方登山,也可能是去种地了,也可能就参加一个老年联谊会之类的。
许:听说你对电影对戏剧还是蛮感兴趣的,你现在还有这个情结吗?
那:只要骨子里有这个东西,自然就会关注,更会不自觉的去关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跟电影,也因为喜欢电影,稍微跟摄影有点关系。其实现在要做一个电影已经不难了,原来那会儿想考电影学院做导演,但是后来又担心考不上。后来我们一个成绩不怎么好的同学去考,既然考上了,所以那时候就非常的后悔。那同学出来虽然没有当导演,但是都当老师了,也挺好。觉得拍电影也要有一定的天分,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挺可悲的,很多东西永远也补不上了,所以我觉得吕楠很聪明,他的特点就是把几本书读懂就够了,他可以通过几本书直接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他可以跳过正常的学习和培养,可以用很艰苦的方式直接达到他内心的目标,他把艺术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爱恨交夹摄影节
许:你做了那么多摄影的展览,能谈谈你的策展经历吗?包括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都是一些稀里糊涂的结果,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媒体人,我现在还在负责编辑杂志,因为从小学的时候就想当一个记者,所以毕业以后,能干的就是这个,报纸杂志全都做过。其实做策展的工作都是因为偶然的原因,2004的时候故宫要做一个国际展览,是一个国际的摄影比赛,找我去帮他们策划,就不知道怎么的给他们策划成了一个国际性展览,从那次就成了策展人了。当时也不懂什么是策展人,就是把他们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我各国的朋友把这些摄影家都请到中国来。
许:你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资源,把世界上著名的摄影家都请到中国来?
那:我没有资源,但是别人有这个资源,是朋友的朋友在介绍。比如找美国的普雷基,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美国的朋友,要是请法国的摄影师,我又把法国的事情交给法国的朋友。想要请到的基本都还是能请到,所以从那次后就成为了所谓的策展人。那会儿对策展人也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已经把我称为策展人了,归类于这个范畴里面。因为每年都参加平遥摄影节,就开始实行这种策展人的职务,所以就变成了策展人了。
许:你参加过几届平遥摄影节呢?
那:除了去年没参加外,有8届,加上今年的就该是9届了。
许:相当于是见证了平遥摄影节的历程。
那:我绝对是属于平遥摄影节的一个元老,可以发布一个平遥贡献奖了,玩笑。对平遥宣传是做过很多的事情。在现场采访,做了一个很大的专题。当时很多人是不太重视平遥,但很多摄影师都是我们在平遥发现的。
许:你在这次的大理国际影会上策了王石的展,还获得了金翅鸟环保公益奖,你怎么看?
那:我以前经常为一些企业家和老板们做展览,不是说我要挣他们多少钱,我只是试图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好的摄影师是什么样,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是怎样的,让他们在自己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来为中国摄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次策展王石的照片,其实我没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不策展,就永远跟我没关系。
许:你怎么会为王石策展呢?
那:因为他们是深圳企业家协会的,是朋友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策展比较认真。而王石他是社会公众人物,他的粉丝众多,如果我现在通过给他策展,能让他知道摄影的魅力跟价值的话,我相信他会影响到他周围的很多人。
许:那你策划了那么多届摄影节,你对大理有什么样的感觉,跟平遥摄影节有什么不同,或者跟我们提提一些建议。
那:大理跟平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城市魅力非常强的地方,特别让人喜欢的。有些地方办摄影节,对城市的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大理就有吸引力的特点,大理跟平遥都是古城的感觉。居住的范围比较小。离展览的区位也比较近,方便展览更方便相互交流。这就是大理跟平遥很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是平遥历史比较悠久,平遥的展场比大理要丰富,应该说大理还没有一个正式专业的展场。
许:你觉得银海山水间也不算吗?
那:山水间也不是为摄影节服务的,如果他的房子都卖掉了,那怎么办,所以应该有固定的属于大理国际影会的展场,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地方。但山水间也可以算是一个,管理上要比去年的要更好一些,接待方面都还做的不错,至少没听到有人怨言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打倒摄影节》,那个总监老说我批判摄影节,但是我夸奖摄影节的比批判摄影节的多100倍,而他只看到了我批判摄影节。平遥是个摄影庙会,它可能不如大理专业,但是他的特点完全是就是一种自由,
许:你怎么看大理摄影节的未来?
那:我相信大理以后会更专业化,除了大理本身的城市魅力之外,应该彻底的突出的特色不够明显,比如说,有人说平遥“乱”,但是大理不会有人说它怎样,没有一个词汇来把特色的东西概括出来。这个地方虽不会像丽江那么浪漫,但是更平和更古朴一些,更能够让人静下来。说到大理摄影节,如果光以展览来讲,专业程度还不够,特色还不明显,缺少重要性和有目的性的策划,其实产生了怎样的一种观点和观念,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都是成为大理国际摄影节的里程碑重要点所在,在这方面,我觉得大理还需努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