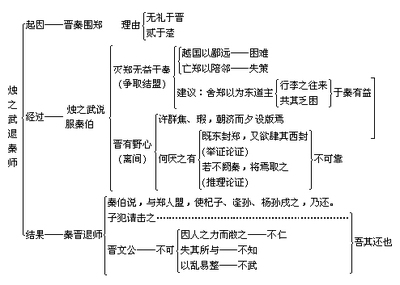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尼采
《悲剧的诞生》是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1844—1900)的成名作,写于1871一1872年。这个时期他依然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但在这本书中已经突破了叔本华的界限,尼采哲学开始萌芽了。不妨说,《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哲学的摇蓝。
这本书的主题是考察希腊悲剧的精神,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高扬艺术和审美的价值并而为人生的意义提供坚实的基础。
他以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概括希腊悲剧中隐藏着的两个原则,这两个不同精神原则的对立导致了古希腊悲剧的张力;同时,它们也是希腊精神的根本,是希腊人的两种“本能”,这两种本能的相互对立与共生并存促使希腊人创造出了灿烂辉惶的文化成就。而当这种精神丧失以后,希腊人的创造力也随之丧失殆尽。
日神是希腊的光明之神,名为阿波罗。在日神的照耀下,这个世界显得单纯、透明而美丽。所谓日神精神,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梦”。梦幻是美丽的,它停留于外观之美,这是一切造型艺术的特点。换句话说,日神精神是建立在我们的视觉之上的,它沉溺于这个现象的世界,尽情体会作为个体的喜悦与欢乐。
同时,这种日神精神又是严肃的,它在美丽的外观中保持着尊严。在日神状态中,万物秩序井然,散发着静穆的光辉。这种状态类似于叔本华所说的个体化原理,每个生命都是意志的个体化表现形式,它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欲求)而挣扎并相互蚕食,而意志在个体的背后坐享其成。日神是造型的力量,在尼采看来,是日神造就了这个个体的世界。但与叔本华不同的是,尼采的日神所创造的世界不仅仅是个体的苦难,还有美丽的外观和在酒神状态中所体验到的存在的毁灭的快乐。
酒神,希腊人称之为狄奥尼索斯,为冲动之神。以“醉”来描述酒神精神的本质是最贴切不过的。酒神精神的本质是激情,在激情的激烈进发中,人们忘却了自己的个体,忘却了自我,融人那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永恒意志之中,因而也忘却了人生的一切烦恼。个体世界的一切樊篱被打破,什么奴隶与主人、贫穷与富有、生与死,一切界限都荡然无存,万物融为一体,天下大同,所有人似乎构成了一个共同体,甚至人们感到与永恒的宇宙本体也合而为一了,这时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自己也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了一件艺术品——其创造者是宇宙本体。在这美的迷狂中,体验到一种醉的战栗。个体于是得到解脱,融人了整体世界,他自己仿佛也成为那个宇宙本体。
日神精神的作用在于为人生提供一种活下去的理由:正如叔本华所言,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如果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待人生,那么人生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种种艰难困苦使人生显得如此漫长难熬,就此而言,一个人不出生才是最大的幸福。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活了,那就应当活下去,于是敏感的希腊人用美丽的神话为这个个体化的世界抹上了一层壮丽的光辉,使人生显得美轮美奂,值得一过,即使这是一个梦幻,也要把它梦下去。
可是这个美的世界毕竟是虚幻的,在希腊人的美丽世界中总隐藏着深深的痛苦,对于这痛苦的解脱,日神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借助于酒神的威力。于是希腊悲剧中的另一个精神原则——酒神就出现了。酒神的作用就在于正视人生的痛苦本质,把这痛苦当作欢乐来享受,而这只有在忘却自我、放弃个体的主观性时才可以达到。在毁灭的快感中,人们体会到了在现象背后永恒存在的生命核心——太一,在忘我中达到与它的统一。在这里,个体化被看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是应当鄙弃的,在忘却了个体的“醉”中个体被消解,痛苦也被消融。
酒神精神也就是音乐精神。酒神完全没有形象,它就是原始的痛苦本身。音乐依然,它没有任何形象,而只有旋律,即使歌词一类文字也只是音乐的模仿,是内在旋律的生硬外壳,它们只不过在全力以赴地表达音乐,若不然,语言就成为多余的东西,就会伤害音乐。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二元对立是希腊文化繁荣的根源,也是希腊精神的根本。这种对立使希腊精神保持着极大的张力,从而使希腊人焕发出了辉惶的创造力。但是,到了苏格拉底,这种悲剧精神被毁灭了,相应的悲剧艺术也随之灭亡。从此以后,冷静的思考取代了日神的直观,酒神的兴奋被热烈的情感所代替,理性生义粉墨登场了。
苏格拉底提出“理解然后美”,然而由于逻辑的天性过于发达,美也就在理性的分析中被分解,日神倾向在逻辑主义公式中化为木偶。苏格拉底相信知识,提出著名的“知识就是美德”的命题,认为罪恶来自无知,而知识可以消除罪恶,从此确立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即用人类的知识可以把握世界,使西方人走向了肤浅的乐观主义。在这种乐观主义眼光中,只有那些已经被揭示出来的真相才是值得欣赏的——这与艺术家完全不同,他总是痴迷于那尚未被揭开的面罩。在苏格拉底那里,实际上是用“真”代替了“美”。
这种乐观主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它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能够把握世界。它相信,只要追根问底,就可以获得真正的知识,而知识可以带来幸福。它没有意识到逻辑有其限度,知识有其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就是“自在之物”,那是任何知识都不能达到的,只有通过酒神精神才可以到达。
希腊悲剧精神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艺术形而上学,它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是有理由的,否则便是荒谬的,没有存在的根据,也没有活下去的依据。而在审美的世界观中,无论是丑还是不和谐,也都具有了美学的意义,它们都是一种审美的游戏,是永恒存在的太一的自娱自乐,而我们作为它的一件艺术品,也就获得了价值和意义。
尼采所言很有道理。建筑在知识基础上的乐观主义是肤浅的,而悲剧意识才是深刻的。前者导致了主体论的哲学,把人看作宇宙的主人,要征服宇宙;后者是建筑在对于世界的无限意识之上的,在无限的力量面前,有限的人类永远是渺小的,无论活多长时间,即使活十万年,与无限相比也只是一刹那而已。建筑在无限意识上的人生才是有深度的。
不过,人生似乎应当在乐观与悲观、喜剧与悲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才不至于陷人极端。过于乐观使人浅薄,过于悲观则失去生气。
真理与艺术也是这样,它们在我们的生活和精神系统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不能相互代替。若是只有真理,人生将会了无趣味,甚至变得丑陋;假如只有艺术,则未兔陷人空想,脱离实际。两者交替作用,才使人生变得多彩。
尼采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诗性的精神,只有诗性的东西才能够给人生增添光彩。诗性是人生与艺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而诗性并不仅仅存在于诗歌之中,而是存在于一切创造性的活动之中,存在于亚历山大的远征队伍里,存在于毛泽东的长征途中,也荡漾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和康德仰视星空的眼睛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