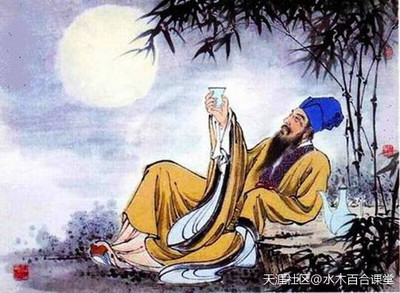乌台诗案始末
李炜光来源:读书 2012年3期
苏东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摊上了个案子,这案子差点要了他的命。有人说,是王安石陷害苏东坡,正史、野史里都有这个说法,真是这样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置苏轼于死地?案子发生在元丰二年(一○七九),当时苏轼刚从徐州调任湖州,他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吟诗作画,自得其乐。然而好景不长,三个月后的一天,苏轼正在伏案工作,进来几个御史台的人,宣布:御史中丞召见。苏轼不知来人的目的,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来的皇差叫皇甫遵,淡然说道:并不如此严重。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上面说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见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湖州到汴京要走二十多天,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案子由御史台审,提出的罪证是一本别人为苏轼刻的诗集。御史台的别称是乌台,苏轼这个案子又是由诗而起,所以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也叫“乌台诗案”。
苏轼获罪的原因是诗作,但到底是什么诗、哪句诗,使他惹祸上身的?御史台主审官把这本诗集当中的一些词句摘出来,捕风捉影,硬说苏东坡在诗里流露了对政府甚至对皇上的不满和不敬,用“文革”中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无限上纲”。
监察御史舒亶在他的弹劾奏疏中把苏东坡的诗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陛下不是实行“青苗法”吗?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不是要明法整顿吏治吗?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却无术”;陛下不是要兴水利吗?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不是要推行盐禁吗?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苏东坡的诗经舒亶这么断章取义地一“解释”,立马变得处处与新法、也跟神宗本人过不去了。宋神宗正为新法不能顺利推行而烦恼,舒亶的挑拨尤如火上浇油,便命御史台立案审查。这就是“乌台诗案”的由来。可见,不是哪一首诗,哪一句诗,而是很多诗里面的几句诗,被御史台的人抓住了“小辫子”,要跟苏东坡算总账。

这些人为何要陷害苏东坡?诗案的发生,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廷围绕赞成与反对变法,形成新、旧两党,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中坚人物,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并屡作诗文讥讽,“新党”成员对之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因变法而引发的新旧党争,终于演变为一场殊死争斗。
苏东坡想不通,变法可以,为什么全然不顾社会的承受力?如果放慢点速度,整顿好人心,选用一批贤良,缓缓图之不是更稳妥、更容易收到实效吗?治理国家,难道就是发展经济这一件事吗?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大宋王朝求的是以文治国,这个传统丢了,国家会出大问题的。想不通,就频频上书劝阻,劝阻不成就联合起一批贤德人士共同抵制,同时,写到他的文章里,作诗讽刺。所以大难终于降临。
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向神宗皇帝上疏,指控苏轼诽谤新法,并进呈苏轼诗文,请神宗御览。神宗对此反应冷淡,只是将他的奏疏交给中书省去办理。事情久拖未决,苏轼毫发无损,令新党人物大为不快。恰在此时,刚到湖州的苏轼依照惯例上了一份《湖州到任谢上表》,里面有几句讥讽时政的言词,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感觉抓到了确凿证据,立即上疏,再次弹劾苏轼。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认为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宥”。监察御史舒亶手段最为毒辣,东坡的那些所谓的“反诗”就是他亲自摘录出来的。他还告诉皇上,苏东坡的那个“上谢表”如今已经是“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见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条)“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他说是“无不”,把问题推至极端。
王安石与这一切有无直接关系?关于荆公与诗案的关系,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政敌说。“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一○七九),而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也就是熙宁九年(一○七六)就离开政界了。那一年,王安石由于丧子的原因第二次罢相,去了江宁,最后连宰相都不干了。“诗案”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其时的宰相已是吕惠卿,怎能把“诗案”和王安石扯在一起呢?从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到“诗案”发生,已经十年过去,苏轼没有放弃对新法的批评,王安石一直不以为然,在他断断续续执政的八年内,苏轼可以畅所欲言,王安石一直未加干涉,怎么他当宰相的时候不办苏轼,退隐山林多年后却想到要报复苏东坡了?吕惠卿确实是王安石提拔的,但王安石当政时,吕与王的政见已然不同了,他当时不陷害苏轼怎么会在王安石远离政坛以后,反而秉从他的什么意志,替他清洗所谓的“政敌”呢?所以,“政敌说”于理不通。
其二,嫉妒说。说王安石是因为嫉妒对手的才华而下毒手的,这纯属想当然。王、苏二人虽政见不同,但在才情文学上他们二人相互欣赏。王安石曾称赞东坡:“子瞻,人中龙也”;在读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的东坡佳句时,抚几慨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东坡则称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相关的例子,在各自留传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历史上也从没有留下任何王安石嫉妒苏东坡的记载,更不会因嫉妒而生仇恨陷对方于死地,这绝不是半山的为人。所以,“嫉妒说”同样站不住脚。
其三,“小人”说。林语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把王安石称作“王安石那群小人”,的确,“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历来被视为王安石的“朋党”,王安石提拔的人、他的助手、学生和继承者,几乎都被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列入奸臣的行列,他本人虽没有被列入其中,但也是被骂了一千多年。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从政的文人。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点,都是奇才,唐宋八大家,他俩就占了两家;他俩都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富有同情心,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们各自的诗作中很多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俩政见不同,两人的关系也受到影响,逐渐疏远,最后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熙宁新法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讥讽,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苏东坡性情豪放,不拘小节,有时出口不让人,有时弄得王安石下不来台,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报复的事显然是有的。苏东坡半生颠沛流离,有一些就是王安石造成的。
客观地说,尽管王安石没有直接参与“乌台诗案”,但也不能说与他毫无关系,起码是他起用的那些人,有几个是贤德君子呢?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他表面上还尊重王安石,遵守他的教诲,但是他的私德、心胸、手段、志向,王安石怎么能担保呢?事实证明,正是李定,是这些小人制造了这个千古冤案。对此东坡的弟弟苏辙早就下过结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实际上,不仅李定,王安石、苏东坡、宋神宗,大家都有小人的倾向,表现就是不能容人,气量狭窄,个人意气用事,政见不同导致朋友都做不成。这样的事,所见所闻实在太多,古来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乌台诗案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系,但跟王安石本人无直接的关系。
此刻,苏东坡正被关在御史台的大狱里大受其罪。诗人的作品件件都成了事儿,被主审官抓住不放,审了又审。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终于使他支持不住了。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而这样的罪名一旦承认,就是死路一条,苏东坡不是不知道,但他没有其他的选择。而认罪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等着杀头了。就在苏东坡已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希望的时候,他把一些青金丹偷偷埋起来,准备一旦知道自己要被处死,就把它吞下去。他还跟儿子苏迈约好一件事:每天送饭的时候,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外面传要判我死刑,你就送鱼,不要送菜和肉。一天,苏迈外出筹集生活费用,就托了一位亲戚代为送饭。可是粗心大意的他临行前忘了交代一句:千万不要送鱼。正是无巧不成书,那位先生跟苏迈一样,也是个老实厚道之人,看苏迈天天不是菜就是肉,太过单调,于是就吩咐老婆做了一条鱼给苏轼送去了。苏先生一下子懵了——“我命休矣!”虽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苏轼还是感到如晴天响了一个霹雳。不就是几句诗吗,何致处以极刑?稍微镇定下来以后,他把狱卒梁成叫了过来:如有笔墨,可否借来一用?监狱里有规定,犯人不得接触笔墨,可是这个狱卒人很善良,同情苏轼的遭遇,平时很照顾苏轼,甚至每天晚上给他准备热水洗脚,不厌其烦。送笔墨对他来说小事一桩,但对苏轼来说却如雪中送炭。
东坡伏在案子上,就着牢房里昏暗的光线,提笔写了两首诗。其中有几句显然是写给他兄弟苏辙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这实际上是苏轼的绝命诗,表达的是他当时的那种极其悲愤、伤感的情绪。写好后,他把诗卷好,交给狱卒,嘱咐他收好,“这儿有小诗两首,请转交舍弟苏辙。”梁成答应:“一定转到,放心。”(见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苏轼为什么把绝命诗交给狱卒呢?苏迈天天来送饭,为什么不交给自己的儿子呢?分析当时的情势,苏迈拿到诗,马上会把它转交给自己的叔叔苏辙,让苏辙现在就看到诗稿,不是时候,除了让家人更加伤心,别的作用什么也起不了。所以,不能把诗稿交给苏迈。现在的情势看来自己难逃一死,临走之前有些身后事要跟自己的家人有个交代,还有一家大小十口的生活负担,看来只有交给苏辙了。苏轼知道狱卒拿到这个诗稿是不敢留在自己手里的,必定往上交。监狱长之类的官吏恐怕也不敢留,因为苏轼不是平常的犯人,如果这事谁都不敢做主,就有可能转到上层人物、甚至神宗的手里去。果然。苏轼的这一步走对了。诗最后还真的转到了宋神宗的手里。神宗看过后一时也很感动。
神宗本人并不大相信苏轼对他怀有二心,也十分赏识苏轼的才华,他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如果不是神宗对苏轼甚有好感,不欲深加治罪,一拖再拖,按照李定他们几个人的意见,早就把判他个“斩立决”了。神宗的犹豫不决让御史台的人很着急,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搏”。一天,宰相王珪面见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问:“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说,苏东坡的《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一句,这句诗大有问题。陛下请看,龙飞本在天上,苏轼却要在地下求什么蛰龙,还在九泉之下去求,这不是在诅咒皇上,要造反吗?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挑拨。在君权至上的社会,这样的罪名一旦坐实,是要灭族的。好在神宗还是个明白人,回答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旁边的章惇插言: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啊,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有“苟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么?说得王珪哑口无言。苏轼在毫不知情之间,又涉险渡过一关。章惇出来后,扭过头问王珪:“王相是要灭苏轼满门么?”王珪狡辩:“是舒亶说的。”章惇也没客气,啐了一口:“呸!舒亶的唾液也可以食么?”(见宋·王巩:《闻见近录》)
苏轼蒙难的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许多人勇敢地站出来,声援苏东坡。当时援救他的有下面几种人:一是同情苏轼的各界人士。从苏轼被捕的时候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向朝廷飞来。上至国家的宰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为东坡说话。
宰相吴充一次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宋·吕希哲:《吕氏杂录》)这话说出来甚冒风险,但对神宗的触动肯定不小。
尚书右丞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路遇谏官张璪。张璪知道王安礼在神宗心目中的分量,急切之下,竟不顾礼仪,焦急地冲着安礼嚷嚷:“公怎么不救他?怎么将他下死牢?”他,当然指的是苏轼。安礼觐见神宗,进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苏轼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为不能容人。愿陛下宽大为怀。”神宗说:“朕不想深罪他,召他对狱,考核是非,不久将放出。”随即又说:“在外面,不要泄露刚才的话。苏轼积怨太多,恐言官们因苏轼的事害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可见事情之复杂,连皇帝也有所怕。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专门负责调查、审问苏东坡的御史李定,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居然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周围竟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令他震惊的是,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说明了人心所向,是抗议,是舆论,也着实透着点儿官员群体的正义感。当苏轼蒙难时,杭州的父老百姓曾公开做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苏轼知道后,不禁老泪纵横。应该说,苏轼未被杀头,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
二是苏东坡的亲人们。苏辙写的《为兄轼下狱上书》最为感人,一开头就以呼天抢地的语气写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进而动之以手足之情:“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又明之其罪有可恕:“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如果能原谅苏轼这一回,我们再也不敢了:“轼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还表示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抵罪:“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样一篇哀婉动人的上书,朝廷竟置之不理。
三是神宗的祖母,也就是宋仁宗的皇后。当时这位太皇太后正病重,神宗为了促使祖母的病情好转,打算搞一次天下大赦,就把这个意思跟仁宗皇后说了。这里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老太太问:“据闻苏轼已下台狱?”神宗答:“是,自八月迄今,已有两月。”老太太说:“忆及汝祖父仁宗皇帝初得苏轼、苏辙之日,回宫喜容满面,曰:吾今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惜吾不及用也。”神宗听罢惶恐道:“娘娘勿忧,尚未定谳。”太皇太后长叹一声,轻声言道:“官家大赦可免,但放了苏轼足矣。”(宋·陈鹄:《耆旧续闻》)老太太一边说,还一边掉眼泪。这边神宗也跟着掉泪。当时不光是仁宗皇后老祖母,整个皇宫里的皇亲国戚们都很喜欢苏轼的诗文——特别是皇后、妃子、公主们。几日后,太皇太后终于一病不起。苏轼在狱中闻知心中大恸,作挽词两章以示哀悼。这时王安石已五十九岁,在退隐地金陵钟山也写了两首挽词,派人送到京城。
四是王安石,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位不凡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后早已退隐山林,回到江宁(今南京)隐居,所以没能及时知道苏东坡坐事入狱的消息,等到这场轰动朝廷的“乌台诗案”传到江宁时,苏东坡的罪名已定,只争一个迟早,晚一步,苏东坡的人头就可能落地。野史中的记载是,王安石忙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交给神宗皇帝,据说信中就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历来对王安石十分敬重,因为王安石是他的老师,虽然先生早已退隐,但在看了王安石的信之后,犹豫再三的宋神宗不再犹豫,马上下旨将苏东坡放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诏书中说:“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从诏书的用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是王安石的一句话最为奏效。在“乌台诗案”中,如果说别人起的是重要作用的话,王安石就是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性的一句话起了关键的作用。
前后持续了五个月的“乌台诗案”终于有了结果,苏轼被释放,但还是给他定了个罪名,叫“讥讽政事”,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并且不准擅离该地区,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流放了。除主犯苏轼外,其余如苏辙、司马光等二十九人,也受到株连。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出狱的时候,那个善良的狱卒梁成把他的绝命诗还给了苏轼。他接过来,一时百感交集,伏在案上边读边眼泪哗哗地流。苏轼经过这场磨难,性情上有很大改变,这以后我们见到的苏东坡,是成熟了的苏东坡——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孤寂潦倒之时,成熟于毁灭之后的再生。他去了黄州,在那里,伟大的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即诞生。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百六十多年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当然,与后世相比,特别是“康乾盛世”发动的无数次文字狱,乌台诗案算不了什么。那些历史上的浩劫,至今人们还可以嗅到溅落在康熙、乾隆龙袍上的血腥味。北宋帝王对知识分子是比较宽容的,这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阶段,最高统治者的精神素养的一种体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北宋文臣强势形成对皇权的一定监督,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商品经济的小康式的居民日常生活,都使得这个王朝显得别具一格,可惜以往人们对它关注和研究不够。
读这段历史,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两位文化巨人最后的握手言和。元丰七年(一○八四)七月的一天,苏轼专程拜访闲居江宁的荆公。史载,王安石闻听苏东坡要来,欣喜非常,穿着粗布衣服,骑着毛驴,到江边去迎接。苏东坡的衣着也颇为随便,冠巾也不戴,神情潇洒地走出船舱,向荆公深深作揖:“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半山老人笑答:“礼岂为我辈设哉!”(宋·朱弁:《曲洧旧闻》)言罢,两人相视哈哈大笑。东坡又说:“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王安石摆摆手,上前拉住东坡的衣袖,两人互相搀扶着踏上钟山小径。
这一次,苏东坡在江宁盘桓了一个多月,他们在半山花园里赏花饮酒,赋诗唱和,还携手同游蒋山(即钟山)。他们谈了许多,话题涉及古今的历史教训和当今的社会风气,与他们赋诗吟歌一样,坦率而融洽。尽管过去政见不同,但如今已时过境迁,两人都感到,夹杂着个人功名富贵而争荣政坛的往事,已如一缕青烟消逝,而现在,到了应该彻底解脱的时候了。这两位文名冠盖当世的唐、宋八大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终于尽捐前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诗情画意的精神境界里,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两位老人分手之际,安石送给东坡一张专治头痛的偏方,而且盛情对他发出了邀请,在适当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半山园附近,建几间草房,就搬过来住吧。东坡愉快地答应了。
见过王安石后,苏东坡曾写过四首“次荆公韵”,其中第三首有句:“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东坡集》卷十四)意思是说他很希望如王安石所劝,在南京定居,与他为邻,但世事悠悠,现在已然迟了。不过,从这句诗里我们体会出的正是他对王安石极为钦敬的表示。而半山老人也非常思念东坡,东坡走后,他感到惘然,有些失落。东坡的旷达潇洒,东坡的聪慧敏捷,东坡的率真豪爽,都令他思念不已。他逢人便提起他与东坡的相会,每当这时候,他就不胜感慨地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宋·蔡绦:《西清诗话》)这段历史佳话,也使王安石谋划迫害苏东坡的说法不攻自破。
以东坡之才之智,他是被谁加害的自有他自己的判断,这个人绝对不是王荆公,否则,王安石怎么会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救他?他又怎会巴巴的跑到江宁去看望王安石呢?
令人庆幸的是,两个伟大的文学家、诗人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文采风流,光照千古,动人的历史情景,直到现在还在激动着我们的心灵,为中华民族拥有这样两个具有伟大人格魅力和艺术才情的文化巨匠而深深地感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