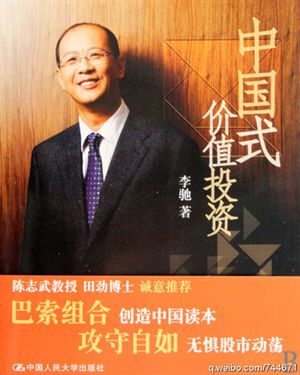批判胡适的“四条汉子”之罗尔纲
当批判胡适成为一种运动时,我们似乎也可以借助“更快、更远、更高”的标准,来考察一下这些“运动员”们。
反应神速、在第一时间就写出批判文章的,是周汝昌;扯得最远、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冯友兰;至于批判中站得最高的人,大概要算罗尔纲。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批判文章如何高屋建瓴,事实上这文章语言平和,批判起来也不疼不痒的。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这个一直对胡适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涕零的人,如今终于直起身来,站在胡适的上方,开始批判起自己的恩师。
漫天乱扯的文章,我们可以不关注——比如,冯友兰因美国和台湾妄图分裂祖国而更加痛恨胡适;又如候外庐批判胡适是混进“文化革命阵营中的大奸细”,像蒋介石一样想要篡夺“革命果实”。但是,对罗尔纲的批判文章,我们今天还是要加以分析,因为罗尔纲和胡适的关系实在太密切,毕竟他是胡适一生中最亲信的学生。所以,了解罗尔纲对胡适的态度,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反面来感受胡适——胡适如此器重罗尔纲,是不是看走眼、认错人了呢?如果说罗尔纲这个人就是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的话,那么这个乾嘉以后最大的考据大师是否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这个问题是残酷的。胡适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罗尔纲为“我的朋友”,在私人信件中称罗尔纲为“尔纲弟”,那么这个朋友、兄弟兼学生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是否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抛弃、背叛了胡适?对胡适来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重大的判断失误,又怎么让我们信服他的其他考证呢?
这样说似乎有点过分夸大和让人不堪,但是,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就得如此分析:如果你身边都是卖友背师的人,都是踩着别人的身体一步步往上爬的人,那你又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地位呢?
正是带着这种沉重的疑问,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胡适批判文集》的第二辑。在心里,我不愿意让我一向崇拜的胡适形象轰然倒塌,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还好,谢天谢地,我并没有面对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
在一堆充斥着“反革命”、“反动”、“腐朽”、“批判”字眼的标题中,我找到罗尔纲的文章,单从文字看,那是一个淳朴得无法让人相信的标题:《两个人生》。这篇批判文章混迹在一大堆充满政治性的漫骂文章里,实在显得有点另类甚至不伦不类。从文尾看,这篇文章写作于1955年1月,其时,批胡运动已经开展了较长时间,在这场“运动会”中,罗尔纲只算个中途入场者。
罗尔纲为什么在此刻匆匆赶来呢?是先前一直在暗自磨刀擦枪做准备活动,还是实在躲不过去不得已加入其中?由于缺乏更多的史料,我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只能在此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章内容来进行“大胆的假设”。
1955年1月,正是罗尔纲“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好时光。那时,他已经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权威,在南方各地办展览、鉴定革命文物,忙得不亦乐乎;在政治上,他不仅当选地方人大代表,还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颂扬,为他赢得了学术上的声誉和政治上的保险。所以,以他的身份,这次批胡运动大概是无法回避的。
不仅无法回避,而且还是个让人瞩目的“嘉宾”。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根本找不到第二个像罗尔纲那样和“苦主”胡适关系如此密切的人——让最被信任的学生罗尔纲批判作为学术界孔子(郭沫若语)的胡适,正如让以建立新儒学为己任的冯友兰出面批判古代的孔子一样,说服力是极为强大的。就这样,一直在场外转悠的罗尔纲,此时不由自主地走了进来——千呼万唤,舍你又其谁呢?
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和胡适最亲近的人,就是罗尔纲。他作为胡适喜爱的学生、工作中的助手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曾经长时间吃、住、生活在胡适的家里,如同一个亲密的家庭成员。另外,他写作的记录胡适言行、治学方法的《师们辱教记》(后来再版时胡适改名《师门五年记》),曾经十分流行,胡适到台湾后还印行此书作为礼品赠送他人。
慢慢腾腾走进会场的罗尔纲,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上来就扣动扳机猛烈扫射。这点,从他的批判文章《两个人生》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与其说这是一篇批判文章,还不如说它是罗尔纲的个人检讨书。我觉得,这文章从各个方面都应得到重视,尽管它看起来像个应景的命题作文,但字里行间所抒发的却是罗尔纲内心的感受,所以也是研究胡适的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字。
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叙述自己在1949年以前所中的两个毒,第二部分则是谈自己解放后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心得体会。对比以1949年为界线的前后两个人生阶段,罗尔纲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前一段人生受胡适的影响,脱离了政治,结果前途暗淡;后一段人生则因为“参加了政治,就有光明照耀着前进”。
那么,在1949年以前,给罗尔纲下毒的,究竟是哪两个家伙呢?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和匪夷所思,第一个偷偷摸摸跑到他身边使毒的,竟然是庄周!“那时侯,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罗尔纲说,“我选读了一门庄子课程,这一部反动哲学,就首先把我拖到幻灭的泥坑中去。”
正当不幸的罗尔纲在泥坑中挣扎时,他又遇见了更倒霉的事:胡适来到他身旁,下了第二个毒。“庄子给我毒,就是使我感到虚无,成为行尸走肉”,罗尔纲说道,“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
胡适贩卖的这让人“一言难尽”的毒,究竟都包含哪些成分?又都是些什么货色呢?嘟嘟囔囔的罗尔纲,只说出两个来:一是历史观,二是方法论。前者,胡适告诫他,写历史必须超越政治和阶级,要客观、不偏不倚。具体来说,就是写太平天国历史时,不能只说光明的一面,而要看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受了他的欺骗”,罗尔纲老实地承认道。
后者,具体说就是考证的方法。在这方面,胡适一直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关于这点,罗尔纲似乎也说不清楚究竟“毒”在何处,只是说“大胆假设”是唯心的,最后容易变成“大胆发挥”。他举例说,他自己在考证太平天国历法时,是先有了二十多条证据,才开始“大胆假设”的,言下之意,有可能胡适是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胆子就陡然大了起来。今天在我看来,这个毒也还算一般,充其量只是治学方法的不同而已。因为通常就是在证据不够的情形下,才需要假设。一旦证据多了,那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还假设什么呢?
这本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难道连胡适所看重的学生、长期研究历史的罗尔纲都不明白吗?显然不是,可他只好这么写,否则,还要批判胡适什么呢?胡适还有什么值得他罗尔纲批判的呢?把这个不算错误的“错误”拿出来胡批乱判一通,也正说明罗尔纲的无奈和不愿意面对批判的真实心态。
应该说,罗尔纲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很有可能是故意找些无关紧要的事来敷衍了事。我之所以这样“大胆的假设”,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只有空穴来风,我们才能捕风捉影。若这被“捉”到的影子又正契合我们所考察的对象,那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能下得了手批判胡适时,罗尔纲这样为自己辩解:他是在看了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要和胡适划清界线的文章后,才“豁然开朗”:既然儿子都可以批判老子,我这个做学生的,又有什么不能批判老师呢?
这段貌似合情合理的话,说得十分微妙,很值得玩味。
首先,我们可以解读出:罗尔纲自认向胡思杜学习批判胡适是错误的。罗尔纲在《胡适琐记》里记录了一个小故事:某天胡适夫人江冬秀和儿子外出,碰见有家办丧事的出殡队伍阻碍了交通,那小孩就对母亲说:将来你死了,我一定不这样办。江冬秀十分生气,回家就对罗尔纲抱怨。罗尔纲当即表示,小孩子这样跟母亲说话是不对的,自己要去批评教育他。在这里可以看出,罗尔纲显然是反对子女说长辈不好的。那么,后来胡思杜批判父亲的言论,罗尔纲按理也应该去反驳、教育才是,怎么能跟着当年的学生学坏呢?
其次,罗尔纲找的这个批胡理由,还反映出他那五味杂陈的心态。我们知道,父子可以反目,但是,那天然的关系总还是切不断的——罗尔纲是不是想借这个理由来说明,虽然学生批判了老师,但师生间的感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呢?
还有一点,罗尔纲是个读书人,他要给自己批判老师找个正当借口,完全可以更加冠冕堂皇。比如,梁启超看不惯康有为的做法,就有了著名的“谢本师”;章太炎不同意俞樾的那一套,也有一个“谢本师”。那么,以此来看,若是罗尔纲真的要和胡适割袍断义,他大概不会想不到这个故事吧。
当然,这些都是揣测之词,虽未必符合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真实想法,但多少对我们理解罗尔纲在批胡运动时的复杂心情有所帮助。人心虽然有顽固、不可动摇的成分积淀在深处,但终究是现实的折射,不可能不受现实的改造。拿罗尔纲来说,他在1949年后所进行的工作,无疑是和胡适的教导背道而驰的,他不仅违背了胡适的教诲,而且,还享受着这“背叛”所带来的政治待遇。这些,我想,对他内心深处长存的感恩之情,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
在文章里,罗尔纲大多数笔墨都在检讨自己的错误,即在解放前研究太平天国史时,“没能从原则上提到太平天国的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罗尔纲认为,这是胡适对他的毒害,是胡适让他既要看见太平天国光明的一面、也要看到其阴暗面所造成的。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太平天国的“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性质;也不去分析胡适所提出的写作历史要作到不偏不倚的观点。对这些,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普遍性结论。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罗尔纲是否真的与胡适分道扬镳,以及在此后的岁月里,罗尔纲是否完全走出胡适的影响,并在学术上超越他的老师。因为罗尔纲日后的发展、成就,直接关系到胡适的知人之明。
1930年,中国公学学生罗尔纲面临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和吴晗一样,也提笔给校长胡适写了封,请求帮助。
那年6月,罗尔纲搬到胡适家中,正式成为他的助手和家庭教师,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亲炙受教生涯。在这段时间里,胡适所教给他的,用罗尔纲自己的话说,是让他终身受用的“不苟且”,即一丝不苟、谨慎勤敏的治学精神。回顾起那段日子,罗尔纲饱含深情地说:“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怎叫我说得出自己的感情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可以看出,只比胡适小十岁的罗尔纲,是把胡适当作再生父母来看待的。所以,当后来胡思杜开始批判父亲后,罗尔纲也就毫不顾忌地跟进,道理似乎很简单:反正都是儿子,亲生的可以批,不是亲生的,怎么不可以呢?
在生活中,胡适对待罗尔纲,也的确令人感动。有一次罗尔纲从广西到北京来,因为不知确切火车时间,胡适竟然连续两天跑到火车站去迎接,就在罗尔纲到达的当天,胡适还在打电话问车站具体的车次。这份情感,就是放在60年后的今天,为人父母者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吧。对那种能够穿越时空的情感,我们有理由表达由衷的敬意。
在学术上,胡适的训练也让罗尔纲刻骨铭心。胡适是公认的开风气的考据大师,许多学术史的无头公案都由胡适发端而至脉络清晰,如《红楼梦》、《水浒传》和《六祖坛经》作者的考证,以及对《醒世姻缘传》的研究,这些学术活动都给罗尔纲极大的启发,因而,他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也是在胡适直接指导下,从考证入手的。
罗尔纲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清代文人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对此文给予严厉的批评。胡适认为,什么才算“好利”,清代文人是否普遍地形成此种风气,都是有争议性的,这个论题的提出,显然有先入为主之嫌,是不严谨的。此事让罗尔纲深刻地认识到,治史者可以做大胆的假设,但是决不能做无根据的概括性论断。
罗尔纲的学术生命十分漫长。1949年后,还延续50多年的时间。半个世纪以来,罗尔纲一直作为最权威的太平天国历史专家受到世人尊重,他的煌煌巨著《太平天国史》更是这一领域最全面、最重要的著作。可以说,罗尔纲的名字,是与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密不可分的。
那么,罗尔纲在这一领域的成就,是否完全脱离了胡适的影响呢?用罗尔纲自己的观点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条道路上,他完全背离了胡适当初给他树立的指路牌,走到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比如,他在《两个人生》里说“历史乃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这个立论前提就注定他只能写作太平天国光明的一面,而不去关注那些负面内容,显然,这就直接背弃了胡适要他客观考察历史事件的原则。
谷霁光在《太平天国史》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实质上是肯定还是否定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也是肯定还是否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革命的问题。罗尔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
在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太平天国的历史有可能被人为地、有目的地夸大、神化,无可讳言,在这个过程中出力最大的,就是罗尔纲。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罗尔纲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过程中,是否重蹈了当年胡适所批评的“概括性论断”的覆辙?“太平天国的反封建反侵略”与“清代文人的好利风气”,在议题上,难道性质不是一样的吗?
胡适曾经告戒罗尔纲:“文字不可轻做,太轻易了,容易流为‘滑’,流为‘苟且’。”对罗尔纲厚厚的四大本《太平天国史》,也许我们无法说这是“浮华”和“苟且”之作,因为里面毕竟有大量史料的整理、史实的订正和史事的发端,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部耗费罗尔纲毕生精力的研究成果,其实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一样,都是半卷著作,它所缺乏的半卷是显而易见的,即太平天国运动的另一面。
除了研究太平天国,罗尔纲还一直进行《水浒传》的考订工作。胡适是《水浒传》版本、作者研究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具有“开风气”的领先地位,罗尔纲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继承并发展了胡适的研究成果。1991年,罗尔纲考订的《水浒传原本》面市,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竟然公开宣称,其《水浒传》研究,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这不免让人好奇,这个和太平天国研究划上等号的人,不是在公然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吗?一部小说的重要性,难道超过那“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
不管怎样想,罗尔纲本人坚持认为自己最大的学术贡献,是搞清楚了《水浒传》的最初版本,即七十回本。这真的是有点突如其来和意想不到,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的宣传者,竟然在晚年又重新回到故纸堆,做起了铅黄校雠的学究营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应该相信罗尔纲的话,他把《水浒传》的版本排到太平天国前面,是他真实的反省和认识。从他的这个认知里,我仿佛又看到墓木已拱的胡适,他那祥和但一丝不苟的目光,正注视着已是风烛残年的罗尔纲。
回归到《水浒传》的罗尔纲,其实也就是重新站到胡适的桌前。白发苍苍的老学生,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回来了,这一次,胡适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成果呢?
胡适已走,哲人其萎。但我可以想见,若胡适地下有知,一定还会再度批评罗尔纲。
对罗尔纲而言,这是无法避免的难堪。“骓不逝兮奈若何?”在罗尔纲心中,始终有一匹跟着老主人不愿离开的马,这“马”的名字叫“反封建”,它一心一意要干的事,就是进行“农民革命”。罗尔纲把《水浒传》也定义为一部反封建、反压迫的作品,“是一部热烈歌颂农民起义,反抗官府到底的小说”。显然,在这里,政治因素先行的意味还是很强的。
今天我们纵观罗尔纲一生的两大研究重点:太平天国和《水浒传》,可以发现,他其实只是在炮制同一个标签——农民革命。是不是贴上这个标签,就永远地具备了免疫功能,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去他1949年以前所中的毒?
罗尔纲为什么如此钟爱“农民革命”这个标签呢?我们还得从他自身因素去找原因。
大约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罗尔纲这个人。在一本叫做“治学集”之类的书里,有罗尔纲写的自转性文章,大意是介绍自己如何开展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工作的。那文章很奇特,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去帮人家做抄写工作,然后这人家就指导他开展研究工作。文章中左一个“这人家”,右一个“这人家”,当时我就想,这既好心又博学的人家,究竟是谁呢?后来,又看到他写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才知道原来“这人家”就是胡适。
除了对“这人家”颇感好奇,我还对罗尔纲的哭印象深刻——总觉得这是个小心谨慎、内心柔弱的人。比如,在他写的纪念好友、同学吴晗的文章里,说见到吴晗的妹妹,忍不住流泪,见三面哭三次;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说在家乡见到解放军入城,也激动地流下热泪;此外,在阅读自己所写的《师门五年记》时,也流下“感激的泪”;在胡适差点遭到国民党阻击后午宴上,想到自己差点陪着胡适一起丧生,觉得对不起母亲,也流下伤心的泪水。
以罗尔纲如此敏感的神经,他在那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所受到的刺激,是可以想见的。想到这些,我们对他一直牢牢贴着“农民革命”标签的举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胡适是《水浒传》研究的开山祖师,设想一下,他若见到弟子所呈上的带着标签的研究成果,会怎样来批评罗尔纲呢?胡适是个宽厚的人,他也许会轻描淡写地问罗尔纲几个问题,比如啸傲山林的好汉,是怎么反封建的呢?绿林兄弟间的生死义气,算不算“封建”意识呢?排定座次的一百零八个好汉,有几个是先前是在家务农的本分农民呢,这些,罗尔纲回答得上来吗?
在《太平天国史》的自序中,罗尔纲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党教育我,栽培我,给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以最适合的环境和最好的条件,使我得尽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党给我的恩德,是终生感戴不尽的。”也许正是处于这样感恩的心,罗尔纲才不厌其烦地一再高高举起他的“农民革命”标签。
不过,无论如何,罗尔纲的通用标签,也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即他的一生都还是生活在胡适当年所给他的“毒”中,这个毒恐怕他无法彻底除去,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至死还牢牢贴着那些标签以求自保呢?再者,于人生暮年回归《水浒传》研究的罗尔纲,也清楚地表明,他的老迈之躯,其实又已回归到胡适的身旁,他犹如一支带着橡皮筋的箭,射得再远,也甩不开身后的起点,而且,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用了近50年的岁月,证明当初那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是徒劳无益的。
身在台湾的胡适,也没有“置身事外”,他一直在关注着罗尔纲。罗尔纲的批判文章发表后,他表示自己不相信那是罗的真心话,还把罗尔纲早年写的《师门五年记》当作礼品赠送给朋友。这个举动也表明,胡适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他始终认为罗尔纲是个值得信赖的学生。
1962年2月24日18时35分,胡适与世长辞。就在那天的中午,在午饭的时候,他还张罗着要把《师门五年记》送给吴健雄等人。可以说,在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罗尔纲还在他的身边。
罗尔纲是否对得起胡适如此的厚爱呢?判断不好随意妄下,我只能说,罗尔纲最后还是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一直是胡适的学生,至于这学生后半生的学术成果如何,为什么没能达到老师对他的期望,为什么没能比老师更有创建性,那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了。
写作参考:
1.《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一版
2.《困学集》,罗尔纲著,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一版
3.《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罗尔纲著,三联书店1958年5月第一版
4.《太平天国史》,罗尔纲著,2000年11月第一版
5.《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6.《胡适传》,白吉庵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7.《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三联书店1955年1月第一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