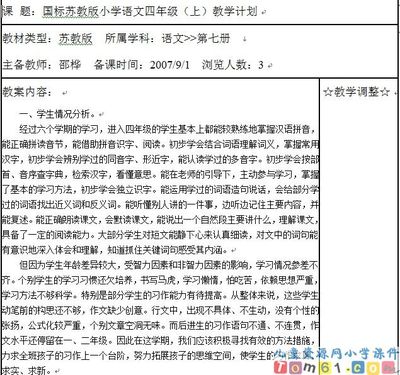这个案件是大头对我讲的。他是我居住辖区的公安分局刑警。他在对我讲述这一案件之前,先说了一句类似开场白的话——不要以为奇异的故事只能发生在戏剧里。实际情况是,不管我们的现实生活多么平庸而沉闷,但是它所缺少的从来也不是戏剧性。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只能说明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太迟钝太粗浅。他的这番话使得整个叙述在开头时候便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事情应该发生在那天黄昏,差不多就是电视节目播放到新闻联播那个时候。因为恐怖总是发生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而一天当中只有这个时间人们精力最不集中。就在这个万家灯火相继点燃的时候,有一个居住在城市郊区的菜农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菜农只是个传统称呼,其实这个人早已不再操持种菜的营生了。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像许多从前的菜农一样,已失去了可以耕种的土地,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靠出租住房为生,也就是说他准确的身份应该叫房东。这个房东对派出所值班民警称,正当其它人们都在手忙脚乱地做着晚饭的时候,他的一个房客也在手忙脚乱地大锅煮着什么东西。他之所以知道这个房客在煮着东西,不是看到而是闻到的。当时他因为其它事情偶然经过此人屋外,他闻到了从虚掩的屋门里弥漫出来的一种浓厚气息,就如煮着大块肥肉的锅揭开锅盖时的味道一样。因为这个房客租他房子很长时间了,彼此熟悉得就像一家人似的,他便停住脚步想开对方这样一个玩笑——吃什么好东西呢,关在屋里背着人吃?但是就在他正想推门而入的刹那间,他感到自己整个人变得僵硬了。这个房东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蓦然睁大了,脸色变得死人一样苍白。他的这种恐惧表情无形之中渲染了事件的氛围,使得听他讲述的值班民警都不由自主紧张起来。他说,他从门缝里看到,正在滚沸的大锅里上下翻动的,不是一块猪肉,而是一颗人头。
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城市包括警方在内的所有的人们,都将私人出租房视做藏污纳垢之地,在这些拐弯抹角的地方隐匿着各种各样出处不明的人,从事着各种各样伤天害理的活动,大部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都发生在这种暧昧之处。因此这个报案房东的话没说完,警方就已经将事情往最坏处想。他们毫不迟疑围困了这幢恐怖的宅子。当这些持枪大汉不容分说破门而入的时候,被疑犯罪的房客丁某正在屋后仓促堀坑,企图将那颗已经皮开肉绽的人头掩埋掉。

刑警大头是在后来介入这个案件的,他在分局拘留所里见到丁某的时候,这个煮了不该煮的东西的人已被收审了一个月之久。收审丁某的派出所此前已对其进行过多次审问,从这些审讯记录中大头得知了此人大致的来龙去脉。这个丁某是多年前从一个山区小城来到这座省会城市的,之所以来此是因为他考取了这个城市的美术学院。还在这所闻名遐迩的学院就读期间,这个面目表情很像名为《思想者》雕像的人,便有多幅作品在各种名目美展中获奖,被认为是他那一届学生中最有希望混成专业画家的人,他自己对此也满怀信心。然而临毕业时事情发生了出其不意的变化,原来答应接受他的省画院突然改了主意,接受了他的一个画得狗屁不是的同学,而他则被分到了某电影院,成了一个给即将上映的电影画广告的人。这个抓瞎了的人一怒之下没有去单位报道,但是也没有回他的老家。他在城市边缘租赁了一间民房,也就是他在里面大锅煮人头的那间房子,开始了他自称的流浪艺术家生涯。据这间房子的房东说,这人刚来时候还像个正儿八经画画儿的,但是画着画着便越来越不着趟儿了,最后索性把画画儿的材料全扔了,开始改用乱七八糟的垃圾做材料,拼凑出各种各样不知所云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不叫作品叫装置,把自己也不再叫做艺术家而改叫了前卫艺术家。大头对前卫艺术家这个称呼不是很明白,不过在此之前他认识一个作家,最初也是写正儿八经小说的,写着写着也把自己写不正常了,开始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解构成一二三四五六个情节段,只写一三五不写二四六,故意让人搞不清楚支离破碎的情节之间的关系,那个人的作家称呼也由此多了三个字的前置定语,叫做了先锋派作家。想必这个前卫艺术家的情况也跟那个先锋派作家差不多。大头说正是由这个前卫艺术家这儿,本案出现了第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面对这颗已经被处理得面目全非的人头,这个被捉了现行的人的辩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坚持声称他不是行凶而是创作,他正在为一个前卫艺术展制作一件新的装置,出于表现需要他为这个装置选择的材料是骷髅,就像他的其它装置选择了其它垃圾做材料一样。他烹煮和掩埋这颗人头的目的,并不像人们怀疑的那样意图隐匿或销毁什么,而是为了使头颅和皮肉之间尽快脱离关系。至于这颗人头的来历他的说法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他说此物并非他从某种完整生活的东西上擅自割取下来的,而是另一个以拾破烂儿为生的姓马的房客卖给他的。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所以鬼鬼祟祟,按着审讯记录中他的原话,完全是“为了避逸不必要的麻烦”。
由于大头是在后来介入这个案子的,所以他第一次见到马某时,这个卖了不该卖的东西的人也已被关押一个月之久了。据说捉拿这个马某的时候稍费了一些周折。此人虽在丁某隔壁租着一间房子,但是日常在此居住的却只有他的老婆和孩子,而他本人则由于打着拾破烂儿旗号干着偷鸡摸狗勾当,时常夜不归宿去向不明,派出所方面整整埋伏了三天三夜,才好不容将这个行踪不定之人等了回来。而这个人被抓获的时候,身上还背着刚刚乘人不备从某辆汽车上拆卸下来的蓄电池。
大头是在分局拘留所办公室里提审马某的。很可能是被关押的时间太久了,这个人的精神已经发生了崩溃。因此还没等刑警对他施加审讯压力,便哆哆嗦嗦地把该说的都说了。该马原系郊县某村农民,一年前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携带已孕老婆和女儿流窜到这个城市,租赁了目前这间房屋住了下来。这次移居原计划是临时性质的,不料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者这次老婆又为他生了个女的,气得他索性决定甩开了继续生下去;二者城市为人们提供了许多不劳而获的机会,在这里混得再秕也比在农村混得好的吃肉多。于是将暂住改成了长住。对于涉及到他的那颗神秘人头,该马不待大头询问便主动交代道:“姓丁的说得不假,人头是我卖给他的。”毫不隐讳的态度令刑警都深感意外。这个对城市许多东西都感到困惑的人,对他的邻居丁某的许多行径也感到困惑,一直搞不清此人——用他的话说——吃哪一路的。他是个拾破烂儿的人,光顾这个名儿就可以思义,他所拾拣的都是这个城市的弃物,这里面包括碎玻璃、废铜铁、破铺衬、烂袜子、旧家具、臭骨头等等,总之都是些只有苍蝇才会喜闻乐见的东西,若不是好几口人等着他朝家里背面就连他都要躲得远远的。可是没想到姓齐的偏偏对这些人见人恶的东西如获至宝,经常以超过废品收购站几倍的价钱买了去,东拼西凑地鼓捣成一堆儿,还取了个名字叫“装置”,弄得明白人知道他屋里是住人的,不明白的人都会误认为那是一个垃圾箱,这使得他一直怀疑对方患有某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不过由于这里面牵涉着钱,他不仅没有建议对方去看病,反而推波助澜地特别注意在垃圾箱里翻找各种古怪物事儿,主动兜售给这个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越来越密切,最后终于发展到了开始发生这样的事儿,就是姓丁的需要某种特殊垃圾,而姓马的手里一时没有这样的东西,对方便以更大的价钱雇用他想方设法搜罗来。譬如这次,就是丁某将一张大钱塞进他手里,问他:“你能不能帮我弄一颗人头?”
马某是这样对大头解释的,他本来不想卷进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中来。因为这次丁某人想要的可不是什么弃物,而是谁都不会白白送人的东西,除非你从别人肩膀上硬夺过来。可是由于他从对方塞过来的钱上认出了四张熟悉的面孔,这使得他到了嘴边的不字说了几次都没说出口。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他可不愿意因为一句话便得罪这么多老熟人。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拾破烂儿的马某竟然真的不知从哪儿割来了一颗人头。而在此之前,他也是这样对收审他的派出所解释的。大头说当时人们听了这个解释,几乎立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抓获了一名故意杀人犯。然而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事实很快推翻了他们的这一结论。也就是说,案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令所有人们冷不防的向后转。拾破烂儿的马某在承认割取了这颗人头之后,接着交代了这次割取的时间、地点和对象,没有一个人想象得到,这次割取不是发生在活人身上,而是发生在死人身上。
大头从马某那儿所得到的东西,与派出所此前对他的提审记录一模一样。
牛结实死后被埋葬在了村外坟地里。就像广播电视讣告里常说的,他是“因病医治无效”而死的,“终年”还不到二十八岁。据他的左邻右舍们说,他先是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猛一看上去就仿佛得了什么病;继而萎靡不振,苦不堪言,给人的感觉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突然有一天便上吐下泻,高烧昏迷,被人们送进医院后诊断为了肝癌。肝癌这种病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不到要命的时候轻易发现不了,而一旦发现便已到了要命的地步。所以从医院回来没几天,这个年纪轻轻的人就像俗话常说的交了面本。按说这个村子只是理论上还叫村子,事实上早已成了城市一部分,适用于城市人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这里人,这里人死后应该像城市人那样送去火葬才是。然而实际情况却正相反,已经被其它人称为城市人的这里人,自己却从未将自己视做过城市人,当然也从不按着城市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谁死了都坚决不让火葬场挣到他的钱。对于牛结实自然也不例外。尽管这是个没爹没娘没家没小的人,这里人仍然将其送到了他们过去送人的老地方。这里人管送人不叫送人叫出殡,由此可见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大事情,自然而然具有相当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所以临时居住在这里的拾破烂的马某毫不费力地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而这时,他的邻居丁某所说的那句话的余音还在耳边缭绕:“你能不能帮我弄一颗人头?”刑警大头说,案情发展到这里起码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是这颗来历不明的人头的归属问题,它属于,至少曾经属于一个叫做牛结实的人。
大头来到这片坟地时,牛结实的坟墓里已经空空如也,除了头颅已被马某割走,身体也已在案发后被派出所掘出,送进了医院停尸房的冷冻柜。这是一片古木森然的坟地,大头说关于这个地方有着很多耸人听闻的传说。其中最为流行的传说是,经常有夜行人经过这里突然迷失了方向,犹如误入了某种精心设置的陷阱一般,无论怎么转都转不出去,直到村里鸡叫天色微明时,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走进了坟地,整个夜晚实际上始终是在乱坟荒冢中转来转去。所以天黑以后附近很少有人敢到这儿来。也就是说起码在传说中这是个闹鬼的地方。这个刑警说他一看到这地方便不由地想,当拾破烂儿的马某在某个黑灯瞎火的深夜,一个人窜进这片神出鬼没之地,寻找并掘开其中的一堆新坟,从中攫取那颗面目仍若生时的人头时,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如果不是拾破烂儿这样的彻底的无产者,换了任何人不把胆吓得找不着才怪了。别说给我一百块钱,大头说就是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不会干。
最早承办此案的派出所掘出牛结实的残尸后,将验尸工作委托给了辖区内的一家肿瘤医院。按理说验尸这种事情应当找法医,他们才是法定的这种工作者,但是派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头解释说主要是案情发展到这一步,给人的感觉是已经真相大白了,也就是说派出所已经准备就此结案了,他们只需要落实一下牛结实确实死于肝癌就行了,这种小事儿就没有必要再麻烦法医了。然而这家医院对尸体的解剖结果令所有人都感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解剖发现牛结实的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肝其实没有任何问题,正相反这是一只非常完好而正常的肝,此前人们对它的诊断完全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致死这个人的其实并不是肝癌。解剖还发现牛结实的其它器官也都十分完好和正常,没有任何哪怕微乎其微的缺陷和毛病。也就是说这个人也不可能死于其他任何疾病。总而言之这个叫牛结实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结实,如果不是他确实死了绝对没有人会将他和死字联想到一起。这一重大发现一下子令所有人都傻脸了。因为这意味着本案又一次峰回路转,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就像夜行人进入了鬼祟设置的怎么转也转不出来的迷宫。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本案对警方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却又必须解答的难题——既然牛结实不是疾病死亡,这一时期又没出什么意外事故,而他这种年纪又不可能无疾而终,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他杀。也就是说,很可能有人采取某种不易觉察的手段谋杀了这个叫牛结实的人,而在此之前恰巧该牛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比较合理的推测是遇到了某种不顺心事儿,生理和心理上表现为“面黄肌瘦”、“萎靡不振”,给人的感觉“就仿佛得了什么病”,庸医又将此误诊做了不治之症肝癌,使得人们理所当然地将他的死认作了自然死亡,而忽略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杀人的人。当时办案的派出所得出这个推论之后认为可能性很大。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最可能的。
至于是谁杀了牛结实,派出所方面认为这个问题更简单,当然是跟姓牛的特别过不去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当即动员了全部警力,在牛结实的生活范围内展开了大海捞针式的筛查工作,从茫茫人海中寻找着这个可能跟该牛有过节的人。令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工作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仅从这个姓牛的人的身边,他们便找到了一批可能杀人的人。面前的这些笔录,来自这个村子的部分村民。用这些人的话说,牛结实是他们看着长大的,他们至今都还记得这孩儿过去的劣行。牛结实是村里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收养的,正因为俩老人都觉着这孩儿来之不易,自小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口里怕化了,仅从给他取的名字便可见他们所怀抱的期望何等之大,这使得孩儿人还没有长大却成了有名儿的厉害角色,摔盆掼碗打爹骂娘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没几天便将收养他的人活活气死了。这些人论起来都是这老两口的拐弯儿亲戚,换言之也等于是牛结实的拐弯儿亲戚,可是自从老两口死后他们便再也没有搭理过他,就好像大家从来不曾认识过这么个人。而且正因为他们都与俩老人沾亲带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只要话题一涉及这个孽种仍然恨得什么似的,无不咬牙切齿道:“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小王八蛋总有一天会叫雷劈了!”
一份笔录来自这个村子的村长。因为村里人都姓牛,所以这个村长也姓牛。这个姓牛的村长说,正因为牛结实也姓牛,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想再姓这个牛字了。就在那段时间这个村子里多了这么个人,吃馆子赖账,借人钱不还,对癞子骂疮,对秃子骂光,拆人一座屋,自得一条梁,夜踢寡妇门,日扒绝户坟,总之凡是人所不齿的事情没有他不干的,久而久之全村人见了他没有一个不躲着走,此人非他正是长大成人了的牛结实,牛村长说跟这种人姓一个姓简直就是耻辱。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一村之长一直将该牛视做眼中钉肉中刺,一天几次到派出所扇他底火垫他黑砖,试图假公家之手将这个公害清除掉。可是这个人就像俗话常说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今天撺了进去明天又放了出来,而且一看就连王法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反而越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将村子和搅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气得这个村长不止一次指天指地道:“总有一天我拼着村长不干了,也要把这个狗丅日的拾掇了!”
一份笔录来自小酒馆牛老板。这是一家位于村口的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酒馆,也就是俗话常说的那种小本生意,因而门口赫然贴了八个醒目大字,“小本生意概不赊账”。牛老板说他写这几个字主要是为了对付两种人,一个是村干部,另一个就是牛结实。自从这摊儿小生意开张那天起,牛结实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一天三顿饭除了早晨睡懒觉其它都在这儿吃,可是开酒馆的人却从来没见过他一分钱,什么时候要都说先记着,要急了就索性给你来个要钱没有要血有一盆。牛老板不止一次试图将这个人拒之门外,但事实证明这么做根本行不通,你敢说不让他进门他就敢把屎拉在你门口,将一个吃饭的地方弄得比公共厕所还要臭,薰得人们远远的便捏着鼻子绕道走。到后来牛老板干脆不再往账本上写牛结实这个名字,任他甩开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这个村里的人们都知道,很长时间以来只要牛结实一进酒馆的门,这个牛老板的眼睛就比兔子还要红:“哪天真把我逼急了,我不在他酒里下包毒药我不是人!”
一份笔录来自一个齐姓女子。人们只是从姓氏上知道这个女子不是本村人,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她是什么地方人,长期以来她一直在这个村中租房居住,夜晚进城到歌厅里去做三陪女。正是这种人在他乡无依无靠的身份,使得她饱受地痞牛结实的欺辱和讹诈。有俗话道“砸不砸要饭碗,坑不坑婊子钱”,但是这一原则完全不适用于牛结实。自从该牛得知她从事着无法见人的职业,先是伺机强奸抢劫了她,之后动辄破门而入,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并搜走她的卖身钱,稍有不从便拳脚相加大打出手,至今她身上仍然到处都是对方烟头留下的疤痕。当讯问她的派出所警员问及为什么不报警,得到的回答是一者她的营生不可告人,二者她连暂住证都没有办,真把事情闹大了被撺进去的还不知道是谁呢。“我们这种人,谁也不能靠,只能靠自己。”由于她夜晚上班白天睡觉,对外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至今还不知道姓牛的人头已经被人卸过了。
一份笔录来自一位村里老汉。这是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他的所有不幸都来自不慎生养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自从几年前牛结实看上这个女儿后,老汉就再也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该牛既然被人们公认为是个无赖,他对女人的追求当然也是无赖式的。他先是红头蝇子见了血似的,一天到晚跟在女孩儿身后,人家去哪儿他去哪儿,撵得对方想躲都没处躲。接着手持镰刀将人堵在路上,威胁对方若不答应就喷她一身血,遭到拒绝之后手起刀落将肚子豁开一个大口子,果真将对面之人溅染成了血人。最后干脆当众放出话来,对方倘若再说半个不字,他就吊死在她家房檐下,让她全家都吃不了兜着走。而依据他连自己肚子都敢动铁器的一贯作风,没有人怀疑他说得出就做得到。对于该牛的无赖行径是个人都气得吹猪似的,然而他们干生气可就是没办法,因为此人自始至终都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并没有碰别人哪怕一根手指头。有俗话道好鞋不踩臭屎,最后老汉为了不把这恶人放进门来,索性决定彻底死了他的心,牙一咬心一横用硫酸破了女儿的相。这个老汉后来得到该牛死讯时,像个孩子也似呜地哭出了声,边哭边喊:“老天爷真是有眼哪!”
所有这些讯问笔录大头后来都看了。这个刑警读完这些控诉性质的答问后独自愣了好半天。在此之前他对牛结实的全部认识就是一具无头尸体,他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个一动不动的死人,竟曾做过那么多得罪人的事儿,惹得是个人都吵吵着恨不能亲手杀了他,而且这里面不管是谁最后下毒手,人们都不会感到大惊小怪。总之所有这些文字最终都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一个人一旦活到这份儿上,被人杀了只是迟早的事儿。大头说这印象就像一个无可辩驳的论据,大声论证了办案派出所所提出的他杀论点,而他们正是被这个论证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对牛结实的第二次验尸工作。验尸仍然是在肿瘤医院的手术台上进行的,但是因为已经牵涉到了凶杀,站在手术台前的不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而换了分局法医室的法医。验尸结果出来得比人们预想的快得多。谁也没想到这是一个与人们的推理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尸体表面无搏斗和暴力痕迹,也就是说该牛不是死于伤害;呼吸系统无窒息和溺水现象,也就是说该牛不是死于扼杀和溺杀;血液和胃内容物中未检出毒物成份,也就是说该牛不是死于中毒。上述一切在这份法医鉴定的最后被归纳为一句话——可以排除他杀。
大头就是在这时候介入此案的。事实上调查进行到这里,整个案件已经陷入了僵局。最早承办此案的派出所反复考虑之后,觉得已经没有能力再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便将案件汇报给了他们所在的公安分局。分局当家儿的几个人研究了案情之后,觉得尽管此案十分离奇,然而整个案件发展到这里,也仅仅看着像是一起由毁尸案引出的案中案,但到底是不是还得两说着,也有可能到最后什么都不是,故未予以更多的重视,只是派了刑警大头协助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此案以示支持。就这样大头成了这个故事的当事人。
尽管没有从分局争取到更多支持,大头的到来仍使垂头丧气的派出所不由得猛一振奋,仿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听说了一种新研制的特效药。原因是这个大头虽然其貌不扬,在刑警行当里却很有些小名头,许多别人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得绝望了的案子,被他也不知怎么一鼓捣竟然都破了。派出所方面此前虽末与这人共过事儿,但对其名字却早已听得耳朵起了茧子,一直在心中将之视为小说里的那种神探。本来一听说此人要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大家都觉得救活这桩死案有希望了,不约而同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谁知现实却很快告诉人们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当被寄予厚望的这个神探真的进入到事件中,大家对他的这种信心反而发生了动摇,甚至情不自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是人们传说的那个大头么?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能够创造性劳动的思想者,而更像是一个从事事务性工作的熟练工。人们看到他的调查是从头开始的,就像对一本书的阅读是从这本书的第一页开始的一样。他先是详细审问前卫艺术家丁某和拾破烂儿的马某,落实了引发案情的人头的具体出处,以及谁是这颗头颅的合法所有人;接着反复走访了第一次解剖牛结实尸体的肿瘤医院,核对了该牛死前确实正常完好,有关他死于肝癌的说法纯属庸医误诊和人们误传;最后认真翻阅了法医验尸报告和对村民的讯问笔录,证明了有许多人都想除掉这个姓牛的,但是姓牛的人的死亡形式又不是他杀。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是那么的不厌其详和不遗余力,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就像一个从前往后死记硬背的读书人,不肯漏掉书中的任何一个字一样。但是他的这种对工作的忘我精神和负责态度,不仅没有赢得人们的认同和赞赏,反而使人更加感到了他的平庸无奇和碌碌无为。因为他辛辛苦苦所做的这一切,人们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做过了,他现在只不过将人们做过的事情又重做了一遍。而人们当初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故而他此刻的所有努力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在做着无用功,就像俗话形容的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这与人们想象中的神探形象错位太多了。总之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看到他们所期待的奇迹,这使得他们的情绪中不由地掺杂了失落和失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