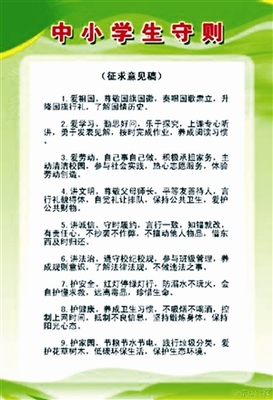我的学生吴丹红
吴丹红是我的学生。近日有记者越洋采访,关于他的,我才知道他又出事了。与记者的谈话勾起了我的回忆,于是我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想法。
我喜欢在小说中写人,虚构的,但我很少为真人撰文。在记忆中,我只专门写过三个人。一个是著名美籍华人李昌钰。我应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贾京平的邀约,半推半就地接下任务,写成了一本书,名字是《犯罪鉴识大师李昌钰》,1998年出版。不过,那本书主要讲的是李博士查办的案件。由于我在1985年的人民大学物证技术暑期班上听过李博士的讲课,所以他至少算我的半个老师。我后来撰文写过的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一个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徐立根教授,一个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乔恩·华尔兹教授。不过,那两篇文章都有哀悼的意思。我没有专门写过我的学生,但是在学生专著的序文中往往也有些写人的文字。数年前,吴丹红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的师父何家弘”,因此我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丹红那篇文章的回应吧。
我不愿意写真人,主要是怕写不准,因为我有时看得就不准。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是我的好友。他就喜欢写真人,因为他爱好摄影,包括人物特写,擅长捕捉人物特征,看人就很准。他曾经专程给我拍照,挎着很专业的相机,还有跟班儿的,举着一块大白板,老站在我的身边。我开始很纳闷儿,你又不是我的跟班儿,干嘛老站在我的身边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反光板,给我增添光彩的。平心而论,那组照片确实拍得很有水平。我现在做课件和出书用的多是他给我拍的照片。卫平没有跟我谈过著作权的问题,我也没有跟他谈过肖像权的问题。君子之交淡如水,自然与孔方兄无关。卫平很幽默,但他讲笑话时自己绝对不笑。他一般只在别人吹捧他的时候才笑,很甜蜜的那种。我就经常看到,因为我经常吹捧他。当我的话语偶尔另有寓意时,他的笑容就会停滞在一个神秘的位置,很像蒙娜丽莎。
假如我这篇文章就此收笔,那肯定是跑题了。但是我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当然不会跑题,至多是思想开个小差。用文学专业的话说,我这叫“意识流”。丹红也喜欢照相,但是从装备到技术都与卫平教授相差甚远。他在那篇文章中配了我的一张照片,是他在欧洲给我拍的,水平就很一般,没有能够展现我的风采。我们不远万里去欧洲拍照,也不能就那个水平吧!读者英明,笔者绕了一个大圈子,这句话才是我想说的。
第一次见到吴丹红的名字大约是在2001年的冬季。我收到一封电邮,写者自称是中南政法大学的学生,报考了我的博士生,希望能有机会,署名是吴丹红。当时,我还以为是个女生。我像对待其他考生一样,回信表示欢迎并祝心想事成。后来成绩出来,吴丹红名列前茅,我也知道了他的性别。那年阳盛阴衰,前三甲都是男生。另外两人是刘为军和蒋胜杰,前者现在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刑侦教研室主任,并在北京市一分检挂职担任侦监处副处长;后者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某大队的政委。那年我还录取了一个不占名额的澳门博士生,也是男生,叫周伟光,现在是澳门司法警察局的副局长。2002年冬天中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主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应杨宗辉院长的邀请,我带着部分博士生去参会,有他们四人,还有前两级的男生,站在一起,我自己也感觉雄赳赳的。特别说明,本人在录取博士生的问题上绝没有性别歧视。后来有一年,我一下子招收了四朵金花,包括一个不占名额的台湾女生。我给自己定的录取规矩是只看成绩。不过,我的心里也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就说吴丹红他们那年,本来我心里倾向于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张方,很有专业水平,而且考了两年;一个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罗亚平,刑事技术专业的后起之秀,李昌钰博士还曾表示愿意就她考博一事给我打个招呼;一个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应届硕士生房保国,发表过文章,而且专门以“与何老师对话”的文体写了一本关于沉默权问题的专著。但是成绩出来,这三人没能进入前三名。不过,这也是塞翁失马的事情。张方很快晋升为教授,还担任过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罗亚平后来师从公安系统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刘耀教授攻读博士,也晋升为教授,还担任了公安大学刑事技术系的主任。房保国考上了北大陈瑞华教授的博士生,毕业后又转回我这里做了博士后,目前是丹红的同事,大概也算得上“五子登科”之人了。
在我的学生中,丹红不能算最聪明的,但肯定是最勤奋的,而且他很有主见,勇于挑战自我。从翻译学术专著到撰写学术论文,他总能出色完成任务。当时我主持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后来出了本专著,我是主编。其实,主要的研究是他做的,主要的章节也是他写的,此事有书为证。他涉足网络较早,便主动提出为我们的证据学研究所创立一个网站。我在电子网络上比较愚钝,整不太明白,就说你做吧。于是他一人连续作业二十多个小时,竟然弄出来一个“中国证据法网”!
当时,我感觉丹红的口才并不太好,不像有些学生那么健谈。其实,我这个人的口才也不太好,与人聊天经常无话可说,别人也感觉我有些木讷。不过,丹红敢于补拙。2003年暑假,我们与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联合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召开了“全国刑事审判认证研讨会”。我主持研讨,便安排几位学生做主题发言。开始,丹红有些发憷,因为与会者除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外,就是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庭长,一百多人,阵势挺大。不过,他后来还是承担了任务,发言的效果也不错。

丹红在与人交往上似乎不够圆滑,有些书生气,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好像与同学们有些隔阂。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学生们在我面前只说学习不谈生活。2004年5月,我带着一些学生去欧洲考察,因为我主持了一个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研究。我们一行9人访问了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法学院、建在海牙的一些欧盟组织机构和瑞典的最高检察署。
首站荷兰,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租了两辆旅行轿车,我开一辆,我的博士生姚永吉开一辆,他曾在欧洲学习过。我们住在海牙市郊离海边不远的一家假日酒店,同食同宿,很有一家人的感觉。我亲自开车,有时一天七八个小时,譬如去比利时的布鲁日和德国的科隆,学生们自然有些不忍,便经常在车上给我讲些个人的笑话,也讲到过丹红。
第二站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们住在一家青年旅馆,可以自己做饭,大家格外快乐。第一天晚饭后,我回屋休息。过了一会,丹红过来找我,样子有些郁闷。除了我之外,还有3名女生和5名男生。他说,那四个男生都出去了,就把他甩在了家里,一个人洗碗。后来我得知,因为第二天要准时去最高检察署,他们怕找不准路,就先去探路,估计也是年轻人想出去玩玩。我和丹红聊了一阵子,谈了做学问与做人的心得,鼓励他多与同学交流,增进友谊,加强融和。后来,我感觉他和多数同学的关系还是挺好的。毕业时,他结婚了,许多同学都参加了他的婚宴,我也去了,还以“家长”的身份致辞祝福。
丹红毕业后,去北京大学做了陈瑞华教授的博士后。房保国过来,吴丹红过去,就好像我和瑞华教授有学生交换协议似的。然后,丹红去了台湾、深圳,出站后到政法大学工作,我也是鼎力推荐的。这些年,他还会参加我主持的一些学术活动,逢年过节也会来看看或通个电话。我一般会对同学说,你们都很忙,没有特别的事情就不要来看我。我夫人曾为此责备我,你老这么说,就好像你不欢迎学生来似的。后来我发现,有的学生打电话,一听是我,问候之后就马上说,师母在家吗。学生们喜欢和师母聊天,特别是女生。其实,我也挺想念学生的,就是不说。
这些年,丹红挺有成就。我看过他写的几篇关于证据法学的论文,很不错。我也为他出版的学术著作写过序。他在网络上的活动,我有所耳闻,并听说他有时还会制造一些故事,但并不了解详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我以为,丹红属于网络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我自己却跟不上网络发展的节奏。我记得,丹红很早就建议我在网上开个博客,但是我一直犹豫推脱。后来我终于开了,人家又都去微博了。我也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丹红,好像是凤凰卫视。我感觉他成熟了,老练了。但是,我不太关注网络热点事件,对于他的一些言论也不甚知晓。这次“微博约架”,我也是听记者说的,感到很惊讶,似乎不像他的行为。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走下去吧,只要是自己的追求。
我曾经对学生们说,今天你们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讲,你们是何家弘的学生,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也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讲,我是某某某的老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数年前,我参加电子证据取证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与会者中有许多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虽然我主持过电子证据研究课题,但那实际上主要是我的学生刘品新博士完成的。我坐在前排,桌子上有名签。我听见,背后有人小声问,这个何家弘是哪儿的;有人答,他是刘品新的老师。现在,肯定也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而回答大概就是:他是吴丹红的老师。至于人们接下来会说什么,我就不去想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