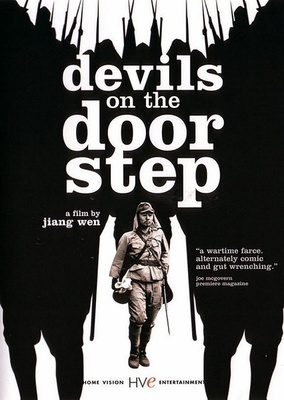孤独的皮格马利翁
——萧伯纳的Pygmalion《卖花女》
剧名:Pygmalion(《皮格马利翁》)
地点:Garrick theatre in WestEnd(伦敦西区加里克剧院)
时间:2011年8月6日星期六14:30------16:30
编剧:Bernard Shaw
导演:Philip Prowse
演员:kara Tointon, RupertEverett
星评:
奥黛丽赫本主演过大名鼎鼎的好莱坞电影《窈窕淑女》,现在它的原著萧伯纳的戏剧Pygmalion(《卖花女》或者《皮格马利翁》)在伦敦西区上演。情节上大体都是相同的,讲一个语言学教授与人打赌把一个粗俗的街头卖花女伊丽莎变成了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而语言学教授却爱上了自己的作品。不过与电影欢喜结局不同的是,原著中伊丽莎发现自己只是这个独身主义者眼中的赌具,愤然离开,嫁给了自己的追求者。
现场
演出现场,观众多半是中老年,加上这出戏气质严肃,现场气氛沉默稳重。演出上下半场用厚重启发性强的古典音乐开场,演员们在干冰气体和灯光打造出的暮霭雨雾中翩翩登场。我感到有点寂寞,故事发生在这个古老帝国最强大、淑女绅士风最盛行的时代,无论是伊丽莎粗俗的举止和浓重的口音、她在首次出席社交场合说出的古怪话题,还是他父亲伪中产阶级的可笑举止,现场的观众都阵阵哄笑。一阵一阵的陌生,那些旧时代的俗语见闻礼仪规范,我无从了解,无法体会。自己好比一个初来乍到、无知少觉的乡下姑娘,隔一层厚厚的弥漫烟雾,看对岸轮番上演嬉笑怒骂。
舞台布景并无新鲜之处,可以陈述一下的是它的巨大。舞台中后部树立着两块对称的类似中国屏风的巨大景片,可以翻转,变换成书房和客厅的模样。那个样式一看就是古老的时尚,甚至是时至今日在伦敦很多古老的建筑里仍然能看到的模样。我似乎又多心似的读出些维持正统保持风范的味道。演出过程中时不时传来阵阵轰鸣声,起初以为是舞台后部搬移沉重布景,后来渐渐反应过来是外面街上重型车辆来往的声音。(剧院在伦敦市中心,在著名景点旁边,来往车辆相当多)我所在的位置是地下一层的楼座,听起来格外清晰,大概是地面比较薄的缘故吧。这座剧院百年古老,它没有想到过以往过过马车而已的门庭外,会迎来如此重型的庞然大物吧。
乡气难演
话说两位演员都不合适语言学教授和伊丽莎的演员都不是非常合适。饰演语言学家的一脸大胡子几乎没有面部表情变化,本来这样或许能够饰演出人物本身古板的独身主义气息,但是变化实在太少了,让观众感觉不出人物前后对伊丽莎的态度变化,只觉得一会发怒一会沉默的口气来得很蹊跷。饰演伊丽莎的女演员是英国当地一位比较知名的女演员,出演过很多英国电视剧,但是她的问题就如同当年奥黛丽赫本出演伊丽莎受人诟病一样:难以诠释出伊丽莎本身难以磨灭的市井气质,即使在她经过训练被改造成为一位上流社会的小姐。我想,如果让巩俐现在再去演秋菊恐怕也很难演得出来了吧,多年的光鲜生活总会让人下里巴人不下去的。
关于皮格马利翁
小小溯源一下,之所以取名皮格马利翁,萧伯纳巧妙地借用了同名希腊神话故事的含义。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的国王,用自己出神入化的技艺雕刻出一个美丽的象牙少女雕像,结果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它。后来他请求美神阿弗洛狄特赐予这座雕像生命,于是皮格马利翁得偿所愿。真是相当理想化的故事!
很喜欢那个国王对着雕像思考这个情节,明明知道对着的是一个冰冷冷毫无生气的事物,因为赋予了太多感情和想象,它也好像有了情绪和态度。这种想象和梦境一样,寄托了人类奇妙和瑰丽的思想,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精神境界。当这种境界走到了一种极端,它就充满了孤注一掷的艺术美感,完美和无懈可击,仿佛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昭示了一种静谧的美好。这样思考着的人类应该很孤独吧,却又实在非常勇敢。尽管这精神上的狂想,临近于着魔的临界点。但它着实反映了许多人类与生俱来不可抗拒的情绪——不可自拔的牺牲、“点石成金”的想象和感动苍天的执着。我猜想这个希腊神话的创作者必定带着悲悯的心情写这则故事,因为他了解人类“飞蛾扑火”的热情和悲情,哀痛我们实在不过是尘土,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希望——让那个孤独而忧伤的国王见到自己的想象成真。
雕像情结
骤然细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才发现我很迷恋它。想起我曾经见识过的两座雕像来。好多年前,读过金庸的《天龙八部》,很多或英雄或潇洒的情节早忘光了,唯有一个情节长留在心里,是段关于逍遥派的前史,篇幅不大,与雕像有关:逍遥派的掌门无崖子和师妹李秋水在一起,他把一块巨大美玉雕成了李秋水的样子,从此整日对着雕像出神。李秋水十分不解,明明真人就在身边,为什么他却痴痴瞧着玉像,后来两人终于闹翻。直到很多年物是人非以后,李秋水在临死之前才洞悉真相,发现那座雕像根本不是自己,而是与自己长相相似的同胞妹妹[1]。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那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只是觉得这个故事怎么那么别扭那么纠结那么固执,还蒙上一层烟雾缥缈的东西,有种云山雾罩的美感和凄凉。这段情节,点到为止,故事里的妹妹没有出现甚至没有名字。不过,90年代初的香港编剧却惦记着她,在电影《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里面,给了她一个名字,叫做李沧海。我猜,金庸先生或许也是满意的吧,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现在想来,按照咱们的审美观点,不出现的“留白”是最具美感的,也更有诱惑力。不过,几千年前的希腊人,却不满足这样的“雾里看花”,非要亲手采摘一回。爱上一座雕像根本就是悲伤绝望的,然而,希腊人的浪漫、善感和不忍心,给冰冷的雕像赋予体温;而金庸大侠则让玉像“转世”成了神仙姐姐王语嫣。
后来我又遇到过一座雕像,源于一个名叫方停君的风华绝代的少年,来自我相当喜欢的一位网络作者彻夜流香的笔下。在宋元著名的“钓鱼城之战”的时代背景下,那是个才华横溢、文治武功又孤独狠绝的俊美贵族少年,背负着保护国家的使命。因为特殊的身份背景和经历联系着宋元之际的江湖、庙堂和敌国的各方势力,在宋朝大厦将倾之际妄想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很少有人能了解这个孤独少年绝高的智商和还未开窍的情商,为了国家大义该爱的人不能爱,该恨的人恨不起来,小说在国仇家恨和爱恨纠缠的追逐中怅然结束[2]。时隔几年,在作者的另一部同系列小说中[3],一个古怪疯癫的虎头少年偶然掉进山洞习得一身绝世武功,当少年成为老头,他这段自行学成一身出神入化武功的故事已经成为神话的时候,他的一位徒弟因为机缘巧合再次落入洞中的时候,才揭开师傅学会武功的真相,那一切源自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像——风华绝代、睥睨一笑,那原来是方停君的雕像。百年前他在结束了战争之后,翩然隐居于这个山洞,把毕生武功绝学绘于山洞之中。跟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佛家弟子,出于对于方停君的仰慕,他精细地雕刻了方停君的雕像,立于山洞之中。百年以后,前尘往事俱已成烟之后,我们通过后来人偶然进入山洞的情节,再次领略了方停君的风采。我始终愿意把这样一段“前世今生”理解成是希腊神话的后现代用法,不知道作者把自己还是读者变成一个皮格马利翁。不管是否读过之前的小说,通过这座雕像,仍然使读者对那样一个乱世中的翩翩少年倾慕不已。尽管由故事看,少年后来又是行踪成谜,但不管是读者还是故事中的人物,都得以思念有形起来。作者“春秋”笔法,我至今想起后世弟子偶然窥得那雕像遗世独立的情节,仍然觉得浪漫不已。
不过,说起来,希腊神话和这两个中国故事起点有所不同:那个国王皮格马利翁多少有点上帝造人的意思,而中国故事是“以人为本”。不去想多么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审美意义,只要想到它们曾经带来的“殊途同归”的震撼和美感,我想就足够了。
路沿石上的生活——“打砸抢”由来已久
如果粗略的看这部戏剧作品的情节,以现代人八卦和潮流的情结来看,它有点麻雀变凤凰、小燕子变还珠格格式的灰姑娘色彩。那也是我们现在人的眼光和角度,无论如何,它实实在在诞生于差不多一百年前[4]。
《卖花女》发表在一个“伊丽莎”们命运转折的关键年代,一百年前的伦敦作为欧洲少有的大城市,有着相当大规模的街头生意。很多年轻女孩子正像剧中的伊丽莎一样:没有受过教育、举止粗俗、沿街做些小买卖。有数据统计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人数在12000到20000之间的小孩子在街头讨生活。到了1911年,由于机动车的出现和变宽的马路加大了路边生意的危险,议会出台了禁止孩子年轻人在路边做生意的议案。于是,像伊丽莎那样的年轻女孩的生活开始了转变。与此同时,劳工市场也开始了变化。年轻的女孩子们成了很有吸引力的劳工资源,她们可以在零售商店、文书部门或者一些工业部门找到工作,工资有时候甚至比男孩子还高。对比风餐露宿、毫无保障的街头生意,这样的工作实在非常的舒服。
同时,年轻的“伊丽莎”们可能还见证另一番社会变革。工党的崛起给英国两个传统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Conservative andLiberal)带来了冲击,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激进的工人阶层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政治的争斗与工业的雇佣关系上的冲突,遥相呼应。这样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年轻的女孩子们灵感,她们开始通过联合罢工的手段与管理阶层对抗,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逐步建立起她们自己的工会。这样的运动,带有很多女权主义色彩。于是,有人描述,这是新工会主义掀起社会变革的开始,激烈的政治派别斗争对于年轻女孩子的意义要大于在工会里的男性。
不仅如此,“伊丽莎们”还可能见识到日渐增长的女性政治性对抗活动。1908年以后,这种冲突对商业和私人宅地的袭击愈演愈烈。1912年,伦敦最著名的几条街道Piccadilly, Regent Street和OxfordStreet遭受了很多次严重的打击。许多女性突然从她们的包里拿出锤子等武器,袭击很多著名的商店,进行砸玻璃等毁坏活动。还有人袭击了唐宁街10号,把一柄小短斧扔进了当时首相的马车里,在都柏林皇家剧院埋设小型炸弹。这样的活动使她们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联系到伦敦最近的打砸抢事件,看来,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民意,这种破坏性的示威活动似乎是一种传统了。
像伊丽莎那样独立的女孩子们触摸感受到那个年代相当犀利的变革情绪。她们的志向抱负和观点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都是相当超前的。但重要的是,这没有使她们的生活变得多曼蒂克。尽管有大量的女孩子生活贫困,选择有限,挣扎在社会边缘。但越来越少的人不用再在街上沿街讨生活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另外,萧伯纳的这出戏剧还有一个要点,就是通过语言学家对卖花女语言的训练突出自己对英语语言的关注。当然这是个相当长的话题,以后有机会还是应该写写滴!
[1]说起这段情节来,真是费了点心思呢。话说真是很多年前看过的小说、电影还有电视剧了,这段情节出自哪一种体裁,实在有点想不起来了。而我印象中,偶尔有些电影和电视剧对原著的改变也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老的台湾版《倚天屠龙记》),所以就重新找来电影和电视剧看,几番之下,根本无迹可寻。失望之后,才想起来应该翻翻原著,于是把逍遥派长辈的纠葛情节前前后后看了一遍,这才心满意足,觉得对金庸大师是要顶礼膜拜的!
[2]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有风鸣廊》。
[3]《灰衣奴》。
[4]剧本发表于1912-13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