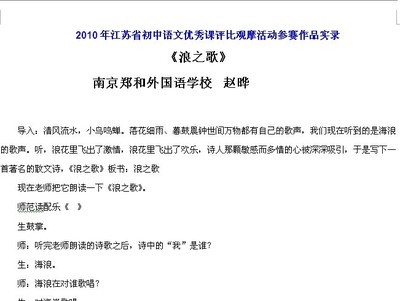《喧嚣荒塬》问世十年后的冷思考
渭南师范学院李险峰
摘要:《喧嚣荒塬》是秦东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成名作,是继陈忠实《白鹿原》之后又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家族小说。它在艺术追求上主要收获了四方面成就,一是以宗族械斗为构思中心具有多重价值,二是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三是营造了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四是小说语言表现出较强的审美张力。
《喧嚣荒塬》是陕西富平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成名作,首先在《中国作家》2002年第2期全文发表,稍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和巴金文学奖,当时的评论界好评如潮,现撮其要者:鲁迅文学院何镇邦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对于我这样以读小说为业的专业读者来说”,《喧嚣荒原》“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1]安康学院教授姚维荣读罢《喧嚣荒原》,“深感这是又一部恢宏大气、内涵深厚、颇具艺术魅力的家族秘史。”[2]周正宝誉之为“新奇而独特的人类生存‘窗口’”。[3]著名作家柳建伟读完小说断言:“《喧嚣荒塬》肯定会在文坛引起震动,成为2002年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党益民这个对许多读者尚显陌生的名字,从此以后无疑会列入中国当代实力派长篇小说作家的名单之中。”[4]著名评论家丁临一认为,“《喧嚣荒塬》堪称是一部沉实厚重、富于内在意蕴的力作。”[5]资深评论家何西来看完作品认为“小说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很好读。”[6]一部作品得到一两个批评者的偏爱在文学批评几乎沦为文学表扬学的语境下并不稀奇,但博得批评界的普遍称赏就值得关注了。
时间是检验一部作品最有说服力的试金石。2011年初,《喧嚣荒塬》以《羌笛劫》命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30万册。回望过去的十年,我们会注意到,评论界关于这部小说的言说方式大多属于印象式扫描,语焉不详,除了雷达在《长篇小说笔记之十三》中有所侧重的学理关照外,鲜有总体意义上的深入解读。而且,所有的赏析和准批评几乎集中于作品面世后不久,此后则留下一长段空白。基于此种境况,本文在《喧嚣荒塬》问世十周年暨又一次重磅出版之际,就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一冷静审视。
《喧嚣荒塬》显然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回望中国小说史,家族叙事是一个传统题材。中国自有长篇小说以来,《金瓶梅》和《红楼梦》开了家族小说的先河,而且是家族小说乃至中国文学的不朽经典。在现代文学领域,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张爱玲的《金锁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是有代表性的家族小说。建国后,老舍的《四世同堂》把家族小说推向了新的思想艺术高峰。80年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船》和苏童的《罂粟之家》代表着新时期文学三种不同审美风格家族叙事的先锋实验。90年代以来,自陈忠实的《白鹿原》横空出世后,后新时期的家族小说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党益民的《喧嚣荒塬》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诞生的。
不难理解,在众多作家纷纷向家族世界进军的态势下,受《白鹿原》这一家族题材经典前文本的逼仄,要写出富有艺术个性、被评论界认可、受广大读者青睐的家族小说,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党益民在这个“家族城堡”中奋力冲击并成功地突围出来,在思想艺术上取得了以下几方面较为突出的成就。
一、以宗族械斗为构思中心具有多重价值。
宗族指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生活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属於现代意义上模糊的族群概念。一个宗族可以包括很多家族。《喧嚣荒塬》中的莫村和桃花沟就是清末民国时期遗失在一个封闭荒塬拥有共同祖先的两个莫氏家族。一个宗族因拥有共同祖先在面对异族骚扰或侵犯时往往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宗族内部往往会因各种矛盾引发冲突,宗族冲突的最终形态便是家族之间的武装械斗。《喧嚣荒塬》中的莫村和桃花沟为了保住和夺得象征着宗族正统地位的御赐金匾、党项秘笈和紫砂宝壶以取得宗族的话语权、领导权与合法性,几乎每隔12年就会爆发一次大的械斗,这样的大械斗历史上已发生过二十七次,血流漂杵,死伤无算。他们之间的宗族械斗似乎具有某种不可逆性和轮回性。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关于宗族冲突的叙事片段屡见不鲜,但像《喧嚣荒塬》这样以宗族械斗为构思中心的文本绝无仅有,因而在题材的挖掘上就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此其一。
其二,在中国古代史上,南方战争相对较少,基本不发生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宗族迁徙,而北方汉族同胡族多有征战,大小规模的举族迁徙时有发生,因而宗族比较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宗族社群,爆发宗族械斗的可能性较小。而南方汉族多是两晋及南宋时期北方汉族后裔,宗族意识自古强烈,容易跟当地其他宗族产生矛盾以至发生武装械斗。因此,在文学和影视文本中,宗族械斗在空间上几乎都发生在江西、湖南、广东、福建一带。而《喧嚣荒塬》中的宗族械斗发生在渭北极度封闭的党项村落之间(极度封闭正是莫村和桃花沟这一党项后裔家族得以在渭北长期定居未被同化的主要原因),不仅宗族械斗的叙事空间具有独特性,而且渗溢出党项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基因。据《富平县志》载,老庙镇(《喧嚣荒塬》中的莫村为老庙镇的一个村级行政单位)民性“剽悍好讼”,用今天流行于富平的一句俗语来诠释倒很恰切:“不为蒸馍,为的是汽(气)圆。”这种民性一方面含有勇猛、无畏、倔强的意志品格,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执拗、愚昧、刁蛮的精神偏颇。莫村与桃花沟之间三百年来持续不断的宗族械斗正是这种民族性格遗存在作祟。
其三,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不是一味地纠缠于宗族械斗本身,没有将对莫氏家族的仇杀史所进行的反思仅仅局限于这个家族内部,视之为孤立的、个别的、偶然的存在,而是将其置于清末以至建国前夕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和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之中。20世纪前半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事件与两千年来的历史进程迥然不同,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总体面貌,也重塑着国民的精神世界。莫村与桃花沟争夺家族话语权、领导权的血腥博弈跟慈禧西逃,白狼祸陕,反袁逐陆,军阀混战,“二虎”守长安,冯玉祥入陕,陕北闹红,富平交农、渭华暴动,西安事变,中条山抗日,国共“拉锯”等迭次上演的历史事件以及冰雹、地震、蝗灾、旱灾、涝灾、瘟疫等频仍的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而赋予家族械斗这一古老题材以崭新的内容,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回望20世纪上半叶渭北斗争史、灾害史的侧门,让我们目睹着封闭的莫村被现代性一步步打开的景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历史认识价值。
其四,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于作品中那些浑然不知地卷入到愚昧的械斗之中的人类灵魂进行了拷问,彰显出浓厚的悲悯情怀。在作品中,这种悲悯和拷问是通过天奇的视角表现出来的。天奇出世的时候不像一般婴儿发出哭喊,后来自然成了哑巴,行为乖僻,在荒塬上人们的心目中是个“怪人”和“傻子”,正因如此,他方可游离于本村与桃花沟的仇杀之中,又未成为父亲的仇人报复的目标。他用冷峻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而这正代表了作者的视角:对于莫村所发生的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械斗、仇杀,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批判的,他把自己的批判意识隐藏于事件的进程之中,通过天奇的视角加以表现,也通过天奇的似乎有悖常理的思索将已被莫村人所习以为常的丑陋揭示出来。曹文轩指出,“文学的职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悲悯情怀。”[7]221在“悲悯情怀”被大众狂欢、娱乐至上、零度书写、身体书写等新思潮几近淹没的创作背景下,党益民在《喧嚣荒塬》中表现出的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显得十分可贵。
二、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
人物形象是衡量一部前现代派长篇小说思想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党益民在《喧嚣荒塬》这部总体上属于传统叙事的文本中成功塑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莫鹏举。这是一个比《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性格复杂得多的悲剧性封建族长形象。他善于利用族长身份赋予他的威权和殷实家财,充分满足其强烈的对性的欲望,不择手段地寻花问柳,追逐美色。不仅明媒正娶了三房太太,而且引诱霸占了同宗兄弟老六的妻子香椿,又利用同宗侄媳草姑为其提供人奶之机强奸了她,还跟三太太的妹子小菊媾和。这是渭北的莫鹏举与白鹿塬上的白嘉轩最大的不同,甚至比《白鹿原》中好色的鹿子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区别或许来自于党项人文化基因在两性关系上相对随意的游牧伦理,也正是这一强烈的猎艳欲望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祸根。他阴险狠毒,暗算岳父,利用土匪中的一股石娃去对付另一股土匪老六,而在石娃失败后又设计诱杀了其残部。他又富有胆魄心机,率领莫村的青壮年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家族间互相残杀的宗族械斗。白狼的匪患突如其来时,他镇定自若,智退白狼,保全了村民。他不动声色地收拾了私通的弟媳与副官。他慷慨善良,在大饥荒年月于河滩架起大锅,倾其所有熬粥蒸馍赈济饥民。他被与三太太有私情的管家出卖而被桃花沟的本家兄弟和土匪老六残忍杀害,生命以悲剧收场。
托尔斯泰对“人”有深入的体察,他说:“有人徒劳地把人想象成为坚强的,软弱的,善良的,凶恶的,聪明的,愚蠢的。人总是有这样的,有的是另一样的,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有时明理,有时错乱;有时善良,有时凶恶。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8]6莫鹏举正是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圆形人物,福斯特指出,“唯有圆形人物才能在某一段时间内扮演悲剧角色。”[9]64莫鹏举丰富的人性展示彰显了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自觉。
作品近百个人物中,除了主人公莫鹏举这一核心形象的成功塑造,其他主要人物也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太婆、天奇的神奇诡秘、天生异秉,管家兴兴的深藏不露、有仇必报,莫鹏祥的忘恩负义、心狠手辣,老六的凶蛮残忍、不择手段,靠做棺材发家的木匠贵生的爱财如命、铿吝自私,满仓的豁达豪放、迷途知返,马先生的沉着冷静、机智果断,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在女性人物画廊中,香椿热烈而有心机,跟莫鹏举在杏林媾和时还不忘带把豆角做幌子以敷衍老六;草姑倔强执拗,遭年馑时宁可“卖炕”也决不接受莫鹏举的接济;三太太刻薄阴沉,暗里诅咒天顺天佑兄弟。再如痴情的柳儿,淳朴的麦花,浮浪的水仙等也都显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致。
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作为一种颇具现代性的小说艺术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滥觞于拉美西班牙语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与中国叙事文学固有的志怪传统一拍即合,很多作家乐此不疲,到世纪末遂发展成颇有声势的“神秘主义”。[10]137-170任何一种艺术风格以及与其相应的技巧手段无所谓守旧还是前卫,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建立在形式与意蕴的适切性基础上。在笔者看来,无论建构民族秘史抑或书写家族秘史,魔幻现实主义的介入也许是难以跨越的门槛。惟其如此,方能营构神秘氛围。
《喧嚣荒塬》既是一部彰显着儒家文化景象的封建家族史,又弥散着党项民族秘史的因子,一度强大的西夏王朝的覆灭以及这个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人的“人间蒸发”本身就氤氲着神秘的历史幻景,因而魔幻色彩的涂抹自然成为作者明确的艺术追求。作品中的魔幻色彩主要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一是设置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太婆和天奇。太婆九十多岁的时候竟长出满口新牙,她在夜间咬碎核桃的声音令莫家大院顿生恐怖气氛,她手中那本发黄的《党项秘笈》总让人感到神秘,她活了一百三十多岁——任何人能活到这个岁数堪称奇迹。另一个神秘人物天奇的“面世”与地震同时发生,此一奇;生下后不发出婴儿啼哭之声,此二奇;刚生下竟用“冷漠”的目光看着太婆,此三奇;不会说话却吹得一手好羌笛,此四奇;一个傻傻乎乎行为乖张被家族边缘化了的哑巴最终却成了莫村和桃花沟整个莫氏宗族的拯救者,此五奇。有此五奇,天奇之“奇”就非常引人注目了。二是设置异物即那只似乎成了精的金丝猴,它一出场就让一只野狼毙命,它能预报莫家的各种灾难,谁也不知它究竟活了多长。三是描述奇异场景,比如小说开头对地震征兆的叙述就弥散着诡异景象。
神人太婆、奇人傻子、异物金丝猴贯穿小说始终,他们的存在和异象描绘共同构成一种神秘诡异的魔幻色彩。从小说的总体艺术效果来看,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人、物、景的多层设置与描绘,同作者试图表达的主题意蕴是谐调的,只有如此,方可建构家族仇杀的“魔圈”。《白鹿原》中也有一点神秘叙事,比如白鹿神秘的闪现,小娥在鹿三身上的鬼魂附体,白灵被肃反者活埋在白嘉轩身上的第六感反应等,但不像《喧嚣荒塬》这样漫漶于文本始终。这样对比并不意味着魔幻色彩的浓淡牵涉家族小说艺术品位之高低,但至少证明党益民在构思儒家文化与党项基因相交织的家族叙事时自觉的艺术诉求。当然,《喧嚣荒塬》并不是一部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是具有魔幻色彩的传统现实主义文本——事实上中国的自然和文化也不具备创造经典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壤,但作者营造神秘意象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表现应值得肯定。

四、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张力。
时至今日,评论界对文学作品语言的关照实现了由载体论(工具说)向本体论的转变,人们不再将语言简单地视为文学用来表达的工具,不再将语言置于被其他要素支配的卑微境地,不再将视点放于语言之外去寻找存在于语言本身的线索,而是从其内部探寻文本的语言性。因此,将小说的语言放在最后予以讨论并非如黄子平早先否定的那种情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常见的格式是,‘最后,谈谈作品的语言……’”[11]45只不过小说的语言风采被前面三个思想艺术个性放射的夺目光芒有所遮蔽而稍显暗淡。《喧嚣荒塬》之所以能使作者一举成名,除了题材挖掘、人物塑造、魔幻色彩的助推,也源于语言的艺术张力。
《喧嚣荒塬》最脍炙人口的是浓郁的方言色彩。语言是一个民族身份得以确立的首要标志,方言是地域文化最突出的表征。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前半叶莫氏家族长期自相残杀的衰败史,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了小说乡土化的语言风格——方言土语随着方言区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日益提高正逐渐被普通话同化着。在当下语境中,笔者以为,方言是一种文化,而普通话仅仅是一种工具。跟所有方言一样,渭北方言不仅语音有独特性,它的某些词语所表达的意义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根本没有替代对象,甚至在任何词典中找不到令人信服的书写符号,只能用同音近音字来替代。这种不可替代性最能表征地域文化。比如,天奇出生时异象环生,太婆说,“就把这碎子叫天奇吧。”“碎子”在渭北方言中发音时有儿化倾向(完整的书写形式应是“碎子儿”),常用以指称小男孩,而且不光指涉年幼这一客观事实,还带有疼爱、亲昵的情感取向。又如来福骂老婆毛女:“你给我往回滚!再避干小心我收拾你。”“避干”其实应写成“屄干”,渭北方言读作pígan(干读弱降,调值大约是21)。在渭北,如果张三认为李四顶撞自己或者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就会用“你胡屄干啥哩”、“少屄干”等恶俗的话语来予以阻止和威胁。小说中不仅人物语言渭北化,而且叙事语言也含蕴着地方风味。莫鹏举被妻妹小菊的美色所迷,“天奇看见无数萤火虫从他爸的眼睛里飞了出来,还看见他姨的脸儿越来越红,红得跟旦柿一样。”富平县享有中国“柿子之乡”美誉,柿子品种五花八门,大概只有富平人能瞬间捕捉旦柿所传达的准确信息。从接受的角度而言,陕西特别是渭北读者更能从《喧嚣荒塬》中产生审美愉悦,与作品中方言的独特表意有直接关系。
其次,作者善于运用故事场景中的物象来做喻体,大大强化了比喻的修辞功能。这几乎是党益民文学创作使用比喻时自觉的美学追求。比如,地震发生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奇怪响声,仿佛有几十个碌碡从天上滚过。”“碌碡”是农业机械大规模出现前常见的石质农具,竖起来呈圆柱体,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庞大而沉重,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基本失去使用价值,而成为农耕文明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让这样的东西成群结队地从天上滚过,不光会造成霹雳般的巨响而让人产生听觉上的震撼,而且会让人产生碌碡突然从天而降的恐惧。倘若描写当下农村或二三十年代巴黎地震发生时的情形,这个比喻显得就不合适了。
此外,作品中有些叙述语言生动传神,栩栩如生,有力地强化了表意效果。小说一开始描写地震前的征兆:“公鸡排成一行在院墙上咯咯地发表议论。”公鸡们似乎预感到了不详。“一只老鼠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跳上了香椿的脊背,稍一迟疑,发现站错了地方,又急忙跳下去落荒而逃。”老鼠对地震特别敏感,慌不择路。像这样把动物的神态和“心理”刻画得如此惟妙惟肖,仅用一句“这里使用了拟人化手法”作出修辞学层面上的解读显然是不能领略这种叙事语言的审美张力的。
以上就《喧嚣荒塬》这部家族小说思想艺术的超越性作了一番梳理。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需要对一个问题稍作厘清。有些读者包括个别批评家感觉到这部家族小说存在跟前文本《白鹿原》似曾相识的印象,便冒然下了有“模仿”痕迹的局限。这实在是一个误读,造成误读的原因不在主观上的随意判断,而在于两部作品客观上相同的时空因素:故事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制于不可更易的共同的历史场景;空间上都处于关中东部渭河两岸的“塬”上,具有相近的自然环境和相似的地域文化(方言、风俗);都深受儒家伦理文化和农耕文明的浸淫。这跟我们阅读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作品时感到似曾相识是同样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何镇邦.家族秘史与魔幻色彩——读青年作家党益民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人民日报》2002年8月18日.
[2] 姚维荣.西部荒塬的家族秘史――党益民《喧嚣荒塬》简析.《中国青年报》2002年6月19日.
[3] 周正宝.新奇而独特的人类生存“窗口”——读党益民长篇小说《喧嚣荒塬》.《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7日.
[4] 柳建伟.一部诡异雄奇的民族生存秘史——略论党益民长篇小说《喧嚣荒塬》.《文学报》2002年6月13日.
[5] 丁临一.沉实厚重的警世之作——评党益民长篇小说《喧嚣荒塬》.《文艺报》2002年8月6日.
[6] 何西来.家族仇杀的反思——读《喧嚣荒塬》.中国作家网,2008年10月12日.
[7] 曹文轩.《小说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8]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9]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花城出版社,1984.
[10]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作家出版社,2003.
[11] 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