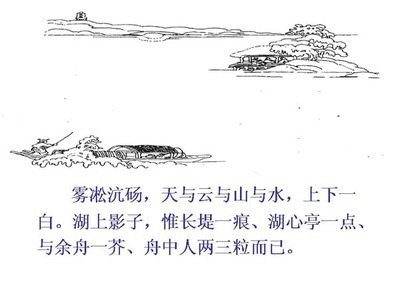天刚蒙蒙亮,丫头秀儿就去大厨房提了大铜壶热水,预备三小姐起来洗脸。
小姐们起身都早,还是正清公老太爷在时立下的规矩,卯正时刻,不仅少爷们要上书房,小姐们也得起来,晨省之后,或诵诗书,或做女红,总不兴晏起。
初夏时分天亮得甚早,不一会儿功夫东方已经透出鱼肚白,秀儿怕三小姐误了晨省的时辰,于是隔着门唤:“三小姐,该起了。”叫了两声不见动静,秀儿心中奇怪,于是伸手推门。谁知门竟从里面拴上了,怎么推都推不动。她忙绕到窗边去,幸得窗子并没拴,一推就开了。
秀儿踮起脚来往里面一望,这一望不由得魂飞魄散,尖声大叫:“快来人啊!快来人啊!三小姐寻了短见!”
她这么惊慌失措的一嚷嚷,幸得这时辰各房的人都已经起来了。隔壁院子里原住着二少爷与五少爷,因而他们来得最快。二少爷原是急性子,见着这情形,一脚就踹开了房门。众人一涌而入,把悬在房梁上的三小姐解下来。幸好三小姐虽双目紧闭,身子还是软的,估计吊上去没多大会儿。于是一面急派人去请大夫,一面就有老成些的嬷嬷,将三小姐平放在床上,替她推胸过血。
这一顿大乱,上下都失了方寸。赵家二太太刚起来梳了头,正巧七小姐来问安,方与小女儿说了几句闲话,忽听见下人叫嚷说三小姐寻了短见,只唬得一跳,心急如焚忙扶了个丫头走过来。七小姐也忙跟着过来。
刚走到三小姐闺房门前,忽听众人道:“好了好了,缓过来了……”
二太太犹未松口气,只听得细细的啜泣,依稀是三小姐的声音,哭道:“我死也不嫁……”
早有丫头打起帘子,七小姐搀着二太太跨进门槛,围在床边的一众人见太太来了,忙闪开一条道。二太太见三小姐睡在床上,面如纸色,一时发急,只说道:“你这孩子,怎么能动这样的傻念头。”
三小姐却也没有别的话,躺在那里只是掩面抽泣。二太太道:“傻孩子,人家来提亲,总不是什么坏事。别的不说,那慕容宸原是现任的承州巡阅使,你嫁过去,就是当家太太,现成的巡阅使夫人。这承州城里,旁的人哪有这等荣耀风光。虽然他人年纪稍长些,年长的人才知道疼人。你今年也二十四了,应家四小姐跟你同庚,如今小孩子都已经有了两个。你这样一年年耽误下去,死活不肯嫁,又是何苦来哉。”
三小姐这才拭了拭眼泪,双眼望着帐顶,说道:“话说得真好听,不就是拿我去巴结那土匪。我宁可死了,也不能作践自己嫁给这种人。”
二太太说道:“你这孩子说得什么糊涂话?若叫你父亲听见,又该生气了。”
三小姐道:“听见又怎么着?横竖欺负我没有娘罢了。”
二太太本来是好言好语相劝,听见这句话,一时竟气得说不出话来。七小姐见母亲气得面色发白,忙劝道:“三姐,如今慕容当政,父亲也是心中为难,不好当面回绝人家,所以才含糊其词,搪塞了回去。三姐莫误听了谣言,三姐别的不想,只想这几年,凡是来提亲的人,父亲大人都从来是先问过三姐自己的意思,哪次有过例外?”
三小姐倒笑了一笑:“七妹妹这张嘴啊,真是比那回廊上的黄鹂儿唱得还好听。父亲不过可怜我亲娘死的早,多留我几年。有人总嫌我吃闲饭,到底要除了我这眼中肉中刺钉才好,如今那土匪头子要娶老婆,你们正中下怀,一石二鸟。既巴结了权贵,又除了我这祸害,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可怜我的亲娘……统共就只我这么一个女儿,她若晓得我活着受这种欺负,还不如当年带我一块儿死了的好……”一边说,一边就呜呜的哭起来。
二太太气得浑身发抖,说道:“谁拿你巴结权贵了?谁当你是眼中钉肉中刺了?什么叫土匪头子娶老婆,这是当小姐的人应该说的话?”
谁知三小姐越发大哭起来:“我哪里是什么小姐?我比那丫头还要不如。上房里打发一个丫头嫁出去,太太还发善心再三嘱咐,打听清楚了人家,好好陪一份嫁妆。哪像我这没娘的孩子,任由得人家欺负。”
二太太见她越说越是厉害,不由得道:“你倒是说说看,这家里谁欺负你了?这些年来,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先挑了尖的给你?哪一样比你妹妹们差些?你口口声声说受了欺负,你倒是挑出个人来,看家里谁欺负了你。”
三小姐哭道:“我哪敢说母亲大人欺负了我这没娘的孩子,既然嫁那姓慕容的这等风光,母亲怎么不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巴结他?”
二太太气得脸色发红,站起来道:“我不同你说了,回头叫你父亲来同你理论。”
三小姐道:“我知道你们要去父亲面前告刁状。我告诉你们,把我逼急了,横竖是个死。你们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世,到时候我揣把剪子上花轿,把喜事给办成丧事,我看你们拿什么去巴结人!”
二太太气得径直而去,七小姐馨雪陪着母亲回到上房,见母亲脸色不豫,因而劝道:“娘,三姐素来是这般不会说话,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二太太眼圈发红,说:“这回的事,原是为她好,想她一个二十多岁的老姑娘了,总不能再耽搁下去。正巧有这门亲事,你父亲就一口应承下来,谁知道一片好心,倒被她当成了恶意。如今这一闹,可要怎么收场。你父亲今日回来,定然又要动气。”
到了晚间,赵锦声回家来听说此事,果然勃然大怒,出了上房往后院走去,就叫人:“取家法来。”
赵家家教严格,所谓家法是二尺三寸长的软藤鞭子。只不过女儿家犯了错,从来不过罚不准下楼,再者,亦不过罚跪香。二太太听见说老爷要家法,知道是气得糊涂了,连忙也走出来劝阻。
赵锦声早年间曾任过驻洋的公使,虽是旧式的大家庭,其实许多作派都非常开明。说是取家法,亦不过恼火三女儿不听话,存心吓唬一下。谁知三小姐是个软硬不吃的性子,听见父亲说要打,反倒连鞋也不穿,赤着足披头散发的冲下楼来,便要往垂花门前的石墩上碰去。众人乱轰轰急着拉扯,三小姐又哭又闹,道:“多嫌着我一个,我死了你们就清净了!”
几个嬷嬷劝的劝拉的拉,总算把三小姐拦住了。赵锦声大怒,把手里的鞭子往地上一扔,斥道:“不许拦,让她去死!”
正不可开交,二太太也赶着来了,叫着赵锦声的字,劝道:“锦声,沉霜不过一时是一时糊涂,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
三小姐却将脸一扭,大声道:“谁糊涂了?你们巴不得我糊涂了,才好卖了我呢!”掩面而哭:“反正我是没娘教的孩子,哪里有人肯为我真心打算……”
赵锦声生平最大恨事莫过于此,被她这么一吵一哭,顿时满腔的怒火都化为乌有。正巧七小姐馨雪听说父亲大发雷霆,因为是女儿家的事,几个哥哥都不便来劝,于是便走过来,向父亲请了安,陪笑道:“天也晚了,爹才刚回来,还是先回上房去用了晚饭……”一语未了,三小姐突然指着她道:“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的,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事哪样少得了你?你得意什么?别以为就是看了我的笑话,你自己还不是被男人骗了,自己嫁不出去,还有脸在这里说三道四!”
七小姐万万不料她说出这番话来,顿时脸色煞白,往后退了一步。赵锦声气得发昏,一掌搧在三小姐脸上:“你这说的还是人话?”三小姐被这记耳光打得怔住,旋即“哇”得大哭起来,几个人都拉不住,拼死拼活要寻短见。二太太见馨雪眼圈微红,实在忍不住要哭,忙将她拉回上房去。
馨雪心里难受,又怕母亲愈发难过,却忍不住满腹的委屈,伏在案上呜呜咽咽哭了一阵,见母亲坐在一侧,只是唉声叹气。她拭了拭眼泪,说道:“母亲,既然三姐不肯,我去就是了。”
赵太太愣了一愣,倒落下眼泪来:“我的儿,这如何使得?本来人家提的就是你姐姐,你年纪又还小,这是终身大事,岂同儿戏?”
馨雪反倒过来安慰她:“娘,您不也曾说过,那慕容宸虽然人鲁莽些,年纪稍长些,也不见得是坏事。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况且如今三姐死活不愿意嫁,若是闹开来,亲友们岂不闲话?您素日知道那起三姑六婆,没事还要嚼出事端来,如今岂不更要说是咱们欺负三姐庶出?姨娘去得早,母亲您这些年虽然视三姐如己出,旁人眼里,终归是隔了一层肚皮。再说父亲早应允了人家,何必让父亲大人觉得为难?我嫁就是了。”
赵太太听她说得轻描淡写,倒越发觉得心里难受:“馨儿,我知道秦家二少爷的事让你伤了心。但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终身堵气……”
馨雪轻轻叫了声:“娘”,慢慢叹了口气,说道:“反正我嫁给谁也是嫁,既然那慕容宸来提亲,三姐又不肯答应,我去就是了。”
赵太太心里原有千言万语,可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叫了声:“我的儿……”搂着馨雪,不免痛哭了一场。她只道女儿是说说气话,谁知道第二天馨雪便对赵锦声言明,自己愿意替姐姐出嫁慕容氏。赵锦声正自焦头烂额,听闻女儿如此主见,一时也没了主意。见馨雪斩钉截铁,说得十分断然,只得由她去了。
赵家乃是承州郡望,百年家声,极为显赫。新任的承州巡阅使慕容宸因原配夫人已经病故多年,家中无人主事,急着要娶续弦。因听说赵家有位庶出的三小姐,芳龄已经二十有四,一直待字闺中。这个年纪还不曾许人家,于是慕容宸派人来向赵家当家二爷赵锦声提亲,有意娶作续弦。
那慕容宸出身草莽,原是米店店主人家的儿子,幼时家境倒还小康。后来多年战乱,父母相继亡故,家道终究败落下去。十来岁的时候很吃了一点苦,给人家当学徒、打杂,什么样的事都做过。后来拜师学过一些功夫,不到二十岁就去镖局当趟子手,混一碗饭吃。等到皇帝退位,他艺高人胆大,拉起一队人来,号称“护国军”。不出三五年,已经在邻近几个县里颇具声势。这几年天下渐定,他兵多枪多,于是被新政府任命为“承州巡阅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成了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慕容宸虽然仕途得意,手下也笼络了些人才,但毕竟新贵,总觉得有些威仪不足。于是慕容宸的“议事委员”王鹤云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娶赵家小姐为妻,赵家世代簪缨,门庭显赫,慕容宸若成了赵家的东床贵婿,自然于郡望十分有利。王鹤云自告奋勇,去向赵家提亲。
这日慕容宸从巡阅使衙门回府,贴身的长随报告说王议事已经等侯多时,慕容宸知道八成是为赵家的婚事,不知成与不成,忙连声道“请”。
王鹤云虽然六十有八,发须皆白,但耳聪目明,腿脚灵便,这门亲事做得十分得意,更禁不住步履轻快,进得正厅来,与慕容宸拱手见礼,说道:“给东翁道喜!”
慕容宸听见这句话,不由得一乐:“真成了?”
王鹤云道:“赵家已经答应亲事,不过说三小姐年来犯了旧疾,一直起不来床,只怕不能侍奉东翁巾栉,所以赵家的意思是,将七小姐许配给东翁。”
他这番话说的文绉绉,慕容宸只听懂了大半,于是呆了一呆,问:“七小姐是谁?今年多大了?”
这正是王鹤云得意的地方:“这位七小姐,倒是正房嫡出,据说才貌双全,是赵家最得宠的一位小姐。不仅作得一手好诗文,还曾经在乾平念过洋学堂,会说洋话。年方十七,正好比东翁小整整二十岁。”
慕容宸一听,双手连摆:“这可不成!我都能当她爹了。我是娶老婆回来当家,弄这么个毛丫头来,那不是要我哄她玩么?”
王鹤云道:“东翁稍安,这位七小姐年纪虽然不大,见识倒是异于常人。听说赵家是二太太当家,七小姐去年刚从乾平学堂里回来,年来常常帮着二太太操持家务,极为得力,赵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称颂。”
慕容宸想了一想,仍旧摇头:“这么一位千金大小姐,年纪轻轻的,为什么答应嫁给我?她肯随便嫁给我,我可不能随便娶。”
王鹤云素知这位东家为人粗中有细,极为精明。于是也不便隐瞒:“我隐约听人说过,这位七小姐在乾平的时候,就与一位秦家少爷相好。两人私定终身,谁知那秦家少爷竟然不守信诺,回家后就跟另一位吴家小姐订了婚,还带着那吴小姐出国留洋去了。赵家七小姐一伤心,书也不念了,回家来帮着二太太料理家务。这次赵家答应将七小姐许配给东翁,说不定其中就有这个缘故。”
慕容宸听见这么一说,才“哦”了一声,道:“既然是念过洋学堂的,那更瞧不上我这种粗人了。再说她是为着秦家的事一时赌气,我可不能当这样的冤大头。你去告诉赵家,我还是要娶三小姐,病了不要紧,我这里有俄国大夫,可以派去给她瞧病。”
王鹤云只得连声应是,又去赵家周旋。
![[转载]《承江雪》——匪我思存 芙蓉簟 匪我思存 小说](http://img.aihuau.com/images/02111102/02045739t018d70a7815697478a.jpg)
慕容宸连日忙于军务,把这等小事忘诸脑后。这日正逢城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耋老八十整寿,慕容宸亲自前去上寿。汽车驶出衙门不久,忽然一个急刹,慕容宸猝不及防,差点没撞到车顶篷上去。不由得说道:“这洋汽车就是不如咱们马车,动不动机括就出了毛病!”
那开汽车的汽车夫姓徐,原是慕容宸的亲信,此时回过头来,说道:“大帅,不是机括出了毛病,是有人拦车呢!”
原来慕容宸草莽出身,虽然现在统辖一省军政,可是对待乡里百姓,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经常有人拦了他的车子喊冤,他也经常就停下车子来,听人絮絮叨叨的说东家怎么欠了佣钱,或者是邻里占了一条沟的地,而他断起案子来,向来公平利落,并不袒护权贵,所以常常有人拦住他的汽车。今天听见汽车夫说拦车,还以为又是这样的讼案,摇下车窗玻璃一看,却见车前站着俏生生一个小姑娘,总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青衫黑裤,垂着一条大辫子,辫梢头系着红绒结,白白净净一张脸,看上去像是教书先生人家的女儿。他遇上女人拦车,却是头一次,不由得问:“小姑娘胆子也太大了,仔细被车撞着。你有什么事,上衙门找俞师爷吧,我这急着出去呢。”
那小姑娘撇撇嘴,说道:“你急,我更急呢。凭你有天大的事情,也得放下来——我家小姐要见你!”
慕容宸这才知道原来她是个丫鬟,不过这样胆大的丫鬟,倒是第一次见。他如堕云雾中,问:“你家小姐是哪位啊?”
那丫鬟将辫子一甩,说道:“我家小姐是哪位,你去见了不就知道了?”
慕容宸皱眉道:“那你家小姐到底有什么事要见我?”
那丫鬟道:“当然是有要紧事。”她又将他打量一眼,说道:“亏你是个大老爷们,婆婆妈妈只罗嗦个不停,真没男子汉气概。”
慕容宸戎马半生,被这么个快嘴丫头抢白,却是破天荒地头一次。只觉得哭笑不得,那丫鬟却自顾自打开了车门,说道:“往前开,我家小姐在韩记茶楼等着呢。”
汽车夫看了眼慕容宸,慕容宸心想,难道还能出什么蹊跷不成,于是点了点头。
汽车夫一直将车开到了韩记茶楼,那茶楼的伙计当然认得慕容宸的车牌,老远就哈着腰,说道:“今天大帅怎么有功夫,到小店来喝茶?”
那丫鬟抢先一步,对那店伙计道:“今儿大帅把这里包下来啦,从此刻开始,你一个闲人也不许放进来,不然的话,唯你是问。”紧接着将十块光洋递到那店伙的手里,那店伙看慕容宸面无表情,连忙又哈着腰引他们上楼。
这个时候不是喝茶的时候,茶楼里基本没什么人,二楼上皆是雅座,就更僻静了。慕容宸见那丫鬟前头走着,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方推开了阁扇的门,说道:“我家小姐在里头,你自己进去吧。”
慕容宸站在这门外,倒踌躇了一下,不过他向来胆大,更兼这是自己地盘上,倒也不担心是做成的什么圈套,伸手就推开门。
那门后原是一架湘妃竹的围屏,斜斜掩去了窗子,却见窗下站着一个人,方不过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却是素衣净颜,脂粉不施,不过那种艳光,简直如同明珠一般,温润而动人。
慕容宸虽然是个大老粗,可是出入风月场合,见过的美人也算无数,做梦也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见到这样一位佳人。他肚子里墨水有限,想来想去,竟然想不出一句话来形容,只是觉得,这女人长得真好看,好看得连她整个人,竟然都笼着一层淡淡的光晕,跟那西洋画里的仙女似的。
那少女见了他,脸上一红,但是远远的就按着西式的礼节,深深的鞠了一躬,低声叫了声:“大帅。”
慕容宸虽然被她艳光所夺,可是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便也立时回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只不便直看她的脸。所以眼观鼻鼻观心,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小姐既然约了我到这里来,想必是有要紧事,只不知道小姐所为何事。”
那少女脸颊晕红,过了半晌,才说道:“我姓赵,在家里排行第七。”
慕容宸哦了一声,说道:“原来是赵七小姐……”他性子虽然粗疏,可是反应极快,话音未落已经反应过来,大吃一惊:“你……你……是那个……赵家……七小姐?”
那少女脸上又是一红,说道:“正是。”
这两个字一说,屋子里静得鸦雀无声。慕容宸心想,我虽然派人去提过亲,但也是提的你的姐姐。虽然亲事不成,但是是你父亲回话说要将你嫁给我,我可没有妄求过你,难道就为这个,今日你亲自来兴师问罪不成?
那少女见他默不作声,更觉尴尬。可是她鼓足一腔勇气而来,可不能此时打了退堂鼓。所以虽然难堪的就快哭了,但是咬一咬牙,还是问出了那句话:“前日大帅遣人去回绝了堂上,可是嫌弃小女子姿容鄙薄?”
慕容宸纵然没读过多少书,可是姿容鄙薄四个字还是懂的,连忙摇手,说道:“不不!小姐误会了!我是觉得小姐年纪轻轻,又知书达理,配我这个粗坯,实在是可惜了了。”他看着她眼圈微红,几乎已经快要哭了,说不出一种可怜可爱,连忙解释:“我真的真的绝对没有看不上小姐的意思,要是撒谎,管叫我天打雷劈。今天小姐也见到我了,你看我这个人,怎么配跟小姐站在一块儿呢?而且我娶这位太太,回家是要当家的,你不知道,我家里上有老,下有下,不仅父母在堂,而且还有一位老奶奶,又有三个女儿,虽然有几房姨太太,但那个乱啊……成天介吵吵闹闹,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我都不愿意回家去……小姐你这么如花似玉的一个人,又还这么年轻,我真不能让你来趟这种混水……”
她本来窘得要哭了,听到他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何,却忍不住噗得一声笑了。虽然是大家闺秀,笑不露齿,而且立时拿绢子掩了去。但慕容宸见她眉眼弯弯,这一笑竟如明月初升,光华照人,也禁不住呆了呆。
“大帅家里的情形,我也听说过。抛开这些不论,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娶我呢?”
她的声音虽然细如蚊蚋,可是听在慕容宸的耳中,真如惊雷一般,一字一字,轰轰烈烈,虽然逊清之后,民风渐渐开放,可是他做梦也没想过,自己有生之年,会被这样一位少女,当面问出这样一句话来。一时竟张口结舌:“这个……”瞥见她眼底泪光盈然,那一个“不”字,可真如千钧重一般,无论如何出不了口。看着她眼睫微微颤动,仿佛无限柔情,只觉得头晕脑胀,仿佛全身的血都涌进脑子里去了,脱口道:“我本人当然是愿意娶小姐的。”
她展颜一笑,说道:“那么咱们就这样说定啦。”
一直走出了韩记茶楼,慕容宸才狠狠得拧了自己一把,直拧得自己皱眉。汽车夫迎上来,看他脸色阴暗未定,忙问:“大帅,出了什么事?”
慕容宸也不知道该喜该乐,该哭该笑,只觉得自己稀里糊涂,似乎就被人下了蛊似的,一见了这少女,竟然三言两语,就被她说动了去。听到汽车夫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事,忍不住长叹一声,说道:“还能有什么事?终身大事。”
他回到府中之后,又请了那王鹤云来。王鹤云听说他要再次向赵七小姐提亲,略带诧异的道:“东翁不是嫌弃七小姐年幼……”
慕容宸道:“年幼什么啊!糊涂胆大!”说了这句话,又叹了口气,说道:“我定是老了,一见着漂亮的小姑娘,就稀里糊涂,什么话都乱答应人家。”
王鹤云笑道:“东翁方当盛年,何出此言?既然东翁改了主意,我这便去赵家走一趟,请东翁放心,这事,鹤云务必替您办得妥妥当当。”
王鹤云这桩差事确实办得漂亮,赵家一点头,便选了吉日送文定,然后接着便是纳彩,过礼,等送了龙凤贴,便定下日子过门。慕容宸对这桩婚事很是郑重,虽然是续弦,但三书六礼,聘礼甚厚。赵家自然更不轻慢,陪奁亦丰。到了送嫁妆的那一日,满城是人看。只见一抬抬的描金漆盒,除了常见的子孙箱、子孙盆、梳妆台之类的东西,更有系着红围子的西洋式落地钟、描金的西洋家俱、西式沙发、靠椅……看得人啧啧称奇。皆说道:“咱们大帅,这回娶了位洋小姐呢!”更兼那多嘴多舌的,却说道:“赵家拿自己女儿巴结慕容宸,真是舍得血本。”还有那一等刻薄的,说道:“你们懂什么,赵家这七小姐跟人私奔,又被人甩了,早就是残花败柳,不然哪肯嫁给慕容宸作续弦?”
馨雪坐在花轿里头,却是一身大红的绣衣,只能看见盖头底下的重穗,微微的摇动。她虽然穿的是旧式的新嫁衣,可是脚底下并不是绣花鞋,而是一双红色的漆皮鞋。赵太太原说,天底下哪有新娘子不穿绣花鞋的?何况承州的规矩,这双绣花鞋最好要新娘子自己绣,将来的日子才是步步高升。赵太太原本忧心女儿不会绣花,所以早早预备下几双大红绣鞋,都是挑了福寿全归的太太替她绣的。谁知馨雪脾气也拗,说道:“我就要穿皮鞋嫁人。”
赵太太原本执意不肯,说道:“哪里有这样的规矩,被人看到还不笑话?”
馨雪说道:“本来就已经是笑话了,还怕别人笑话不成?”
赵太太知道她的伤心之处,实在不忍心再拗着女儿,便忍着由她去了。
馨雪穿了大红漆皮鞋,一路踏着红毡走到花轿里,幸好裙子甚长,根本看不到新娘子的鞋。她坐到轿子里,心里却像是一下子踏实下来似的,本来自从文定,她一直觉得悠悠忽忽,整个人像半悬在空中,可是现在是得脚踏在实处了,尤其外头的鼓吹那样热闹,沿街全是放着鞭炮的声音。不管自己是抱了什么样的初衷,但这条路是自己选定了,没理由也不可能再回头。
她坐在轿子里,只听见前头炮仗惊天动地的响起来,直将鼓吹的声音全压下去,便知道是花轿已经进了门。过得片刻,果然轿子稳稳停下来,只听外边又是一阵喧哗,紧接着鼓吹之声大作,她虽然盖着盖头,但仍旧知道有人掀开了轿帘,却是接亲的全福太太,搀了她下轿子。
婚礼极是繁琐,馨雪被两位全福太太搀着,听着赞礼官又唱又说,好容易新人拜完了天地,送到上房里去,一堆亲戚朋友,都涌进来看新郎揭盖头,慕容宸今天穿了一身华丽的长衫,胸前系着红绸带,被大家簇拥着进来,他虽然很高兴,倒作为一个新郎官,到底还是有几分腼腆。所以亲友们更加要起哄:“大帅拿着枪杆子手都不抖,为什么这个时候,连手都在抖啊?”
“那哪是抖啊,那是乐的!”
“快快掀了盖头,让我们瞧瞧新娘子!”
“就是!听说新娘子是承州城里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快让我们瞧瞧!”
慕容宸一刹那也不知道是喜是乐,反正手一探,就用称杆将盖头给挑了。旁边的全福太太高声道:“好!称心如意!”奉了如意在新人的枕上压住,佣人又奉上青果茶,吃了这个茶,叫“亲亲热热”。
这么一套繁文缛节,新娘子自从揭了盖头,自然是垂首默坐,一直到伸手接茶碗的时候,才略微抬起头来,这一抬头,满屋子当然都是笑声。更有人止不住乐:“快来看!好漂亮的新娘子!”上房里里外外,却早已经是水泄不通。
慕容宸在上房里只待了一会儿,就出去招呼客人了。馨雪陪嫁的两个丫鬟,四个老妈子,都在这里陪着她,周旋着招呼客人。承州的规矩闹洞房闹得很厉害,所以客人一拨一拨的来,除了女客更兼有男客,说笑打诨,千方百计,要逗新人一笑。
慕容宸虽然被一堆朋友拉住了,可是心里却有点委实放心不下。没过一会儿就对自己的副官吴柱国使了个眼色,吴柱国便上前来,附耳问:“大帅可是有什么吩咐?”
慕容宸低声道:“你去看看,新太太那里是谁管事,叫她来我有话说。”
吴柱国答应了一声,走到上房去,只见里头挤的水泄不通,都是看新娘子的人。他便拉过送亲来的全福太太,问了她几句话。那全福太太便走到馨雪旁边,对站在那里的锦弦道:“大帅有点事情,叫太太身边的人去一趟,我看还是你去吧。”
锦弦点了点头,便悄无声息走出来,跟着吴柱国走到外头,不一会儿果然见着慕容宸从酒宴中出来。见到了她,慕容宸不由怔了一怔,说道:“是你?”
原来正是那日拦车的那个俏丫鬟,锦弦笑吟吟蹲身请了个安,说道:“姑爷,那日对您多有得罪,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别放在心上啦。我也是受我们小姐差遣,怕办不好差事挨骂。”
慕容宸笑了笑,说道:“现在咱们是一家人,别说这样的话。你们小姐只怕早起就没吃什么东西,我这里的厨子也怕不合她的口味,所以我差人去俄国领事馆里,请了他们的大师傅来做了面包。待会儿客人散了,你打发人去厨房拿给你们小姐。家里没有当家的人,我怕别人兴兴头头,摸不着头脑,反倒生出事来。”
锦弦听得这番话,忍不住笑着又请了个安,说道:“那我替我们家小姐谢谢姑爷啦。”
她回去上房之后,满脸笑意,直看得馨雪满心疑惑。幸而前面开席,客人们都去吃酒席了,上房里只有几个老妈子陪着她们。馨雪便问:“你这丫头,什么事乐成这样?”
锦弦悄声笑道:“咱们新姑爷,真是会心疼人。惦记着小姐早起没吃什么,又怕您吃不惯这里的东西,巴巴儿把我叫去了,说他给小姐留的体己面包在厨房里,让我过会儿打发人去拿呢。”
站在旁边的芸香忍不住噗一声笑出声来,说道:“这么一个大老粗,倒是挺细心的。”
馨雪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想到这件事情,觉得慕容宸这个人,也不失几分可爱之处。
这天中午她就吃了几片面包,喝了两杯热茶。到了晚上的时候,前头搭的戏台开始唱戏,府里越发显得热闹。慕容宸却腾出功夫来,亲自来接了她往花厅里去,一家子见礼。
馨雪虽然拜堂的时候就拜过了婆婆,但是一大家子其实还是没正式见过。眼见的一位老太太坐在上首,知道这是婆婆,便老远一躬。慕容老太太虽然是个老派人,可是见了这样温柔美丽的新媳妇,早忍不住眉开眼笑,说道:“别闹那些虚文,好孩子,快坐下。”
馨雪却以为,有高堂在堂,自己并无坐的道理,却见慕容宸坐下来,又对她说:“你也坐吧。”她看见丫头老妈子抱了红袱来,才知道是要见礼,锦弦最是机灵不过,于是扶着她的手,就坐在慕容宸右侧。一时间几个乳母带了四个孩子进来,都是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二三岁,小的却只得两三岁,还被乳母抱在怀里。大小姐毕竟年长些,不用乳母说话,便先跪下去,低声道:“见过母亲大人。”
馨雪虽然出身大家,不过毕竟年轻,好在带来的几个老妈子都十分得力,连忙搀起来,连声道:“大小姐请起。”余下的几个孩子也在乳母的指点下磕了头,赵家打听得这边有四个孩子,也早早预备有礼物,此时便用托盘呈出来,交给四个乳母,却是四份一模一样的“笔锭如意”。
孩子们见过礼,慕容宸便微微踌躇了一下,说道:“请几位姨太太来见过太太吧。”
(未完待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