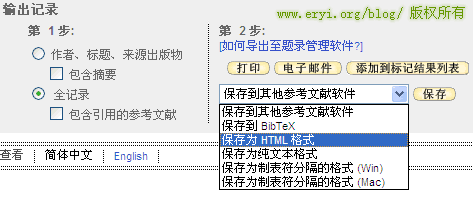我们的生死/柳红
2008年3月17日星期一,载《癌症康复》杂志2008年第2期
儿子生前,我们没有机会面对面地讨论死后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怎样送别,葬在哪里,墓地的样式,想起来就遗憾。非凡子尤,定知自己时日不多,縈绕在心者,必是妈妈如何承受死别之痛。所以,他才没能和我商量。还是怪我,没有成长到足够高度,让儿子放心。只记得,最后一两天,子尤几度抬起左手,伸出一个食指,指点着我,一字一顿用力地说:“妈妈,一-刻-也-不-要-离-开。”他是怕我错过,错过分别的时刻。
子尤死在我怀中。想起来,就觉得他也是幸福的。生于妈妈怀抱、死于妈妈怀抱,这世上有几人?只是,他给妈妈的痛苦、教育和考验来得太深、太急、太重。妈妈我,情何以堪?命何以立?身何以安?
我们俩人讨论死亡最多的是2005年5-6月,那时,他刚过15岁生日。他在一次抽搐之后,口述一篇《生死间的随想》,其中说到:
“由这次梦境般的经历,我想到人濒死时的感受,他们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能表达,但家人从表面上看来已是一派死状,家人亲切地哭与呼唤在这些人听来明明白白,由近到远,由清楚到模糊,然后他们的灵魂就从身体里出来了。肯定有灵魂,这是能证明的!”
那时,我们住在北大校医院,每天,我用轮椅推着他在校园、在未明湖畔走来走去。有说不完的话。
2005年6月1日,他对我说:“此生的意义就是把该想的事想明白,来或走你都已经无所谓了。我基本就到这境界了。李敖一生不出台湾,别人替他遗憾,而实际上他已经将自己的舞台定位在历史之中,不局限在力所能及,所以他的思想已经使他对于生死看得很轻了。他死了,仍然活着。一般人说“我没活够,我不想死”,是因为他身体上干的事情永远也干不够,你的思想却可以满足你。人这一生重在一个“悟”字。”
子尤生前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生亦漂亮、死亦漂亮》,这是《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一书的书评。他写道:
“生病以后,我渐渐认识到,人活着是为了感受人生,明白人生的意义,怎样活比活本身更重要。崔雅得到上帝的宠爱,在疾病中升华,活明白了,圆满地完成了人生的旅程,也就是提前完成任务。人们经常策划庆典像结婚、毕业、生日等等,我倒觉得,不如策划一下死日。崔雅是在众人的爱中安详死去的,没有一丝遗憾。她死得漂亮,风雨大作,天地为她送行!这样的死,有什么不好?她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书名是“超越死亡”,谁做到了?崔雅做到了。她真正超越了生死的狭隘界限!
四十岁离去,太年轻了,但她获得的,比许多八十岁的人还多!她不需要我们给予她什么,相反,用自己的行动,带给我们一切!所以在感动崔雅之余,我们对于如何评判人生的价值,应该好好深思。”
这里,子尤分明在写自己。超越死亡,子尤,做到了。
记得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社五名队员在登山中遇难。一家人吃饭时聊起来,我为这些生命连连惋惜,子尤却说:他们多幸福!能死在自己热爱的山上,死在登顶途中。……他的态度把我震住了。此时此刻,我的眼前还是子尤激动地饱含眼泪的神情。那年,他12岁。
只能说,对于生死,他有先天的了悟。连这,也是我在子尤走后才一点一点认识的。
他说:“我选择可能快死时去西藏,到雪山,赤身裸体迎接死亡。……我很喜欢过去人死了的那种仪式,与自然挨得近,不是指现在的追悼会。”
和对死亡的超然态度相联系的是,无限地热爱生,热爱世界的一切。以至于他说自己“活得欣喜若狂”。
虽然病情很重,还是没有想到在2006年10月22日凌晨,子尤死了。子尤最后一句话说:“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
一位知子尤者说:“好戏在后头!”
10月24日送别子尤。朋友说:“子尤是诗人,我们要以诗意的方式送他”
于是,我们决定烛光、鲜花、诗歌送子尤。
复兴医院的告别室破旧阴暗狭小。两个小时之后,在亲友的手中,化腐朽为神奇。子尤巨幅彩色像在正面,红衣、长发。红烛燃火,映出金色。上方高悬我妈妈写的五个大字隶书:“永远的子尤”。我把家中红色的窗帘全部带来,包出红色的灯,红色的挽幛,红色的桌布,子尤身上是红色的盖被……告别室里回荡着子尤的声音。
两个小时的告别,分成了两段。第一小时,人们手拿一束玫瑰花走来,向子尤告别,把花瓣铺洒在他身上;第二小时,同学和朋友围在子尤身旁,随着一个女生的指点,进入他的生命历程,先进入了小学,读他的诗,唱那时的歌;然后进入中学,读他的诗,唱他的歌;……
头一天,我把长发剪成短发,朋友为我买了一身紫色镂花丝绒旗袍,还有绣花鞋。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子尤的身体在一起,我要怎样的表现才让他满意?
2004年6月25日,子尤上手术台的那天早上,曾经嘱咐我:“妈妈,你要是端庄的、典雅的、井井有条的、忙而不乱的,你每次歪着脖子驼着背从外面跑进来,都给我丢脸。”遇到世上任何一位优美优雅的女人,子尤都要对我说:“妈妈,你要像她那样。”他最不喜欢我在人前哭。有一次,朋友来病房探望,讲起我们刚刚经历的一场生死考验,大家都跟着我哭了。只有子尤笑着。事后,他批评我,说:“我是笑着让别人哭,你是哭着让自己哭。”姥姥每天来病房送饭,神情凝重。子尤不愿意她那样。她总是对我说:“你要笑。”边说,边用两只纤细的手,提起我的嘴角向上弯。
这就是子尤。他有一颗高贵的心,十分美好。我只有追随他,上升、再上升。他在去世前不久还说:“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是一个要让我妈妈提升的人。”
我甚至于觉得,我的儿子除了享受、展开他的人生之外,就是在用他的生命哺育我。
所以,我只有优雅地挺立。
站在子尤身旁,抚摸他光亮的头发。任伤心泪流,却不失态。我俯身和子尤说了好多悄悄好,告诉他谁来了,仿佛我们在病房里接受亲友的探望。朋友说那一天,我们母子是一幅绝美的画面。
子尤吾儿,你满意吗?
有朋友对医院领导说:你们医院的告别室,历史上只有一天辉煌过,那是因为子尤。
子尤的骨灰住回家里。我们朝夕相处。没有儿子的生活,只有忍耐,用新的爱、饱满的生活内容和工作来填充。一年之后,2007年10月15日,安葬骨灰。
墓地选在北京昌平的凤凰山陵园。此地四面环山,有燕山、太行山,临居庸关长城,玉带---响潭水库在侧。陵园,要么古琴悠扬,要么佛音缭绕。小小子尤墓在草坪中央。地上嵌了一块汉白玉,中间是子尤的亲笔签名,四周是子尤诗句:
“生亦漂亮死亦漂亮”
“北京城,
你这苍老的风
我将陪随你一生。”
“别人让天空主宰自己的颜色
我用自己的颜色画天。”
“一切的故事
其实都是相遇然后分离。”
姥姥手书,刻金字;立着的石碑上,是一方名章“子尤”,地上有两条玻璃条凳,一条上面印满“自由”;一条上面印满“FREEDOM”。子尤墓和韦君宜、杨述夫妇墓相邻,还有一棵柿子树在旁边。
通常,周六是我去看子尤的日子。先乘车到南口,然后步行,大约10公里,绕山而行。秋天,采黄色的野菊花,红色的黄栌,捆成一束献给子尤。冬天,我也兴致勃勃,看枯树秃枝,看山峦变化。远远近近地,狗叫声不绝于耳。孤身一人却不孤单,不枯燥,只想有人和我分享。而那个分享的人,就在前面等我,想着就满心安慰。
每一次去,拿块毛巾,提个桶,擦净石碑、玻璃、长凳。带本书,带个本子,坐在凳子上凝神、读写。天好时,可以躺在石碑上迎面晒太阳,做做俯卧撑,扭转拉伸身体。看喜鹊在我们跟前的柿子树上欢快地飞来飞去。也常常和其他纪念亲人的人攀谈。亲人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子尤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这一生,只要我走得动,都会这样走着去看儿子。
春分时节,我想种些花儿,四季花开,此起彼伏。昨天去,撒了些香菜籽,期待嫩芽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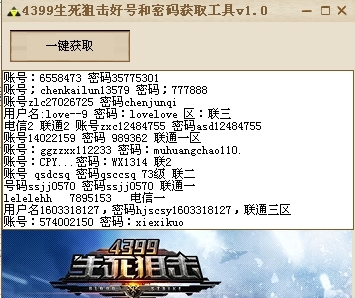
我的生,因子尤的死,而有了不同的意义。我们心心相印,我们一同前进。
前几日路过扬州,看到“视死如归”一解,即:死是永生。这个解释我喜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