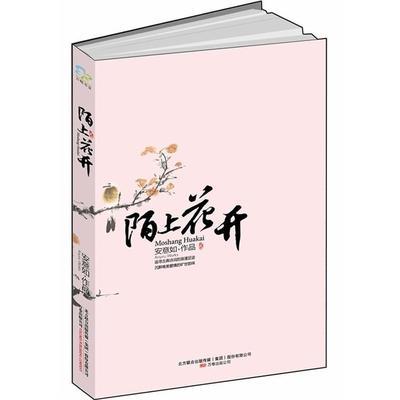邂逅安意如,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弘文人文馆”的漫漫古典情系列,零零总总十八本,我单单拎出她的来,一读,便爱上。
之后,她又写《陌上花开缓缓归》,写《惜春纪》,我都一一读过。这是一种惯性。我与作者,一旦结缘,便想一直维系。而如今,这徽州女子居于京城,携《观音》走来的时候,我却未能及时与她神交一番。直到最近,与几个博友聊起她,决定组织一期沙龙,我才翻出《观音》来看。读罢掩卷,长舒一口气,却半晌无言。
回首看来,这重延宕,竟极有暗示性。
因为,我会失望。
还未翻看书,先看封面上那一行字:“戏写世道人心,人生百态,戏也是音。观音,观世间疾苦繁华,声声入耳,一一在心”,知道她要说戏说人生,我却一阵心惊。我不听戏,不看戏,却深知戏曲博大精深。它从来都要伴着鼓点,依着角儿,展示于舞台之上,呈现于大众之前。安意如要借助文字这个唯一的媒介,来述说一种兼具视听性的表演艺术,何其困难?
看前言,明白她有褪石露玉的初衷,也听她坦言她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挫折,心惊之余,倒生出钦佩来。然而我所钦佩的,只是安意如的初衷以及她迎难而上的勇气。平心而论,《观音》一书,确实是安意如的失策之作。
对,是失策,而非失败。失策与失败,总还有一线相隔。对于一本失败之书,我向来懒于评价;而失策之作,却比成功之作更值得玩味。
闲言休叙,我们来入正题。
我说安意如失策,先是失策在“观音”二字上。诚然,作为一本书的书名,它鲜明醒目,却又透着一层朦胧暧昧,深得广告真昧。然而,“音”之用“观”,就如同上阵带笔,考试用枪,全然失了法度。或有人言,此乃通感。我并不否认音可以观,只是想指出,这“观”与“音”之间的间隙和疏离,从一开始就暗示着安意如此书的失策。
安意如最大的失策在于,她选择了“戏曲”这种体式作为评论对象(在此我忍不住要偷笑一下“元戏”这一提法,呵呵,且住,且住)。对戏曲的截取言说,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从前言看,安意如对戏曲的理解是很独到的:
“体会杂剧是另一种情味。当你习惯了唐诗宋词的优雅缠绵之后,你几乎会自觉地抵制这个世俗化的产物。它很难符合高雅清淡的口味,显得直白低俗,不耐咀嚼,有时候还充满了龌龊和猥琐。
它不像诗词歌赋那样懂得撩拨,欲近还远,善解人意,它太不懂掩饰,直至会搞坏你的胃口。可是当你进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孤寒由来有因。杂剧本身是一个寂寞的产物。是一群有志难伸,或者在我看来是活该一辈子不得志的读书人派遣寂寞、消遣社会的产物。他不可避免地太过用力,流露出些许尖酸刻薄的个人情绪。”
这段话说得虽有些刻薄,但也不失灵性。今人谈古,无论是谈文学还是说历史,一旦过了唐宋,总不免沮丧。元朝统治者从《易经》里扒出个“大哉咸元”标榜自身,大则大矣,却始终掩不住那股穷兵黩武的莽夫气。在上者不文,在下者受累。文人不得不直面“九儒十丐”的社会地位,沦落市井。杂剧作家处境如此,作品也就免不了带有“孤寒”之气。在这一点上,安意如目光如炬。她看表面看得精准,看内里也看得通透。
可惜的是,安意如抓住了杂剧的魂,却笔锋一转,丢开气质写起爱情来。爱情,总是依存在故事里的。说是故事,就要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就要有情节的起伏延宕,就要有人物形象。可这恰恰是杂剧不擅长的地方。你看《长生殿》,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自唐以降,诗文里写过,传奇里写过,词曲里唱过,说书人讲过,谁不知杨李二人之间有这么一段祸害了大唐国祚的绵长深情?你看《雷峰塔》,谁不知那断桥边,白蛇遇上了书生,衍出一段人妖之恋?
中国戏曲里的故事总是旧的,旧得离谱。即便新翻出几个人物,演到深处,仍不离旧时桥段。中国戏曲里的精华,在情字上。生与旦的一段段缠绵悱恻、婉转蕴藉的唱词,正是这精华的载体。分析这些,安意如最是擅长。可她偏不如此,转而指点起世事人情,以今人看古人,以文人说市井,吃力事小,惹人哂笑事大。安意如兀自清高出尘,却忘了当时这“孤寒”剧作的拥虿者,多是些市井小民,庄稼百姓。所以,安意如在看《长生殿》和《梧桐雨》时出离愤怒,在看《雷峰塔》时耿耿于白蛇的偷盗行为,实在是白白生闲气。面对市井的文学样式有它自己的存在范式,安意如拿文人的标准来衡量,是用错了尺。
可叹的是,安意如没能点出戏曲受众的市井一面,却将坊间俚语学了个十成十。什么“花痴书呆子”,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想那些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养在深闺的大小姐说出此等话语,我就忍不住冒鸡皮疙瘩。何必,何必。虽说为文须放荡,笔下恣肆时也要谨记过犹不及。
不过,《观音》也并非一无是处。《牡丹亭》、《倩女离魂》和《救风尘》几篇,还是可圈可点的。
《救风尘》一篇中,安意如也用了市井俚语,却用得恰好。分寸一丝不差,嬉笑怒骂,收放自如。此时的安意如与数百年前的赵盼儿交相辉映,两人身上那种女中豪杰的气势,竟谁也不输于谁。
《牡丹亭》、《倩女离魂》两篇,应是安意如的本色之作。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辞》里说:“情不知所以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至也。”

数百年后的今天,安意如以她女子独有的细腻,写下《牡丹亭》的题记:
“爱情,是往返的幻觉。我馈赠于你,你回馈于我。
放不开,那命运鉴定的爱情;躲不开,这注定凄艳的荣幸。
所以——就让我以死来殉你,请葬我与此,等来年春动,你以生来赎我。
经书苦口婆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间男女置若罔闻。”
这一段尽显安意如的才气和本色,即使与汤显祖的题辞放于一处,也不现半点怯意。
杜丽娘在游园时,看着满园春色,唱一曲[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
《红楼梦》里,黛玉隔墙听到这戏文,玩味良久。
它好,好在纯粹。只关情致,无关其余。
即便有痴儿男女,也只是这情致的陪衬。
在策划沙龙的时候,紫竹曾经提及,安意如是否该来个华丽转身?读过《观音》之后,我突然无比怀念那个《人生若只如初见》中的安意如,怀念她轻启檀口,说一句“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野,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
俱往矣。
如今,我也只能效颦,叹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