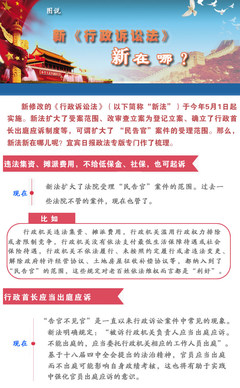新《刑事诉讼法》73条意味着什么
(以“‘73条’意味着什么”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1期,发表时有删节)
仝宗锦
今年人大会议表决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于明年正式施行。围绕这部法律修订,特别是其中73条引发的讨论,至今依旧不绝于耳。对比旧法文本,其实新法总体而言谈不上更加糟糕,不少地方,例如非法证据排除、律师阅卷会见权、证人出庭等问题甚至还有相当进步,热议的关键原因在于,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变迁,人权保障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渐深入人心与国家在打击犯罪方面愈来愈严峻形势之间形成的深刻矛盾。
从79年刑诉法制订到96年修订再到今年这次修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一方面是权利意识增强和普世价值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日渐复杂。在此大背景下,法律虽然主动或被动承担了保障人权的功能,但总体上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面目出现的,而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则仍重在打击犯罪而非彰显人权价值,尤其在当下国内维稳局势下更显突出。正如王兆国副委员长在草案说明中提到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具体来说,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贿赂等犯罪的有效惩治,高科技条件下技术侦察手段的采用等等,亟需在法律上作出回应。
引发公众热议的73条是:“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此条虽然仅仅针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特别重大贿赂”三类犯罪,但由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维稳名义下渐有口袋罪趋势,此次明文列举突出,导致公众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73条的要害不在于通知家属与否,虽然上述条文中“无法通知”措辞仍存在侦查机关可能规避的广阔空间,而在于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家庭监视居住且公安机关可独自决定的新型强制措施。旧刑诉法57条虽然也提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仅仅针对居无定所的嫌疑人,因而法律本意实质上是为那些人提供方便。但新法对有居所的三类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质上是基于侦查需要的剥夺自由,因此74条才对此折抵刑期。这实质上是双规从党员干部到一般民众的扩大化,以及收容审查的死灰复燃。
公安机关侦查过程的顺利开展与侦查时间长短和侦查过程是否受到外界影响密切关联。理论上说,嫌疑人在侦查人员手中控制时间越长,控制空间越封闭,那么侦查效果越强,同时,嫌疑人人权也越可能受到侵犯。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与否其实主要体现为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之间的价值选择,具体来说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为对侦查过程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规定上。在旧法的强制类型序列中,监视居住本来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类型,它不似拘留和逮捕那样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仅是限制自由。因其较轻,所以时间可以较长,最长可至半年。而新法73条的规定,使得旧法拘留最长37天期限内无法完成侦查的,以及达不到检察院批捕条件的嫌疑人,现在可以仅由公安机关一家独自作出剥夺长达半年自由的决定。这意味着公安机关权限的极大扩张。
尽管73条只涉及三种犯罪例外,但侦查机关完全可以以涉嫌其中某项罪名先行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然后再改变罪名侦查并提交公诉材料。去年公布的刑诉法草案说明提到,“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多发生于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况”。而73条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恰恰是发生在看守所外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侦查机关一家掌控的地方,在律师难于介入的阶段(因上述三类犯罪律师会见需经批准),如何能够避免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无疑将面临极大威胁。

有人用美国《爱国者法案》等来为刑诉法73条做辩护,认为针对此种特殊犯罪的特殊对待是完全合理的。这一逻辑和用美国对言论自由也有限制来证明我们规范言论也是合理的是同样的逻辑。首先,美国那些法案一直广受各界批评;其次,那些法案多数是911事件后因应恐怖主义新态势的,所涉范围和程序被严格限制;再次,美国公民权利有强大宪法保障,包括律师、媒体等等。实际上,美国《爱国者法案》等一系列针对恐怖主义的法律,是某种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立法,我们当下的刑诉法修改,其背景仍是常态政治。同时,考虑到转型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必定会伴随政治性自由的吁求。诸如煽动颠覆等实体罪名的存在,更会因当下程序性法律的授权而可能被大肆滥用。
其实,任何法律的修订,无论重视秩序还是强调自由都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立法博弈过程中,找不到公民权利的守护神。公安部门希望扩张警察权自不待言;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部门,但同时也是公诉机关;法院有限的解释权既无法触动前二者,更在于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大本应代表人民,但间接选举的多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大的合法性和责任感。
实际上,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羁绊和法律实施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关系,恰恰是刑事诉讼法修订叙事中的核心问题。理想的刑事诉讼过程,需要摒弃现有的公检法三机关流水线作业模式,代之以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诉讼结构。然而,这样的举措,由于牵涉到三机关权力的重大再分配,其实已经脱离了司法改革的技术化轨道,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
通过一点一滴的技术改进,最终达到理想的司法改革目标,这是长期以来法律职业群体的一般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三十多年来的几次司法改革,从80年代开始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96年刑诉法修订引起的刑事审判方面的变化,再到新世纪以来司法改革方案的讨论,包括法律职业化的强调,最终是改革越来越走向细节化,越来越不愿去触碰根本的体制问题。2003年前后,中央研究了很多问题并提出了很多方案,真正涉及了部门之间司法权力的再分配。可惜持续到2006年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就草草结束了。此后司法改革就只涉及部门内部的调整。三十多年来的司法改革过程,实际上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如果不认真对待政治体制改革,理想的司法改革目标也难以达成。
不过,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就像宗教学者奥特所谓“我们时代的上帝问题”,是“不可言说的言说”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