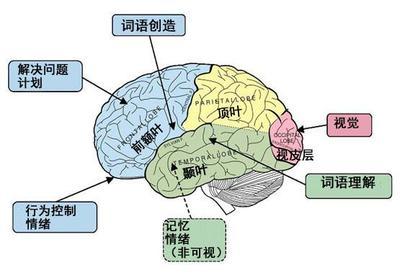扭痧,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人一旦在高温季节有痧气后,就是用手在脖子上扭,从而扭出一条条紫红的、长短一致的“萝卜条“,这是过去农民用来治痧气的最好方法。效果虽好,但扭起来的痛真有点受不了,现代的年轻人大都不敢接受,他们一有痧气就去医院配点痧药,吊一下盐水,花它百上百落钱并不在乎,只有一小部份老年人一旦发痧,还在跟自已的脖子过不去。可是在我们童年的时代,在炎热的夏日里,身体一有不适,大人们动不动就给我们扭痧,为了省钱,怕痛不想扭也得扭,逃走了抓住后还要扭,这种扭痧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村子里,四叔家屋旁有一棵好大的枣树,它几乎把四叔家的一半房子遮了起来。一到夏天,枣树上都挂满了青青的枣子,树下是纳凉的好地方。夏天的中午,村子里的人们在家里热得受不住,都提一条小马凳,手上端着一大碗黄仓仓的麦细饭,咸菜汤冒着腾腾热气,麦细饭上还放着一蓬香喷喷的乌干菜,当时的情景绝对不亚于鲁迅先生笔下九斤老太一文中的描述。吃完午饭,一些人在懒椅上轻轻地哼着:知了喳喳叫,懒惰人家困晏觉,勤劳人家拔荒草。随即睡去、呼噜声此起彼伏,和知了一比高低。不睡午觉的人们利用中午休息,相互在脖子上扭痧,呱嚓呱嚓的扭痧声在枣树下响成一片,有几个小孩不肯扭,做父母们的硬是把孩子的头、手、脚紧紧捏住,一边扭,一边在训斥:小棺材,侬猛太阳要勿要去晒哉?!要勿要去晒哉?!小孩们痛得大声地哭喊着:呵哟姆妈!我痛死了!我不要扭了!。但一旦身子舒服了,孩子们又把扭痧的痛苦抛在脑后了,不管烈日炎炎,有的去玩水、有的去小河里摸蛳螺和鱼虾、有的去棚知了、有的去竹园里翻跟斗、、、、、、。我小时候身体也不是那么好,一到夏天经常发痧,母亲的手小,扭痧时有针刺一样痛,每当母亲给我扭痧,我是比较听话的小人,总想把痛忍住。开始还好,扭好二三根“萝卜条”,实在忍不住哭出来,而且哭中有笑,笑中带哭,就这样勉强把痧扭完为止。村子里扭痧最好的师傅要算三叔婆,因为她给人家扭痧速度不但快,而且不太痛,人家扭痧用一只手也感到很累,而三叔婆二只手同时给人家扭痧。三叔婆扭痧的动作特别麻利,看上去象左右开弓,一上一下,声音悦耳动听,扭出来的痧条长短宽均匀。三叔婆扭痧还因人而异,给男人扭出来的痧条宽大粗犷,有一种阳刚之美;给姑娘们扭的痧条细巧恬静,显得有点妩媚。每当“双抢”大忙的时节,由于气温高,劳动强度大,发痧的人比以往更多。下午休息,树荫下坐满了汗流浃背的人们,要三叔婆扭痧的人排着队。三叔婆身体素质很好,平时不会发痧,但每当给这么多的人扭好痧,自已却发了痧。后来三叔婆去世了,到枣树下纳凉的人也少了许多。我本来也经常叫三叔婆扭,自从她离开人世以后,我觉得不会有第二个扭痧象她那样好了,于是我学会了自已给自已扭痧。后来我感到,自已给自已扭痧有二个好处,一是对自已的脖子不会扭得那么狠,二是扭扭停停,不痛不痒,照样能起到治痧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准有了质的飞跃,于是农村里这种扭痧的现象也渐渐消失了。现在的父母再也不会下狠心在孩子又嫩又细的小脖子上扭痧了。现在家里条件好了,尽管在盛夏酷暑,因为家有电扇空调,很少看到小孩子在烈日下玩,因此现在的孩子头上不生疮,身上不会有痱子,相貌象纸上画的一样可爱,不象我们小时候,头上经常生疮,身子上的痱子似厚袋皮。在我的右耳朵上方,至今还留有一块癞头疤哩!src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