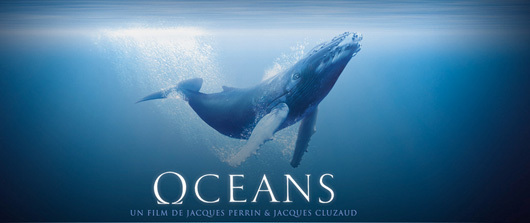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人性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杨文榜
摘要:唐传奇《莺莺传》是一篇感动人心的作品,然而小说中作者元稹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庇护使得这一文本略显怪异。在后世的改编之作中,张生的形象得到改变,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情感礼教人性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就是这样一篇以情动人的作品。
《莺莺传》的故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男主人公张生,温良朴实,风度翩翩,行事非礼不为。年二十三尚未遇到合于心意的少女。他东游蒲州,寓居普救寺。巧逢远亲崔门孀妇郑氏携儿女返长安,亦借住寺中。这时,突然发生了节镇驻军骚乱,张生求友保护,郑氏一家才幸免于难。乱定,郑氏宴张生,命其女莺莺出谢,张一见倾心,但莺莺贞慎自持,张没有机会表达爱慕之情。后得婢女红娘相助,为之传送《春词》,莺莺遂以彩笺题《明月三五夜》诗回赠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喜出望外,乘夜攀杏花树逾墙而往。莺莺出见,端服严容,责以非礼。张生不知所措,感到绝望。谁知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她又主动到张生处幽会。临别依依,但去后又不通音问,张生赋《会真诗》抒相思情怀,莺莺方与他重聚于西厢。张生牵于功名,入京应试。莺莺预感将有不幸,愁容惨淡。翌年,张生落第,滞留长安,寄书莺莺致意。莺莺复信,情词哀婉缠绵。友人知情,无不惊叹。诗人杨巨源为咏《莺娘诗》,元稹写了续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小说结尾,写张生在女人祸水思想的影响下,忍情地与莺莺分手,一年后,女婚男娶,各有所归。张以旧情欲见莺莺,为莺莺所婉谢。
元稹在中唐与白居易齐名,是“元和诗体”的重要代表作家,他所写的艳诗和悼亡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而偶一出手写成的传奇《莺莺传》更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唐代传奇小说。元稹深谙艺术创作的奥秘,运用优美、细腻、含蓄的文笔描写了崔、张恋情,他所塑造的少女崔莺莺形象十分真实感人!
不妨让我们看看作品中的具体描写。作者写莺莺被其母郑氏催促出见张生就运笔不凡:“常服蒞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①这样,少女的羞涩内敛个性已活脱而出。接下去,作者借红娘回答张生的问话,进一步写她的教养与爱好:“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②作品写她的日常生活也起到了丰富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如说:“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③她“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④。作品塑造了这样一位美丽聪慧、多情哀婉的女性,通过叙写她与张生相爱的曲折过程,表现了她的矛盾心理活动以及她之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不易与大胆。崔莺莺是一个处在深闺受封建思想教育与外界较少接触的少女,她受到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可谓不深。孟圣人早就说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于是崔莺莺虽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在内心又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⑤,正颜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⑥。数日后,当张生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⑦。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终难彻底摆脱社会、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最终还是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于礼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⑧。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她只是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十分感人。
与崔莺莺可亲可爱的形象相比,男主人公张生的形象却令人匪夷所思!对照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的人性标准,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行为显然令人不齿,而尤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为自己的举动作了如此高妙的辩护:“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蒘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⑨张生用“忍情”一说为自己的始乱终弃行为辩护。本来在漫漫的封建长夜里,男人视女人为玩物,始乱之、终弃之的例子举不胜举,那原不值得惊讶。但他竟然昧着良心作出这样一番宏词高论却不得不令人瞠目结舌!而更加令人讶异的是,时人及作者元稹竟也褒扬张生的举动,在崔张“自是绝不复知”⑩后,文中有云:“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11)在张生心中、作者笔下,美丽多情、温柔聪慧的少女莺莺真的是引人“败”“溃”的“妖孽”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作者又为什么要将崔、张恋情写得那么缠绵悱恻、美丽动人,并极尽赞美讴歌之能事将莺莺绘就得那么一塌糊涂的美与善呢?!
元稹的《莺莺传》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文本!
这一奇怪的文本引来后人无数的评说。
有人据张生的始乱终弃及其自我辩护就得出如下结论:张生既非礼法之士,也非情痴情种,而是一个执著地奉行纵欲主义的风流公子,他的“忍情说”是极其虚伪矫饰的诡辩。
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恐怕也没有这么简单。
说张生不钟爱情、作者不讴歌情,从文中看并不是事实。《莺莺传》中多次出现“情”字,如红娘给张生出主意:“试为喻情诗以乱之。”(12)后来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紞(13)。崔莺莺寄张生信中云:“儿女之情,悲喜交集……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因物达情,永以为好”(14)。张生一方面“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15),另一方面又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学先生,他是一个“非忘情者”(16),当见到崔莺莺之后,立即“惑之,愿致其情”(17),在西厢相会的前前后后,他简直就是一个依情而行者。因此说他完全不恋情并不是事实,他要是不惦念“情”,在他后来路过莺莺家时,则完全没有必要再要求见上莺莺一面。张生显然是一个有情之人,只是他的情浓实在及不上莺莺对他的浓情,莺莺已被情儿所伤!
但是作品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以普通人的心性来看,始乱终弃之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举动,张生却觉得自己的行为“自有理”,更有甚者,聆听张生“忍情”一说的听众“时人”及作者元稹也完全默认张生的观点。“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18),元稹询问张生与莺莺断交的原因,张生于是就发表了那样一通冠冕堂皇的“忍情”演说,话音刚落,文中即云:“于时坐者皆为深叹。”(19)“叹”则“叹”矣,原来座中并没有一人反对张生的“志亦绝矣”(21),如此反应,于情何说!连写诗作画抒情表意吃文艺饭的元稹在此时也冷淡了“情”字。“皆为深叹”,折射的只不过是一种矛盾而无奈的心态罢了。作者元稹对自己人生中似曾相识的“善举”又何尝不是矛盾而无奈的心态呢?!
自宋代以来,历代学者提供了大量而有力的证据,从多种角度证明《莺莺传》中张生即作者元稹自寓。宋代赵德麟《辨〈传奇〉莺莺事》云:“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侯鲭录》卷五。按:《莺莺传》原题《传奇》)他通过考察白居易所作《微之墓志》《微之母郑夫人志》、韩愈《微之妻韦丛墓志》、元稹《陆氏姊志》、唐《崔氏谱》、元稹《古艳诗》《春词》等以及元、白的有关诗作,证明元稹事迹与《莺莺传》中张生相合,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自寓说”这一结论。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辛部《庄岳委谈》云:《莺莺传》“乃微之自寓耳”。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云:“元微之……其作《莺莺传》,盖托名张生。”近人鲁迅、陈寅恪、汪辟疆、孙望、卞孝萱等人也持此说。
原来,崔、张的爱情故事是作者元稹依据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写成的。
这也就不奇怪了,由于《莺莺传》中包含着作者的真实记忆与经历,于是作品表现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描摹崔莺莺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体现出莺莺性格的两重性,让人读来倍觉真切、颇有美感。
我们不难想见,在情感上,元稹念念不忘他的初恋情人,但作为社会人的他自然又不愿意爽快地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于是在作品中他就不得不为张生,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曾经的“善举”开脱一把,寻找一个巧妙的借口。于是作者一方面用优美、动情、细腻、逼真的笔触塑造了美丽矜持、聪明可爱的女主人公崔莺莺的形象,一方面又将崔、张恋情视为士人的一般艳遇,将莺莺称为致人败溃的“尤物”“妖孽”,将张生与莺莺的断交视为善于“补过”。元稹的这样一种写法,实际上是他创作《莺莺传》时的矛盾心理在作品中的体现。
我们知道,文学史上一些涉及作者隐私的作品,创作者在文中流露的心态都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既想如实地记录下本事,舒缓一下由于不断回顾往事而导致的紧张心理,可又出于种种顾虑,不想让人轻易地“对号入座”。所以这类作品总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还会使用一些障眼法,制造一些假象以迷惑读者。唐末李商隐的《无题》诗是这样,中唐时元稹的《莺莺传》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元稹在《莺莺传》中没有如实地交待张生抛弃莺莺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创作时矛盾心理的集中体现。《莺莺传》的历代读者很难信服张生“忍情”一说即为离弃莺莺的原因,但在作品中又很难直接找出张生此举的真正缘由,这与作者在文中对莺莺的身份地位作了模糊处理有关。
在小说中,作者只是简单介绍崔家“财产甚厚,多奴仆”(22),并未明确莺莺的出身地位。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中认为她出身寒门,“莺莺所出必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23)。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第四章《进士与娼妓文学———莺莺传与霍小玉传》中说得更干脆:“莺莺的出身必与霍小玉相仿佛,而所谓崔郑(莺莺母亲托言郑氏之女)等显赫的姓氏,只是作者信手拈来装体面罢了!”不过,小说行文中也隐约其辞地为莺莺的非贵出身提供了内证。恋爱的过程中,莺莺始终有一种将被遗弃的预感。即便是在她与张生热恋的时刻,也没有摆脱这种预感的阴影。张生欲赴长安应试,临行前莺莺“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24)她与张生的恋爱不能进而发展为正式的婚姻,是因彼此都顾念到张生的仕途前程;张生的始乱终弃之所以能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谅解,甚至赞扬,其原因也在这里。在当时门阀观念畅行社会的情况下,“擢进士第”以建立自己的功名,娶“高门女”以取得可靠的政治前途,是士人中盛行的最高理想。
由此可见,张生留着联姻这一条道,想另攀高门寻求个人的功名仕途,是他最终离弃莺莺的直接动因与主要原因。
而他的“忍情”一说,只不过是他抛弃莺莺的次要原因。张生掷出“忍情”一说,文中云“于时坐者皆为深叹”,也就是说座中并没有人反对他的“志亦绝矣”,这与当时中唐士人对情与理所具的特殊认识也有关系。唐代是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时代,情理分离之说,来自佛、老,中唐儒生也难免不受影响。在佛老看来,情是成就佛道的障碍,是乱性的根源,极易使人蒙蔽心性而走向堕落。唐以后,持性情分离之说者分化为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抑情扬理,如北宋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极力否定情的价值;另一派主张抑理扬情,如苏轼兄弟作《苏氏易传》,认为圣人设教,一切皆本人情。我们研读元稹所写的《莺莺传》一文,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像后代儒生那样走向任一极端。他一方面大胆地展现情感的魅力,另一方面又不否认理性的价值。缘其如此,在对待张生抛弃莺莺一事也即他曾经所做的“善举”上,作者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困惑与矛盾,在感情与理性的两极间摇摆不定。
元稹这种矛盾心态,我们还可以从他数年后所写的《梦游春七十韵》中见得。诗中指涉了他的初恋,当他与情人断绝往来之后,他异常伤感,“夜夜望天河,无由重沿溯”(25)。可是待他从这种伤感中缓过神来后,他又盛夸道性的价值:“结念心所期,返如禅顿悟。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杂洽两京春,喧阗众禽护。我到看花时,但作怀仙句。浮生转经历,道性尤坚固。”(26)问题是,我们读了这样的诗作,还是不禁要问,如果他真的“道性尤坚固”,他又何必反复回眸他的初恋而“作怀仙句”呢?其答案只能是,初恋留给元稹的印象是美好无比的,他对他当初势利地告别恋人的举动始终凄凄惶惶、愧疚难当。当初他情不自禁地创制传奇小说《莺莺传》,也是为了缓解他内心的焦灼愧疚之感。看来,这样的尝试只管得了一时,让他心理上暂时好受了些——他似乎找到了当初离弃恋人的理论根据,佛理说“情是乱性的根源”,那是他的救命稻草——但管不了一世,数年后他还得再吟诗篇大“梦游春”,以释前情。
因为真情,是永远掩埋不掉的!
作者元稹也正是凭着《莺莺传》主体部分流溢出来的男女真情,依靠他所塑造的可亲可怜可敬的莺莺形象打动了读者,俘获了历代读者的心。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27)不容置疑,《莺莺传》是一篇感动人心的传奇小说,它在主体部分流溢出来的真挚恋情基于人的一般天性,其情其感荡人心怀。但读者又觉得作品美中不足,他们不太喜欢巧舌如簧为自己辩护的张生;而作者元稹对张生的始乱终弃善作庇护,又使得这一文本外显怪异。怎样看待这一“怪异”文本中的张生形象?张生身上包蕴着怎样的历史人性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人们考察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28)。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与“人的一般本性”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甚至相反的一面。在每个时期“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顺应着人性的发展、通向未来的部分,也有只适应于当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乃是人的一般本性的扭曲的部分。由此观照《莺莺传》中张生的行为举动,我们就不难看出,张生起初对莺莺的相思相恋是自然而又健康的,这样的感情发自内心、基于人的一般本性;后来他抛弃莺莺且为其辩护的举动则是势利而又扭曲的,这样的行为是人性的异化,是“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之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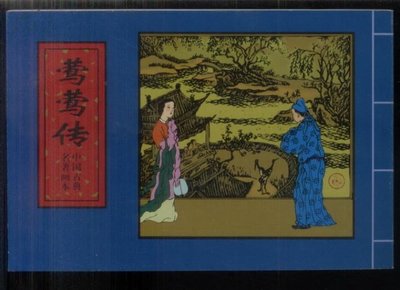
我们知道,一篇文学作品要能在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里得到时人的认可,它至少得与当时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相适应。张生最终抛弃了莺莺却还能得到时人的肯定,其原因就在这里。作者元稹写出这样的文本而不以为怪,其原因也在这里。然而,如果一篇作品仅仅是或主要是与其中的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却不符合“人的一般本性”的内容相适应,那么,在那个时代过去以后,它的魅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甚或全部消失。文学之河已经淘洗了无以计数的应时之作,它们埋进了历史的河床已被后人永远遗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元稹的自寓小说《莺莺传》却历经千载还被人反复阅读,其根由就在于小说中对张生“善举”的粉饰并不占主要地位,作品的主体部分恰恰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崔、张相识相恋的曲折动人过程,并不遗余力地讴歌了青年男女出于人的一般本性而生的真情真爱!
也正因为如此,《莺莺传》问世后的一千多年中,崔、张的爱情故事不断地被人改编与移植在诗歌、小说、说唱、戏剧等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其种类之多,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是罕见的,《莺莺传》也就成了唐传奇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小说。在那众多的改编作品中,又以金代董解元所撰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所作的杂剧《西厢记》最为有名。《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董解元,主要活动于金章宗(1190—1208在位)时期。“解元”是时人对士子的泛称,董的真名不详。诸宫调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作者已经变张生的抛弃莺莺为二人终于结合,而且将张生改写成了一个忠于爱情、得不到莺莺宁可自杀的痴情男子,莺莺也改变了原作中纯粹被动的性格,演变成了一个由被动应付爱情到主动追求爱情的性格类型。红娘在原作中是个次要角色,在此作中却成了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莺莺的母亲在小说中只起了介绍莺莺与张生相见的作用,对他们的爱情从未加以干涉,而到了《西厢记诸宫调》中却成了阻碍崔、张结合的封建礼教的代表,从而使整个作品贯穿了男女恋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面貌。其中的张生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莺莺探病,长亭送别,梦中相会等场面都是新加的。传奇《莺莺传》三千多字,《西厢记诸宫调》已有五万多字,这大大丰富了原作的情节。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赞美私情而背离礼教,流露了尊重人的一般本性的民主意识。
到了元代“天下夺魁”的杂剧大家王实甫手里,《西厢记》的思想倾向更为鲜明。作者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而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上也毫不相让,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十分激烈。《西厢记》表面上又安排了两条矛盾冲突线:一是以老夫人为一方,莺莺、张生和红娘为另一方的矛盾,这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势力,与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双方壁垒分明,冲突尖锐。二是莺莺、红娘、张生三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多由他们所处不同位置而引起的一些猜疑和误会构成。这两组矛盾错综交织,互相发展,使整个剧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常给人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获得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综观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改编,我们看到,崔、张爱情故事的内涵已被大大地拓展与丰富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越来越具有魅力!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董解元、王实甫在改编中所做出的种种尝试与努力。
而在董、王所做出的种种创举中,他们对张生形象一以贯之地打破原作定规,塑造出新的形象,是最为关键、最富创见的一着!
因为,张生形象一经重塑,《莺莺传》这一怪异文本外显的主题就被巧妙地置换了。
我们纵观张生在《莺莺传》中的全部表现,可以看出小说反映的根本矛盾其实并不是张生的始乱终弃而导致的崔、张矛盾,而主要体现为张生内心所具的仕与婚的矛盾!如上文所析,如果张生与出身不贵的莺莺缔结婚姻,他也就失去了攀婚名门、仕进有望这样一条康庄大道,于是他不得不舍弃莺莺而待他婚。张生内心仕与婚的矛盾才导致了他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这样的矛盾才与文本的情节线相始终。而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由于张生形象的改变,他成了一个忠于爱情、非莺莺不娶的痴情男儿,作品折射的根本矛盾与表现的主题也就被相应地置换了。毋庸讳言,在原作《莺莺传》中,封建礼教也无时无刻不束缚着莺莺的天性(她与张生的结识与结合都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她在对待张生的示爱举动其外部行为前后不一,后被张生遗弃也缺乏抗争、自怨自艾。但是很明显,封建礼教所致的莺莺这种内心矛盾并不是《莺莺传》这一作品所要表现的主要矛盾,因为《莺莺传》这一文本表面上肯定与宣扬张生的“迷途知返”,客观上则昭示了张生内心仕与婚的矛盾。张生形象一经重塑,改编之作就呈现了与原作迥异其趣的风貌,董、王的作品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西厢记》又以其更为精湛的艺术表现,形象化地揭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光辉的主题。
张生形象的重塑,是董、王改作中的重重一笔。这一形象的诞生既是神来之笔,又是历史的必然!
张生形象的新变是人性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因为一部人性的发展史乃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逐步向“人的一般本性”重合的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性的进步,董、王生活时代的人们已经非常不满意于张生在《莺莺传》中的拙劣表现,非常不高兴让这样扭曲的张生形象再出现于反映民众心声的爱情正剧中,于是董解元、王实甫们就不得不顺乎民心民意让《莺莺传》中的张生形象从读者与观众的视域中消失。于是《西厢记》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爱情经典,持续地影响着后代的文学乃至人们的生活观念。于是人性的发展就带动了文学的进步,文学与人性也就这样水乳交融地结伴而行。
作者简介:杨文榜(1966— ),江苏高邮人。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9)(19)(20)(21)(23)张友鹤.唐宋传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4)(25)冀勤校点.元稹集外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6)(27)章培恒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