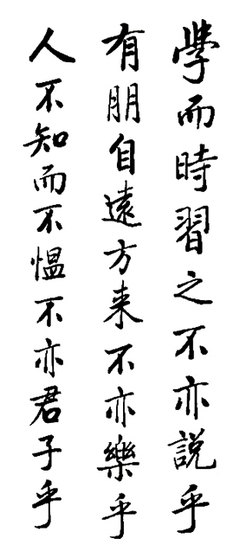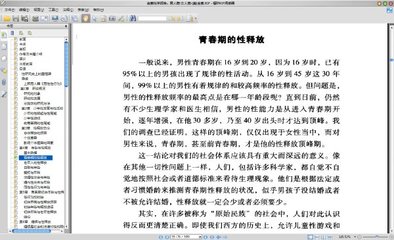为性学而献身!
文/潘海
在北京的工作虽然超忙,但周末的昨晚,还是抽暇会见了京城的两位性学同道。一番聊来,忽然从中悟到,对于性学研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其实都意识也实际上必然是一种献身。而这所有的献身,其实都是崇高和无私的。
性学研究,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实证型”研究,一种是“论证型”研究。前者,我们可称为“实证性学”;后者,我们可称为“论证性学”。而相应的,进行“实证型研究”的性学家,我们通常称之为“实证型性学家”;进行“论证型研究”的性学家,我们则称之为“论证型性学家”。
两种性学家,都需要献身。
先说“实证型性学家”。
“实证型性学家”的献身,人们一看就会暇想,认为所谓“献身”,无非就是“自身投入、与人做爱”,通过个人亲身参与的大量的性实践,产生出某些规律性的结论,然后将这结论推广向社会,形成自己的学说。
这种献身,通常会遭到人们某种甚至普遍的道德谴责。认为“实证型性学家”不过是以性学研究为借口泛滥个人的性欲,从而被扣上“好色之徒”、“淫荡之女”甚至“下流无耻”等人身谩骂、人格抵毁的黑帽子。
事实上,“实证型性学研究”的所谓“献身”,并不都是快乐的过程。不仅开发合适的性对象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这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成本是一定要支付的),而由于人海茫茫,并不是每一个被你开发的性对象,都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有些甚至很低能、很没有悟性、很不会配合,甚至根本不能理解你想从二人的“床上开发”中得到什么。这样,就把本来具有学术意义的床上行为降低为一般的男女做爱、甚至连做爱的水平都达不到,只是一次味同嚼蜡的低级性交。
这种低级的性行为,对于“实证型性学家”简直就是生命的浪费。
譬如,一位身为女性的性学家,想通过一定数量的案例,实证“阴茎大小对于阴道的影响”。她从女伴的谈话中闻知一位男性阴茎很大,便主动邀他上床。经现场实证,该男的阴茎,勃起状态下,直径超过5.6厘米、长度超过16厘米,在东亚人种中属于“超大型”。
这位女性学家欣喜若狂。她在国内还从未见过如此硕大的阴茎,如果把它放进来,一定会有一般阴茎所不能产生的“经典感觉”。于是便决定实验。
可是,这根阴茎实在太大,以致于女性学家找遍京城的性用品商店,竟买不到相应尺寸的避孕套。实在没有办法,女性学家只得冒险让男人不戴套进入。而更让人沮丧的是,这男人根本不管女性学家的研究需求,不按女方的要求来做。他只顾自己快活!
女性学家要求他:进入以后先不要抽动,停留3~5分钟,让她感受一下,在超大阴茎的超强充塞下,女人的阴道还有没有收缩的空间、女人耻骨前后的PC肌还有没有夹击的力量?然而,这位仁兄根本不听女性学家的解说,一把就将阴茎插入阴道最深之处,然后叭叭叭猛抽猛撞,两分钟不到,早已一泄千里如注。
女性学家非常失望,就说:“你歇一会儿,再做,但一定要听我的!”可是,如此硕大的阴茎,再次勃起所需的充血量很大,需要一定时间,导致不应期延长。女性学家对它用手用口进行各种刺激,希望它能快速勃起。但这位可怜的女子,赤身裸体地苦苦折腾了两个小时,那根“实验器材”却始终无法再用——男人由于极度快乐,已经极度疲软。第一次实验归于失败。
后来,这位女性学家心有不甘,又约这位男人出来“幽会”几次,但没有一次达成实证目的,而她自己,却完全沦为那根超大阴茎的免费玩具!
你说,这样的献身虽然悲哀,但对于人类性学的研究,是不是又很崇高?
所以,不能对“实证型性学家”的床上献身进行无知的猜想和无聊的攻击。
再说“论证型性学家”。
“论证型性学家”自己通常不参与性行为,而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式:社会调查与个别访谈。也就是说,“论证型性学家”主要是把别人的性经验、性感受搜集起来,整理归纳,分析提炼,从而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结论,然后推向社会,并形成自己的学说。

所以,“论证型性学家”一般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器官排除在研究之外。这种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避免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或者个人的狭隘经验当成普遍的规律。这样,就能使自己的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更具广泛性。而且,由于性学家本人不与研究对象上床,相应的研究成本与道德风险也明显偏低。因此,国内外的性学家大多采用这种研究方法。
但“论证型性学家”也是要献身的,那就是他必须让自己“无性”,或者说,他只能以“中性的身体”进入研究环境、尤其是与研究对象进行私秘性很强的个人访谈时。他不能有性的冲动,更不能试图去扮演某种性角色。因为他的个人冲动、或者他扮演了某种性角色之后,他的研究结论,就会带上他个人的冲动痕迹和角色色彩。那么,这样的研究就不再是“论证型”的,而变质为“实证型”,则他的研究结论就可能失去客观。因此,采用“论证型”方法来研究性学的,无论是从学术方式、还是从职业操守上讲,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身体放进去——这种“有我无我”的境界,就是“论证型性学家”的真正献身。
这种献身非常悲壮。
如果性学家是男性,你看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坐着你的对面,向你促膝倾诉,非常具体地向你讲述她的性经历和性感受、向你咨询她所无法化解的性困惑或者性难题。而你明明知道她的“致命伤”在哪里,甚至你也明明知道自己只要出手,当下就可以为她除去暂时的痛苦。但是,你不能做!
你必须始终保持一本正经,你的两眼必须以没有任何非份之想的真诚之光直视着她的两眼,你必须让她按照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思维逻辑来讲,只是在她实在无词表达时你才能予以小心的提示或者作进一步的询问。你永远都不能按照自己的预设结论去引导她,更不能以阴暗的叵测之心去诱使她走进你精心编织的“床上性局”。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性的自控能力不强(或称“性的排我能力”不强)的人来讲,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熬,甚至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但“论证型性学家”必须学会忍受这一切,哪怕是在那位姑娘公然向你调情、或者一时失控拉住你的手时,你也不能为之所动——你必须保持你在她面前的应有距离与高度!
你说,这样的献身,这样将自己的身体献于性外,虽然近乎有些残酷,但对于人类性学的研究,是不是也是一种崇高?
人类是需要崇高的。即使是在一个已经没有信仰、甚至没有理想的国度,崇高仍然可以支配着社会人际、尤其是两性人际关系走向光明磊落、走向无私伟大!所以,对于性学家,无论他是“实证型”还是“论证型”,只要他以崇高的献身(献给别人或排除自我)来推进研究,我们都应以宽容之心、理解之心,来正视他或她的献身。而正是有了这样勇敢或者坚忍的献身精神,人类性学研究的成果才会产生如此跨越的飞跃,才会让人类更多揭开自己身体的秘密与心理的规律,从而在人类文明的旗帜下实现两性的真正和解与和谐。
2010年6月5日晨,写于北京东直门外,珠海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