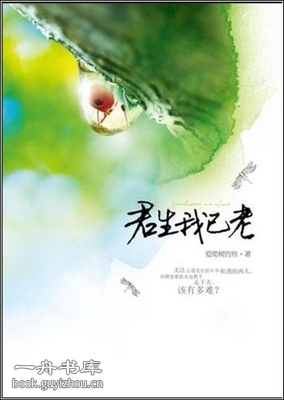皂荚树下的童年贫穷而快乐。
土坯墙,柏木梁,一群娃娃滚满床。父母亲就在那潮湿而充满土味的老房子里,养活我们弟兄五个。孩子多、劳力少,家里的生活困难得不行。想吃上白面馍,几乎是不可能的。热气腾腾的白面馍,只是羡慕之下的听闻,只是口水之中的目睹,只是梦中或可满足的念想,是一家人无比奢侈的理想。因为穷,我们家常常遭遇别人的嘲笑;父母亲却并不言语,只是拼命做活,好为五个光屁股娃讨生活。
秋日的半下午,生产队下工了。孬旦手拿小镢头归来,看我在供销社前面玩,就用小镢头在我头上抡着圈儿吓唬我,嘴里说:“看我怎么牉了你!”没想到,他手一滑,小镢头果真就落在我的头上。我受了伤,疼得真叫唤。孬旦的妈很快就过来赔情道歉,嘴里直说:“别哭,看我怎么打他!明天叫你去我家吃酸面叶儿!”我就乖乖地随母亲回去了,心里净想着第二天吃酸面叶儿了。然而第二天孬旦的妈竟没有来叫我。吃酸面叶儿,却成了我连续好多天美滋滋的一个愿望;但过了很久,也还是没有吃上那向往不已的酸面叶儿......
冬日里,母亲带着我们在生产队里的猪场里喂猪,用大锅头给猪烧饭,当大锅冒出热气时便在锅放些剩菜叶,再丢进去一些萝卜头、生产队挑剩下的小红薯之类。过一会儿母亲就用马瓢把猪食舀到桶里,提着桶向猪圈走去。只要母亲咳嗽一声,幸福的猪们就兴奋地叫着向食槽里拱成一堆,弄得没法倒食了,母亲就拿笤帚打它们。猪圈里老母猪要生小猪了,母亲就整夜看守着。有母亲的细心照料,小猪们长的很快,特别欢实。当母亲咳嗽一声、小猪们兴奋地叫着的时候,我们弟儿几个的肚子早已饿得直叫;但不用担心,母亲提了桶回来时,就用烧火棍在锅台下的火灰里拨出了些小红薯,冒着热气,散出香味来。这些红薯很小,是生产队挑剩下用来喂猪的,却又成了我们得以充饥的口中食。手里捏着,嘴里啃着,和圈里的小猪们一样的幸福了。
入春了,冬菜容易吃完,夏菜又接不上,我们家就更不好过了。母亲常常在窗外的一个大缸里捞取腌好的咸萝卜,让我们吃。掀开盖子来,就有一股咸味扑出来;用勺子拨开一层白沫,捞出一根萝卜,捡掉一些小白虫子,用清水冲冼几遍,母亲就拿到昏暗的厨房去,切成细丝儿,加点葱花,浇些醋,吃起来也是有滋有味的。地里野菜上来的时候,母亲就约了伴挎个篮子,铁路边嫩嫩的小白蒿、荒地里的肥肥的荠菜、马齿菜和林苋菜,就都成了美味的菜肴;尤其是水渠边的水芹菜,碧绿的小叶子、青里发紫的茎和雪白的根,水水的、带着点湿漉漉的粘土、散着一股浓浓的香气,诱惑最大了,一看一闻就会流下口水来。虽不是山珍海味,却是极美味的东西;现在看来,又是极好的绿色食品,无公害、降血压,有益健康。母亲总能用她粗糙的双手,为我们弄出可口的饭菜来。我们知道,母亲不会让我们挨饿的!
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快乐。光着脊梁在皂荚树下纳凉,有时拿着芭蕉扇到处乱跑。不用怕热,我们打井水喝。正屋后边有一口井,先扎好步,用绳子挂个铁桶,左右摆两下,等进了大半桶水后再向下一送,就打满了水,用力拔上来就有了清凉甘甜的降温水,比任何饮料都好得多。街上也有卖西瓜的,我们家是断然买不起的,许多人家一次也只是买几芽儿,没有买整个的。看人家吃西瓜,我们弟兄几个只有羡慕的份儿,就去央求母亲。母亲总是有办法的,她给我们每人发个篮子,让我们去街上捡西瓜皮。我们提着篮子回来,母亲就关了街门、上了栓,带我们到井边;打上一大盆清凉甘甜的井水,把西瓜皮倒入盆中,洗涮干净,用刀削去一层,递给我们,我们就排了队很有秩序地接着。先接到西瓜皮的人就很快躲到一边去,双手捧着,低头啃起来;啃完了就又排到队伍的最后一个;母亲总是吃盆中剩下的最后一个,而且是最小的。我总是拼命地啃,啃完了红瓤,又啃白色的皮,不舍得很快扔掉,常常把最外边的绿皮也啃出了洞!
那些日子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并不觉着苦。一方面原因是年龄小,感觉不到父母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母亲的呵护,我们每有一点愿望,总能在母亲的手里得到实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