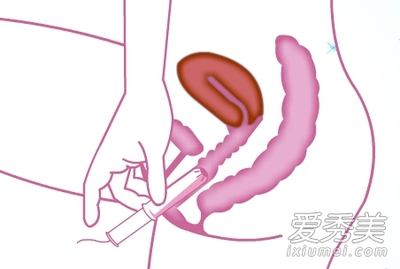被遗忘的人在爱中复活
(栗宪庭)
在这世界上活过的人,被遗忘的永远是大多数。即使是被公共记忆的少数名流,也大多因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一个时期的时尚,使这些记忆的概念化程度,远远遮蔽了人的活生生性质。人对他人活生生的感觉记忆,除了被封存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也许只有回忆文字和视觉艺术--尤其影像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同时人对他人活生生的感觉记忆,在什么程度上能成为公共记忆,则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吕楠从19**年到1990年,花了两年时间,跨越十个省市拍摄了这组《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的生存状况》,他首先遇到的是摄影史上的同类作品,玛丽·艾莲·马克拍了一家医院的81号病房。德巴东拍了意大利的十家医院。吕楠想全面了解精神病人的生存现状,他感觉玛丽·艾莲·马克是一个局部,德巴东把它扩大,但是没有把扩大的东西形成一个整体,因为艺术是一个整体,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就是散的、失控的,他希望他拍摄的精神病的生存状况是一个结实的整体。所以他的这个系列作品分成了三个部分,不仅是医院、家庭,还有流浪,形成一个精神病人的各种生存状况。
摄影的深刻,在于心灵的思考,摄影师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影象要在一瞬间形成,但不意味摄影师总要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他关心的是根本和持久的东西。那么对于吕楠,什么是精神病人持久和根本因素?当时吕楠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触动了吕楠,那是他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期间,当他走进一间病房,有一个病人正往外看,他想拍他,这时病人突然走过来,那病人很壮,吕楠想跑又怕伤害那个病人,就在此时那病人已经到了吕楠面前,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一刹那,他看到那病人伸出一只手来要和吕楠握手,那一瞬间是病人的友好和爱心打动了吕楠,之后在吕楠的心里就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个概念了,他们只是那么一类人,有着所有人的喜怒哀乐,爱恋和亲情,而不是社会给与他们的那种概念化的状态。
人以教授,医生,工人,农民等社会化类型生存的同时,也被这种生存类型概念化了,在这方面,精神病人作为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和一个名流的生存状态,在被概念化上是一样的。但每个人都是活生生和各种各样的,教授,医生,工人,农民,都不是概念中的教授和医生那类人。所不同的是,名流由于更多地被关注,而留下了大量的回忆文字和影像资料,精神病人更少被关注,更容易被妖魔化。吕楠区别于玛丽·艾莲·马克和德巴东留下的问题,就是以全景方式关注了这类人。而且,吕楠抱着对精神病人的一份爱心,让精神病人从被社会妖魔化了的概念形象中复活,变成多种多样和活生生的形象。如第9幅,画家张夏平,墙上的画和对张夏平狂躁瞬间的抓取,既有所有病人的共同特征,也抓取了她非常特别的神情;第12幅,着力突出一个小女孩和正常儿童一样喜欢抱着熊猫玩具的状态,只有通过忧郁得略带呆滞的神情,让我们想到她不正常的一面;第14幅,拿着死去儿子照片沉浸在思念的痛苦中,正常人与病人的痛苦是一样的,作品强调出对悲痛的“无法自制”,以及丧魂失魄的失常状态;以及第28幅,墙上挂着自己画的雷锋像,安静呆滞地坐着的病人;第38幅,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支撑一个有几个精神病人的家庭生活,以及她被生活所折磨的神情;第49幅,把门窗都当柴烧掉的病人等,都注意抓取了特殊的病态表现。而第46幅,正在为室友画像的病人,以及围观的病人,画像和围观者都与正常人的状态无异。第25幅的打牌场面,第26幅的打乒乓球场面,都强调了他们与正常人共同性,但所有病人的神态,又可以让人感觉到他们是一群病人。细看每一幅作品,吕楠以不同的方式,抓取了不同的瞬间,可以让人读出每一个病人的不同经历和特别的现状,同时,在正常人的个性与病人状态之间,在相同病人和不同的表现状态之间,作者都努力把握了一种非常具体的分寸感,这种分寸感就是一个人的人性具体性,也是这批作品何以打动人的地方。
人们常常把特立独行的人称作“精神病”,在常人眼光中,精神病人是过于沉浸在个人感觉中不能溶合于集体的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表现也不一样。吕楠在处理此类精神病人的状态时,特别注意他们处在集体中的状态,并细腻的把握了每个病人的特别感觉。如第2幅,与打牌、打乒乓球强调正常状态不同,突出了病人虽同处一室,却都沉浸在自己的个人感觉中,虽每个人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却形态各异;第6幅,屋子中间,一个吹笛子的病人,其他人都在安静地听笛声。也许笛声把他们带到各自的内心世界,也许精神病人把对笛声的个人感受夸大了,所以细看吹笛子的场面,反给人一种出奇的安静甚至沉闷的气氛;第10幅,每个人都在各想心事,近景一个人在写信,那神态的专注,不似正常人在大厅广众场面写私信的状态,捕捉住了病人沉浸在自我状态中而旁若无人的样子。
吕楠的一些大场面,拍出一种意象的感觉,意象是超出现实感的一种感受。我们通常说的现实,都是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段里,以一定价值体系体现的社会状态,对于精神病人,他眼中的世界是超现实的,而对于正常人,精神病人的世界也是一种超现实状态。如第11幅,大面积灰墙前,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视觉上有点堵;镜头有意放低,让地面上的两根大木头戳在观者面前,霸道而硬生生的。在墙和木头两个巨大力量的夹击中,是一排小小的穿白色衣服的病人。第22幅,整个画面被锋利的之字形割成几个大的锐角形,在高墙端部之字形的路上,坐、立或行走着的病人,被锋利的直线所分割。第27幅,巨型的烟囱和高高围墙作为背景,单调而冷酷,梦游般的病人,像群雕一样戳在画面的中央,梦幻而荒诞。第39幅,两个楼房形成的夹角中央,散落的病人和翻着白眼的病人,以及第40幅,一人躺在圆桌上,其他人围着转圈的情景,极似超现实主义画面,展示出一种怪异的意象世界。
还有很多幅作品以神态抓取见长,如第16幅,画面近景,镜头抓住窗外的阳光正好投射在一个女人眼部的瞬间,突出了沉郁的眼神。第41幅,选择双手抱膝缩成一团的正面角度,在身体的比例上,脸部显得超大,惊愕神态因此更突出。第47幅,整幅是脸和手的特写,手指甲和鼻子的高光鲜明,画面黑白强烈,使头像像一个铜铸雕象,把痛苦凝固。
汇集病人的各种生存状况,包括医院、家庭、流浪等状态,自然是吕楠最显而易见的努力,其中吕楠还注意拍摄了被特别“待遇”的病人,如被关在石头屋子里,被铁镣锁着的,被捆在树上的病人等等,而且这几幅作品,并没有选择病人狂躁的瞬间,而是选择他们安静地被锁着被捆着的状态,在被强制和安静之间形成对比。另外,怪异动作是吕楠注意到病人的一种特别的状态,如第32幅,第51幅,第53幅等。当然,每一幅作品都值得仔细阅读,这是一部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的大全。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精神病人只是一种医学上的分类,那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专业领域,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相似的人性状态,也许,精神病只是程度的区别,每一个人也许都有过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所以,这些照片让我们感动,不管你熟不熟悉这些人,它展现出的是我们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人的生存状态。
生命在上天堂的路上
(栗宪庭)
吕楠《在路上》的拍摄范围跨越了十个省市,而且在中国,天主教信仰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所以他有过数次相机和胶片被没收的经历,至今,他在内蒙古拍摄的部分胶片依然没有拿到,可以想象吕楠在拍摄过程中的艰难,以及心理和经济上所遭受的压力,这可能也是《在路上》没有城市教众信仰状态和场面的原因吧。
吕楠为自己的这组片子起名《在路上》,我看了这六十张照片之后,我理解了他的感受。我们从大多数拍宗教的摄影资料上看,很多摄影师不是拍宗教庆典就是拍教堂。吕楠也去过一百多个教堂,大的令他吃惊,如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子。只有两千多个教友,他们自己集资建了个中西结合的琉璃瓦教堂,高65米,长65米,宽24米,中间没有一根柱子。据吕楠介绍,它的建造像一个奇迹,那些教众有的供瓦,有的供砖,干活全部义务,非常纯粹。是什么力量让这些教众以如此爱心奉献给宗教事业?是信仰,“在路上”,对于信众的人生意义,就是一生都是走在上天堂的路上,只有虔诚和有爱的人,才有资格上天堂,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也是一个上天堂的必经之路。所以吕楠没有选择可能更有表面效果的宗教庆典和教堂来拍摄,而是选择了信仰中的人,用镜头去体会教众信仰的虔诚表情和动态,以及教众最日常和朴素的场面,这是他作品感人至深的原因。没有拍摄者对被拍摄者的爱心和感动,就不会抓住感人至深的场面和表情,拍摄过程也是一个爱心和爱心的碰撞过程,如吕楠体会到的“中国1950年代的时候就跟世界隔绝了。一个村子里宗教是这样形成的,先盖一个教堂,大家自动往教堂集中,形成教友聚集村。而且中国的政治又不允许利用宗教干任何事,所以他们只能作一件事情就是信仰,就是充满爱心,做着友爱的工作。他们所以那么真诚和久远地保存着三百年前的传统,靠的是他们那么强的信仰力量。他们的温和和爱心真的让我大吃一惊,那些农村的老妈子从来不闲谈,就是念经,在家里作自己的事,关心需要关心的人,晚上再进教堂念经。当一家有人要死的时候,别人会说太好了,他们不恐惧死亡。爱是什么,我们只能践行爱,而不能拥有爱。我们拥有的只是情感,而情感总被对立的一极所左右。但爱不是这样,耶稣对他门徒的情感有别于他人,但施予的爱却是同等的。”所以,拍摄的前提是吕楠首先被教众信仰的力量和爱心所打动。
信仰的虔诚和爱心,因不同的信徒而有区别,拍出每一个人活生生的具体性,拍出每一个场面的独特性,才显示一个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和境界。如多幅作品注重信徒虔诚的神情刻画,但又突出了每个人的不同,如第2幅《露天弥撒中的朝圣者》,由于作者采用低视角,使信徒虔诚的跪姿和表情都很突出,且每个人的表情又各不相同。第23幅《饭前祈祷的老妇人》,老妇人虔诚的动态和表情,在简陋厨房和中国式灶台的衬托下,更加感人。第24幅《在家里念经的三个女人》,两个老妇人为病榻上的老妇人祈祷,在微弱的烛光下,三个老妇人虔诚同一,神情各异。第31幅《拿十字架的老妇人和羔羊》,盘腿而坐的老妇人拿着十字架,以及羔羊似在亲吻十字架的瞬间,使画面有种象征感觉。第40幅《老夫妇的晚祷》中的老夫妇,一俯默祷,一仰凝视,人物统一中有变化。第53幅《练习圣歌的少年》,烛光映照着两个唱圣歌少年的脸庞,让画面形成伦勃朗式的暗调子,突出了少年认真而圣洁的表情。第56幅《祈祷的老妇人》,画面近景处理,黑背景和白头巾把老妇人虔诚的表情围合在画面中心,尤其突出了微闭的眼睛和泪痕,我曾驻足在这幅作品面前,情不自禁掉下了眼泪。
第16,25,55,56,57幅,都是拍为亡者祈祷的画面,祈祷者的沉静,亡者的安详,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各有不同的处理。如第16幅《一个孩子的葬礼》,一个孩子的死亡,竟有那么多的教众围着墓穴祈祷,就很感人。而且画面处理层次分明,层层集中到十字架,先是背景的大山,接着是围合似城墙的教众,中心是墓穴,墓穴中间是浅色的小棺材,最后指向画面最前方的十字架,加上透视和黑白关系,十字架非常鲜明。第25幅《墓前的两个苗族女人和孩子》,是所有祈祷亡者场面中唯一有悲伤情绪的画面,但两个靠在墓堆上悲伤的妇女,作者选择的是她们掩面的瞬间,使悲伤变得有所节制,尤其镜头采用低视角,让墓堆上突兀的十字架直插天空,而浅颜色天空,把十字架变成沉重的黑色后,就使画面的情调变得肃穆多于悲伤了。尤其第55幅《亡者》,处理得极其精彩,三分之一的黑门洞,和大面积的白墙,在画面右边形成一道贯穿多半画面的竖直线,仿佛成为阴阳两界的分界线,然后是占画面主要位置的亡者遗体了,由于把遗体横贯画面的中央,在黑白分明而坚硬竖直线的衬托下,亡者的衣物、枕头的曲线,就显得非常柔和、温暖,尤其亡者的脸庞和表情,在黑色头巾和衣服的簇拥中,竟有着不可思议的安详甚至美丽!
《在路上》有多幅拍摄了教众在行进路上的场景,如第1,3,13,15,21,44,47,48,51,60。其中第1幅《朝圣的人们》,突出的是朝圣队伍在行进中的庄严。第3幅《前往圣地的人们》,镜头选择朝圣教众的全部背影,而涌动着朝向画面上方十字架的处理,使画面中形成了一种大“势”的气氛。第15,21,48,51幅,都是单独行进的人,或背着圣像,或拿着圣像,或行进在布道的路上。而环境的恶劣,路途的艰辛,都突出了行进者肩负重任的形象特征。
其中弥散或集体祈祷的场面以及细节,处理得尤其感人至深,如第44幅《纪念耶稣诞生的神父和教友》,其中一个跪在地上的教友还正在输液。第32幅《家庭弥撒》,环境是一个破旧的窑洞,一群人围合在狭窄的空间里,灯泡直接进入画面,造成很暗的背景,突出了黑白强烈对比的信众,尤其突出了处在围合中心点的神父,但神父高举圣饼,使神父的脸陷进阴影中,而让圣饼成为了画面中心中的中心。而其他的弥散、祈祷场面大多选择的是贫困、简陋的环境,恰恰让这种生存环境成为信众的衬托背景,或者正是他们信仰的虔诚,才使这些信众获得生存的精神力量,突出了他们在艰苦、贫困生存环境中依然祥和、平静和充满爱心。这正是吕楠的用心之处。
《在路上》的几乎每一幅作品,都显示了吕楠独特的视角。如多种民族的信众,多种独特的祈祷场面,如在渔船上,在中国式灶台前,在土炕上等等,以及砌着十字架的中国式门楼,有毛主席象和耶稣象作背景的家庭合影等等。还有第59幅,画面家徒四壁,信徒手捧一本《圣经》,穿着两只不同的鞋,端坐在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前,棺材上写着“我信肉身之复活”,信徒表情严肃而略有忧虑,这种画面的独特性,可能永远不再会有第二幅了。
吕楠给我说:“我是没有宗教的,我只是有信念,艺术家要有信念最好不要有宗教。”在我看来,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宗教,吕楠被教众信仰的虔诚和爱心所感染,才使他能以同样的虔诚和爱心拍摄这些教众,这就是吕楠的宗教。我们观看这些照片,我们被教众的虔诚所感动的,正是镜头背后作者的心灵――他怎样选择了那些感人的场面。
庄严的日常“经典”——吕楠的《四季》让我肃然起敬
(栗宪庭)
吕楠前后共花了15年时间,独自一人,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拍摄了《被人遗忘的人》、《在路上》、《四季》三个部分的系列作品,以完整而宏大史诗般的规模,仿佛象征了人类今天的“精神现状”,象征了作者期望“人类伟大精神复归”的三部曲。我怀疑这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艺术家,能以这样庄严的态度来对待艺术创作?所以,当吕楠把这三部作品放在我的面前时,它给我的震撼,让我久久不敢动笔,对于他特立独行的15年,我的任何文字都是微不足道的,幸好他的作品能够印刷成册,让大家仔细观看。

吕楠用了整整七年时间,拍摄了这组反映西藏农民生活的《四季》,从春播到秋收的场景,从吃饭到家庭亲情,囊括了西藏农民生活的很多细节和方方面面。在7年时间里,完整的秋收他拍摄了四年次,春播他拍摄了两年次。最后一次,他在西藏连续工作达9个月之久。他靠地图选择拍摄地,用比例尺来计算和选择能够靠步行走到的村子,他一个村挨一个村地走,最远的村子他竟步行了7个小时。而且几乎每天下午他都冒着沙尘暴,往返不同的拍摄地点和驻地。在拍摄的剩余时间里,他天还要花4到6个小时学习柏拉图、歌德的著作,听巴赫的音乐。正是这种宗教般的虔诚,才让他把如此枯燥和寂寞的工作过程,变成与古典主义伟大精神的一种对话方式,把拍摄变成对庄严肃穆的精神体验。
由一百零九幅作品组成的《四季》。以一年时间为顺序,把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变成一部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经典”:既结构完整,又幅幅像西方伟大古典绘画和雕塑那样,经得住观看和仔细推敲。结构完整,是指一百零九幅作品,组合得像一部伟大的日常生活史诗和交响乐,既主题贯穿,又把宏大与细节安排得节奏分明,如第一幅,用一座普通西藏民居做开端,把人们带进质朴而安宁的环境中。接着是春播的各种劳作场景,然后镜头由远及近,把我们的视线,带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最后,镜头由近而远,一幅《去搭厦季羊圈的女人们》,以恢弘的大场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远山与天空浑然一体,衬托出画面中的主旋律重色块的劳作姿态,而木杆的参差不齐,给画面增添了活泼因素。一朵白云从山间浮出,像突然出现在乐曲中的小号声,整个画面诗意盎然,像作者恋恋不舍地离开时的回眸--即将消失的远处,一个新的希望又在开始。
我理解的经典,就是吕楠能把劳动和日常生活、日常情感变成一种具“永恒意义”的美感。因为,《四季》超越了我们通常看到的一个局外人对于西藏的猎奇角度诸如突出的宗教活动、原始感觉、粗壮的体魄之类,以及超越了通常摄影师对一个事件的关注。而以一种敬畏的心理,突出了西藏农民劳动和日常生活的诗意和神性。照片的诗意和神性,是靠作者在捕捉对象时,去除画面所有类似突发事件般的动感和偶然因素,强调劳动、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与人类普遍情感的关联,并以类似古希腊、文艺复兴绘画和雕塑那种稳定、完美的构图,凝重的影调表现出来。如我问他拍西藏的难度在哪儿?他回答说:难度“就是它没有任何事件、普遍得不能再普遍了,所有家庭环境都是一样的,而且同一时期所有家庭干的活都是一样的,就这一点特别难。”但是,《四季》能把这种普通变成不普通,把日常生活变成“经典”,在于吕楠体会到“他们的劳动是百分之百地为自己。我第一次看到把劳动变成了劳动本身。凡高说强烈的阳光下就是庄严肃穆太对了。在西藏,没有面朝泥土背朝天苦的那一面,他们完全是为自己干,所以劳动终于变成劳动是快乐的。就跟艺术变成艺术本身一样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东西。一旦有世俗就跟伟大没有关系了。”作为人类永恒的目标,劳动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养家糊口和辛劳,变成具有神性感觉的诗意,既是吕楠在拍摄西藏农民日常生活过程中的体验,也是吕楠不断与西方伟大古典主义传统对话的过程。《四季》对劳动过程神性诗意的表现,首先体现在春播、秋收等劳动场面中。在这类作品中,劳动者“体态的庄严和肃穆”,是吕楠非常强调的,如《挖人参果的母子》,视平线略低于主要人物,使淡淡的地平线横贯画面的中间,一半是山和天空,一半是土地,构成画面主要的灰色背景,使重色调的母子非常突出,同时,母子一站一蹲的动作,冲破地平线,立在天地之间,尤其是母亲的动作,选择镐头高举正要落下的瞬间,把动作塑造得像一个古典雕塑。另如《播种的夫妇》,画面中的牦牛,一抑一扬,在协调中增加了对比,使整个画面的劳作动态,既舒展又节奏分明。尤其妻子撒种的动作,轻盈、矫健,但并不夸张。而且由于大面积灰色调子,所衬托的重色调动作,以及厚重的着装,使《播种的夫妇》的画面处理,并不显示一般意义上的喜悦和生动感觉,而是强调节制的力量和稳重感觉。此类强调劳动“体态庄严和肃穆”的画面,在春播和秋收等劳动场景中比比皆是,你会觉得这些劳动场面,并不是拍出来的一瞬间,而是反复推敲画出来的,如《拾麦穗的女人》,让人联想到米勒的《拾穗》;《降神师和前来降神的人们》让人联想起伦勃朗的《蒂尔普教授的解剖课》。虽似曾相识,但迥然不同。似曾相识,在于吕楠对“庄严肃穆”画面主要情调的控制;迥然不同,是你无法在《四季》中,真的找出几幅相近于西方古典绘画的作品。相似的只是感觉,因为吕楠在乎的是,从西藏农民日常生活中挖掘出那种“伟大的真实”,它具体、实在得与任何一个地域的生活不同,但却有着与西方古典艺术乃至所有好艺术品共通的人文感觉。
另外在捻线、打茶之类家庭劳作的画面中,吕楠更多强调的是人物在劳作时的动作,尤其是手的动作和表情的关系,配合着手的姿态,是表情的愉悦、专注,或平静、坚定……如《挖土豆的老人》,他筋骨分明的双手,尤其是坚定的目光,平静、庄重的表情,刺激了我的感觉,使我无法使用类似艰辛、贫困这种过于情感色彩的词汇,来形容画面中劳动、食物与这位老人的心理关系,那不是我们这种为物质欲望奔忙、痛苦的城里人所能理解的。其实,画面挖掘到的这种内地农民难得看见的神情,正是不需要我们去理解,是要我们致敬的!在《缠线的母亲和孩子》中,母亲与一双儿女的专注神情;《捻线的母亲和儿子》中,儿子趴在正在捻线母亲的腿上安然入睡,整个画面气氛的温暖和祥和,都让我们感动。
几乎占《四季》总数近半的作品,表现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相互间的亲情和融洽的关系。在此类作品中,吕楠非常善于把握能体现人物关系的瞬间,去突出人物之间的爱和亲密,如《妻子和生气的丈夫》,一边是怒气未消的丈夫,双目圆睁,一边是妻子和蔼的表情和抚摸着丈夫手的动作,这个瞬间,可以让人联想到一个完整的爱和亲情故事。另如《秋收中的母女》,在秋收的草垛旁,未成年的女儿,裸露着身体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可能是由于作者的出现,女儿羞涩地低头微笑,两种微笑,传达出母亲、女儿,和未出现在画面中的作者之间那种善意、和谐的交流。此类作品在《四季》中最多,都着重人与人之间在各种生活细节中的爱、亲情、理解、关怀、融洽等关系。诸如《在邻居家头痛的奶奶和受到惊吓的孙子》中的相互关怀,《梳妆的表姐妹》中对美的共同愿望,以及相当多幅的《奶奶和孙子》、《爷爷和孙女》、《抹擦脸油的奶奶和孙女》,表现了隔代人这间孝敬、融洽的关系,画面非常感人。吕楠在处理此类作品时,继承了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传统,善于通过典型瞬间,去把握人物的心理和主题,即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伟大人类之爱,爱劳动,爱亲人,爱每一个人,甚至爱小动物中,爱自然的一草一木……吕楠在和我聊天时,特意提到他在西藏注意到的一个生活细节:“比如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有一个村子里所有的猫都是骨瘦如柴的,没精神连走路都晃。有一天我刚去一个村民家,看见他家的瘦猫叨着一只老鼠,猫终于吃到东西了。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把老鼠放了,猫还想追,他给挡住了,老鼠跑了。”这种对生命一视同仁,既来自宗教,也来自西藏农民相互之间,以及与自然动植物之间形成的一种和谐关系。这是吕楠在拍摄西藏农民生活中体会到的。
作者拍摄的过程中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或者说,吕楠这15年拍摄《被人遗忘的人》、《在路上》、《四季》的过程,就是一个受爱的教育的过程。15年前当吕楠第一次拍《被人遗忘的人》时,发生了一件事,至今让他记忆尤深:“当时我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我把他们当成很可怕的人。在安定医院,进一间病房,有一个病人正往外看,我想拍他,这时他走过来,我就不拍了。那人很壮,我只能到他的肩膀,这时,我想跑,又怕伤害人家,就在我想的时候,他已经到我跟前了,我就用手护住头,心想别把我打出脑震荡来,脑子一片空白,但在一刹那,我看到他伸出一只手来,要跟我握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精神病病这个概念了。他只是那么一类人,这种想法一直贯彻到西藏。”吕楠在拍摄《在路上》时也谈到他在拍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他说“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利用宗教干任何事。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信仰,就是爱。他们那么强的信仰,那么温和,让我大吃一惊。当一家有人要死的时候,别人会说太好了。他们不恐惧死亡,当然他们也有恐惧,是当灵魂和肉体要分离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是灵魂不能上天堂。爱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情感一直被对立的情感所左右。所谓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但爱不是这样的。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情感有别于他人,但施与的爱却是同等的。我是没有宗教的,我只是有信念,艺术家要有信念最好不要有宗教。”
吕楠被现实中的庄严肃穆、虔诚和爱所感染,但没有因为拍宗教而皈依宗教,宗教只是他选择的题材,题材对于吕楠并不重要,或者说题材的重要,在于它是否“能帮我解决问题,它只是我解决问题的手段”。吕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摄影师能否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把握住现实中具有更深刻更伟大一点的东西,这是摄影成为艺术的理由,也是摄影师成为艺术家的理由,这就是吕楠的信念,也是吕楠的宗教。什么是现实的“真实”?不同艺术家,不但看到的现实不一样,由现实引起的感觉更是千差万别。艺术而不是所有摄影图片的价值,在于对现实场景、生活瞬间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感觉不同,而发生的表达方式上的不同,看艺术就是看不同艺术家眼中的形象,及其形象所隐含的作者感觉。什么是农民生活中的“真实”?也许呆滞的目光,麻木的神情,劳动时的艰辛和痛苦的动作和表情,都是真实的,它存在任何地域,乃至在西藏吕楠拍摄的对象中,一直存在。但摄影师要什么,选择甚至是挖掘什么样的瞬间至关重要。如吕楠所说:“我一直认为照相机只是一个工具。如果说利用这个工具做出的东西没有达到其他领域的水准,那么不是工具有问题,一定是使用工具的人出了问题。比如说摄影包括对真实的认识,往往照相机是最会骗人的,真实需要的是挖掘。摄影师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影像要在一瞬间形成,但不意味摄影师总要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心灵的思考是必然性,不是偶然性。我是要关心人们根本、持久和本质的东西。照片传达出来的都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总是偶然的表象的,我希望能解决解决这些问题。”
吕楠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摄影史要解决的问题。我同意吕楠的看法:“苏珊·桑塔格在摄影论里说在一个摄影展览上,题材与题材之间留下的是巨大的鸿沟。”,“艺术是以整体向世界说话的,它形成不了整体。”摄影在以前“存活只能为报纸和杂志工作。接受人家的委派你才能拍照片你才能存活,他面临这么一个困境。实际上当时的摄影没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摄影在20世纪60年代电视出现的时候,得到一次解放,但是也很难。到了80年代就已经有人积累出作品了,个人已经有连续性了,可以谈到摄影家啦,比如说辛迪·舍曼。”“一个重大事件可以谈照片,不能谈摄影师。”“摄影一直谈照片,不能谈摄影师。”在这里,吕楠涉及到两个问题很重要,一是摄影师的个人感觉,以及相关的语言、风格等因素;一个即所谓“真实”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艺术个性的重要性,涉及到艺术的一般规律,此不赘述。摄影师证明自己是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师,你得靠个人感觉的独特性,以及语言的独特性,你才可能弥合像苏姗·桑塔格说的“题材与题材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获得吕楠说的“整体性”--即整体的个人特征。当然,做摄影师--照相馆里的摄影师和相当数量的新闻摄影师,是另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真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概念,任何作品都没有空泛的“真实”,你必须在作品中给出“真实”的具体性,而这种具体性,虽然涉及对现实的社会学分析,但在我看来,摄影成为艺术,其“真实”性主要涉及到一个摄影师的个人立场。如果一个偶然场合,恰好发生了一个偶发事件,你偶然拿着相机,你拍下了一张或者若干张照片;或者,你拍摄了常人看不到的新奇的现实场景和人和的,因为它成为绝无仅有的事件见证,使照片显得弥足“珍贵”。也许从社会档案、新闻的意义上,这种真实性依然不容置疑,所有的区别在于谁更专业--焦距、光圈、影调、构图等等,但在我看来,摄影首先是超越社会档案意义上的“被雇佣”关系时,才能被称为艺术。就是说,真实,哪怕是涉及到对一个事件的见证,摄影师作为艺术家,他的个人立场,独到的视角,也是首要的尺度。因为人类生存的每个时间段,大多数个人,只是被特定意识形态言说的个体,所以,真正的个人感觉和自由心境,才牵涉到艺术的“真实”。
我问吕楠在拍摄过程中是否注意到影调或者构图、造型处理上的技术问题,他回答说:“什么都看不到,什么光影,我从开始做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到。我看的是整体,我的作品需要的是景深,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人在这个整体里的处理是很难的。我一个镜头可能要拍几个胶卷。而且我的照片不剪裁。”但整体感是一个不断地选择、取舍、凝练的过程。如秋收,他拍了四次,就是说他在四年的时间内,会连续拍同一个场景。我粗略计算一下《四季》中的秋收场景,吕楠大概选了二十几张,我们无法确知吕楠是从多少张照片中选择出来的,但我们会知道这个比例是惊人的。我的意思是想说,对一个场景的惊人拍摄量,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突出、完善自己想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吕楠和拍摄对象的对话过程,也是吕楠确立表达语言和他自己内在灵魂的对话过程,同时是吕楠和西方伟大古典传统的对话过程。这三个过程,缺一不可,使吕楠逐渐清楚了他要的东西--劳动成为劳动自身、爱、亲情等,这是今天日渐消失的,却是西藏农民日常生活中异常突出的人类“伟大情怀”,所以,对于吕楠,只有庄严和肃穆,才能表达他看到的这一“真实”。如果哪一天,我们能够把吕楠在同一个场景中“淘汰”的照片,和他选择的照片,作一个详细比较,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吕楠如何在一连串日常生活的偶然瞬间中,寻找到他心中具有“庄严”感觉的瞬间。我以为这是《四季》能保持整体感觉的一把“钥匙”。
庄严感要求画面单纯和稳重,如春播、秋收之类的场景,每一个场景的人物劳动情节,都突出一种劳作,播种的画面就只是播种的情节,拾麦穗的画面就只是拾麦穗的情节,也许拾麦穗和割麦子的人是在同一个场景中,但每一种劳作都被吕楠单纯出来。而且人物以一两个到三四个为主,几乎没有大场面的热闹场景。劳动动作也不特意强调动感,总是在动态中选择最能说明该动作的最具稳定感觉的姿态。所有的亲情场面,情节也非常的单纯,突出最能交代人物之间亲情关系的情节,绝没有多余的动作和节外生枝的情节。《四季》以近景构图居多,多数画面的人物之间都有一个眼神向画面中心聚拢的特点,这多由于画面情节总有一个人物关注的中心点所决定,它使此类作品的构图趋于稳定。中景构图的视线大多居于画面的中间位置,把天地一分两半,单靠影调的大面积灰色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背景,托出主要人物的动作,人物也大多占据画面主要位置,动作的单纯化,也给整体构图带来稳定感觉。影调处理,是《四季》中最引人入胜的特点,室外光线下的大中型场景,多不强调强烈的阳光效果,像我们通常看到的拍西藏作品那样。吕楠总是把天空和大地的浑然一体,作为灰色调的背景,突出人物大体统一的暗色块,以突出人物的分量感觉。而室内光线的作品,多以类似伦勃朗式的暗背景,突出人物的灰色块尤其是面部的浅灰色块。吕楠说夏季强烈的阳光使室内光线对比强烈,致使他很少选择夏季来拍摄室内的作品。为了更好地处理室内光线,吕楠常常选择把窗户用纱布遮挡的方法,使室内人物的光线更加柔和。我没有问过吕楠是否使用闪光灯,但可以感觉到他的作品从没有人为化的影调特征,自然光线下的人物的影调真实自然,正是他要的因素之一。尽管我们无法以确知吕楠从西方古典主义艺术借鉴的细节,但从“四季”构图、影调和单纯化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猜想到作者的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的修养之深。
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以处理“乐”和“哀”两类画面为例,《收割后感谢神赐予收成的人们》,是人们高举着庄稼向天欢呼的场面,天空在画面中占据了较大面积。人物欢呼的动作,都选择了稳定的站次,欢乐而不雀跃。而且,喜悦的表情统一在暗色块的人物动作中,也不十分突出。《跳舞的姑娘们》,虽是载歌载舞的场面,却被作者放在画面较远的位置,故意不突出舞蹈的欢快动作,而是把舞蹈融入天、山、地之间,让整个画面呈现一种与自然共舞的气氛。只有姑娘们白色的上衣袖子,作为亮色块,成为画面最活跃最欢快的因素,但因为面积小,欢快因素显得非常有节制。《跳绳的孩子们》也以同样的拍摄方式,突出的是人的欢快与自然和谐的气氛。“哀”画面处理,则多着力于人物表情的刻画,如《刚刚确知女儿右眼失明的母亲》、《妻子和被马车撞伤的丈夫》、《丈夫和失明的妻子》,对于如此悲惨的结果,作者并没有强调凄惨的氛围,也没有强调母亲、妻子、丈夫的痛苦表情,而是突出了他们对于不幸者的关爱,以及亲人的“承受”感觉。哀、乐情绪控制的感觉,既来自吕楠的拍摄对象,也被作者有意的强调出来。这其实也符合中国儒家的传统美学观念,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种对于画面情绪的控制力,不仅表现在对哀伤欢乐情绪画面的控制中,我们如果仔细看所有的画面处理,会发现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控制的能力。《四季》的每一幅作品,所以能始终统一在庄严、肃穆、大器、凝重的整体气氛中,控制力可能是吕楠最重要的语言方式。
来源:http://blog.poemlife.com/user1/Bethesda/archives/2008/60109.html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