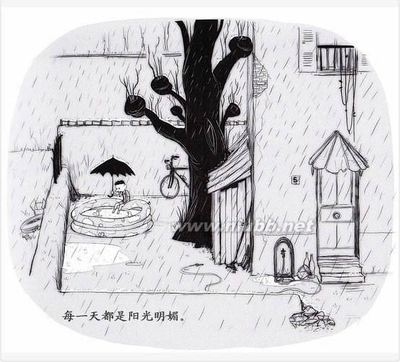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收藏,并从各自的爱好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无穷的乐趣。我有许多收藏品,比如伞、书签、陶瓷、邮票等,但最花费精力、最有成就感、也最廉价的收藏当属我的几十本剪报。
喜欢剪报也许与自己念旧有关。一张张报纸是我看过的东西,就那么扔掉或是卖掉吗?连同那些奇文妙章,连同那些精美的图片?实在不忍。但又不能把所有的报纸全部收藏起来,于是也不知是从哪一天,我在不知不觉中拿起剪刀开始剪报了,现在已剪辑了厚厚的几十本。我收藏起的是一份份永恒的记忆,她们成了我的一个个知识宝库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剪报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起名叫《报海采珍》,再根据分类独立成篇,剪的最多的是散文,散文篇已经有八本了,其次是旅游,读书,美容,养生保健,美食,美容,女人,书法绘画,科学育儿,感情婚恋、花等等。
第二部分叫《一世瓷缘》,全部是与工作有关的,陶瓷艺术欣赏、本企业报道、陶瓷行业信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宣传报道文章。
我没有专门为剪报而订报,剪的最多的还是平常工作中常看到报纸,如淄博晚报、淄博日报、齐鲁晚报、人民日报等,主要是剪它们的副刊。
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曾经说过:“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不耐看主要看副刊。”当然有人曾预言说多少年后网络阅读将取代报纸,但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报纸仍是阅读率最高的纸质传媒。有位名人说得好,读报这件事对于千千万万的人来说,几乎和吃饭一样不可少的。与正襟危坐在电脑前不一样,我喜欢以各种随意的姿态捧读的感觉,喜欢那报纸的清香,喜欢剪刀走过报纸的嚓嚓声,喜欢做一个编辑的感觉。
报纸看过后把需要剪的内容单独放在一起就算粗选一遍了,粗选后的报纸是一堆又一堆。书橱里放不下,就放在衣橱里,酒柜里。粗选到一定量后进行粗剪,然后再精剪、分类,根据主题和分类排版,根据排版情况进行最后的精剪,再粘贴、配图,每次粘贴后要及时用平整的重物压住,我的办法是用一块平整的木板压住剪报本,上面放两个重哑铃,这样能保证剪报本的平整。最后的工作是编上页号,打出目录。一份象模象样的剪报本就这样正式出版了,我俨然成了一个编辑。
夜阑人静之时,我时常拿出我的剪报集浏览翻阅,仔细品味,真有一种说不出的享受。我十分钦佩杨绛关于读书的观点: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每当翻看我的剪报本,也深有同感。很有意思的是,我多年前剪报的作者有很多已经成为朋友。我最喜欢剪的文章作者如郝永勃、周蓬桦、韩青、于洪亮,还有马瑞芳、张炜等名家,天长日久,看他们的文章,感觉是与老友相守,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又陶冶了情操,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我能够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还能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真的是得益于我的剪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那些人也并不都是专职作家,有很多普通人。那为什么我还愿意看,还被感动,愿意剪下来收藏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们真实,有真情。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业他的性别他的年龄,心里都有自己的文章,或是散文,或是随笔,或是小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有些人限于种种条件无法一一诉诸笔端。看的多了,自己的一些感悟也自然地流露出来。终于,我也有了专属于自己的剪报本,上面有都是我近年在淄博晚报等报纸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
我从十七岁腿受伤以来,各种各样的疾病经常把我扔在床上。在床上,除了疼痛之外,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是读书,二是剪报。如果没有剪报,我在床上的日子是多么无聊,如果没有生病在床,平日就是风风火火地为工作家庭奔波忙碌,我的剪报也没有时间整理。去年春节期间,做了一个小手术,躺在床上许多日子。身体虽然躺着,但我的手、眼却忙碌得很。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我的剪报声喀嚓喀嚓,满床上、窗台上、桌子上、沙发上、地上、床头上都是报纸片,我淹没在报纸堆里。这情景,让我想起电影《桃花运》中那个爱钱的李小璐,她梦见面值1000元的美元像雪片一样纷纷落在她的身上,她被淹没在钱堆里十分快乐。我的报纸也是我梦中的财富,我在报纸堆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痛并快乐的日子。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如果上帝给你关上了一道门,他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疾病让我下不了床,走不出门,买不了新衣,办不了年货,但是一把剪刀让我剪开了另一片天空。几大本剪报本渐渐丰盈起来,一本本剪报编辑成册,心中很有成就感。
张爱玲说,悄然而逝的时光之中到处可以发现一些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生,一世。
少年时读《红楼梦》,对里面错综的人物关系总也弄不清楚,无意中在中国青年报上得到一张红楼梦的人物图谱,那种感觉真是欣喜异常!后来一直成为我阅读《红楼梦》的指导,成为我珍贵的剪报。工作中若有人卖废报纸杂志,我都要先收过来过滤一遍。从里面总能淘出一些宝贝来。我平时也很注意收集图片,不放过任何一张街头广告,放在剪报中做插图,令版面生辉。有一年随女工活动去安丘青云山,就收获了一张剪报。当时很多人坐在地上看演出,我看见一个人坐在一张报纸上,注意到上面有关于桃花的内容,我就站在人家身后一直等着,等人家看完演出起身走了,我才如获至宝地把那张报纸从地上捡起来,是潍坊日报副刊的一篇文章叫:“倘若桃花可称魂”。
多年前,我们姊妹几个一起回青州老家,临走时大哥一家说要顺路到我家看看,就一起回张店来了。一进门,大哥的司机就惊讶地问:“这房子是不是很久没人住了?”,我笑着说:“我们一直住着呀。”我明白了,他看见我家客厅里到处是报纸,地上,沙发上,被报纸铺满了。他们准备帮我收拾一下,我说你们别动,我自己来。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挪出一个地方让他们坐下。我也并没觉得难为情,因为,剪报工作必须有这样一个场面。
五光十色的网络再怎么眼花缭乱,我依然衷情于我的剪报,因为,青灯黄卷的韵致,电脑是不能给的。
(2010年8月5日《淄博晚报》城市笔记特约撰稿)
剪报让我有了自己的剪报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