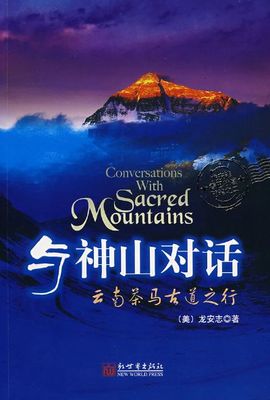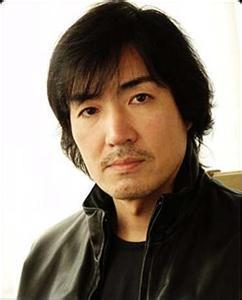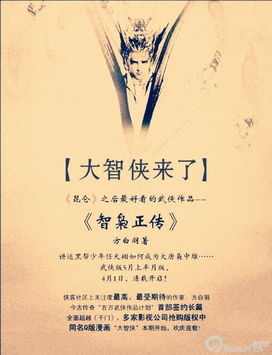方白羽-智枭48
安庆绪在李嗣业快如疾风的陌刀追杀下,后力不继,得已向后退却,这令唐军声势大振,纷纷高呼着爬上城墙。安庆绪眼见攀上城头的唐军越来越多,守军渐有不支之势,他突然一胡语高呼:“伏倒!放箭!”。
听到这命令的叛军立刻原地伏倒,几乎同时,密集的破空声已如蝗虫飞过般铺天盖地地而来,几乎完全覆盖了就要被唐军占领的这一段城墙。密集的箭雨犹如死神掠过城头,粹不及防的唐军将士纷纷中箭。只有听到安庆绪号令的叛军兵将,巧妙地躲过了这一轮排驽的齐射。
原来这是司马瑜在城内设下的第二道防线,他将无数排驽和连环弩架设在城内的房顶之上,一旦唐军攻上城墙,便由城墙上指挥作战的将领以胡语下达命令。听到命令的守军立刻原地伏倒,跟着密集的箭雨就会紧随而至,任唐军再多再勇猛,也挡不住如此密集的箭雨。
李嗣业也身中数简,眼见安禄山又起身杀回,他还想迎战,却被几个伤势稍轻的亲兵强行架离战场,顺云梯滑下城楼。下面的亲兵接住李嗣业时,但见他身上血流如注,已受重伤,众将士急忙将之送到后方包扎。安西军主将受伤,军心大受影响,好不容易占领的一段城墙,又被叛军夺了回去。
双方激战打天黑,唐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依旧没能攻上城墙。不仅如此,李嗣业还被叛军排驽重伤,这是邺城战役以来以一个身负重伤的唐军主将,军心大受打击,九路大军只能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史思明的主力在准备充分、修整完备之后,徐徐逼近邺城附近,对唐军的威胁越来越大。这时于朝恩又出昏招,下令引漳河之水灌城。河水滚滚涌入邺城,这虽然给邺城守军造成了一点不便,却给唐军造成了更大的麻烦。洪水将邺城周围的原野变成了一批泥泞。无论攻城器还是人马过去,都会陷入泥泞之中,成为城上守军的活靶子。攻城行动难以为继,于朝恩又为邺城守军赢得的几天喘息的时间。
而此时史思明已看出唐军久攻不下,早已人疲马乏,而且大军最重要的粮食,在史思明的骚扰拦截下,也越来越紧缺。他依照司马瑜的计谋徐徐逼近到离邺城不足五十里之处,不过他依然不急于与唐军决战,只是加紧派出轻骑骚扰,拦截唐军粮草,一点点地蚕食唐军优势。现在就算是以鱼朝恩的脑子,也看出与史思明大军决战已是在所难免。经过与九路节度使商议,鱼朝恩派出以李光弼为首,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为副的四路大军迎击史思明,以郭子仪为首的五路大军则继续围困邺城。李光弼率二十万人马来到滏水,就看史思明十三万大军早已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
史思明大军侧翼的高坡之上,司马瑜手执窥天珠仔细观察着唐军的排兵布阵。墨子留下的窥天珠原本是观察天象的一期,在司马瑜手中却成了侦查军情的绝妙工具。有窥天珠之助,唐军的排兵布阵和兵力调遣就如同实在眼前一般清楚。
“速报史将军,李光弼大军正面只是佯攻,另有三万精锐骑兵正悄悄向我军后方迂回包抄。这是李光弼仅有的骑兵部队,只要先干掉它,唐军就只剩下挨打的份。”司马瑜收起窥天珠,向随行的偏将下达了自己的命令。
偏将应声而去,不一会儿就见史思明大军在后方布置起来,司马瑜把玩着手中的窥天珠,嘴边泛起了一丝得意的微笑,心中暗自感慨:这哪里是窥天珠?简直就是胜利珠啊!有了它,对手的一切兵力部署一览无余,而己方的部署对手却一无所知,难怪当年墨家军纵横天下,屡屡以弱胜强,无数次击败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对手。除了墨家弟子的勇武和墨家兵法的高明,只怕这窥天珠才是墨家军天下无敌的最大秘密。
仔细将窥天珠收入袖中藏好,司马瑜调转马头往己方中军疾驰。虽然他取得过无数次胜利,但没有一次能像这次一样信心百倍,胸有成竹。
就在司马瑜仔细观察唐军兵力调动之时,任天翔也在不足五里之遥观察着叛军的阵地。他原不想再卷入战争,不过由于自己被司马瑜利用,所以他感觉自己有责任弥补犯下的过失。他原本率义门众士在郭子仪帐下效力,但鱼朝恩分兵之时,却死活要将郭子仪留下攻邺城,所以郭子仪便将他推荐给李光弼,因为他对司马瑜的熟悉程度,显然在李光弼之上。
李光弼与郭子仪虽然都出自于溯方军,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郭子仪宽容大度,李光弼却是个不苟言笑,治军极严的铁血军人,在军事上极其自负。他也有资格自负,因为全军阵中,唯有郭子仪的战功胜他一筹。所以他对郭子仪推荐的任天翔,心中纵使并不怎么看重,但表面上还是给足了面子,让任天翔可以在军中自由出入,并以幕僚的身份列席其最高军事会议。
李光弼对自己的态度任天翔心知肚明,不过他并不计较,他只想帮助唐军击败史思明大军,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放走司马瑜的过失。
心术越见精明的任天翔,眼力也越发锐利。虽然他看不到叛军后方的军事调动,却发现了远处那扬起的尘土。虽然若隐若现极不明显,而且很快就被风吹散,但他却立刻就想到,叛军后方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从扬起的尘土看,至少是数万人的大规模调动。
通常后军是粮草轻重所在,在大战来临前决不该有大的调动,叛军的举动显然有些蹊跷。联想到今日一大早,李光弼就令骑兵集结,先于大军出发,莫非是要大范围迂回到叛军后方,在唐军与叛军正面交锋之时,作为胜负手从叛军后方实施突袭直插史思明的中军大帐?
想到这任天翔心中一颤。这计划不能说不好,但是叛军已知晓李光弼的部署,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任天翔虽然不敢肯定叛军已知唐军精锐骑兵在做大范围迂回,但临战之前叛军后方隐约扬起的尘土,却让他心中生出一丝警惕。他急忙勒转马头,招呼几名随从道:“走!速见李将军。”
一路疾驰回营,任天翔直奔李光弼中军大帐,对正在为大战做最后部署的李光弼道“将军是否有令骑兵助理迂回袭击叛军后方的计划?”
李光弼对任天翔临战之前节外生枝显然有些不满,不过还是耐着性子答道:“不错,三万骑兵已经出发近一个时辰,按计划两个时辰之后,他们将在叛军后方发动突袭。”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改变计划?”任天翔忙问。得知三万骑兵已经出发近一个小时,任天翔心中又是一紧。他知道这三万骑兵是李光弼手中最大的机动部队,一旦损失,唐军就只有用步兵去迎击闻名天下的范阳铁骑。但此刻就算千里快马也无法将他们追回来,更别说让他们改变计划了。
不过李光弼却道:“有,我与骑兵统领王思礼有约定,只要我燃起三股狼烟,就表示局势有变,骑兵将立刻撤回。”
任天翔心下一宽,忙道:“太好了,望将军速令骑兵撤回。”
李光弼不解道:“为什么?”
任天翔忙将自己的担忧简单说了一遍,最后道:“咱们三万精锐骑兵刚启程不久,史思明后军就在做大规模调动,我担心咱们的计划已被他识破,三万精锐骑兵将落入他的陷阱。”
李光弼不以为然道:“公子仅凭天空中扬起的一点尘土,就妄言叛军会有所准备?要知道这个计划今早才由本帅亲自制定,并且立刻执行。这个计划只有我与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三位将军知晓,史思明如何得知?”
任天翔知道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都是独当一方的节度使,忠诚和谨慎都不容置疑,要说他们会走漏最重要的军事计划,这实在令人不可想象。不过史思明后军的调动实在蹊跷,领任天翔不敢大意,他不顾李光弼的不快,耐心解释道:“从扬起尘土看,那是数万人马的调动,绝非偶然。先如今史思明身边有司马瑜这样的鬼才,将军不可大意啊!”
李光弼摇头道:“没有准确的情报,就算是孙武重生,也决不会临时调动大军应付来自后方的袭击。就算我军的计划被叛军奸细探知,他也还在回营的路上,史思明如何提前得知?”说到这里他微微一顿,若有所思地问,“你在那里看到叛军后方的扬尘?”
任天翔道:“就在离叛军前锋五里之外。”
李光弼在心中默默一算,哑然失笑:“叛军阵地纵深近十里,你在其前方五里之外看到扬尘,就能准确判断出那是数万人马的调动?笨将军戎马半生,自问也没有这等眼力和判断力,也没听说过有人能在十五里之外通过扬尘判断兵马调动规模,公子目力难道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高明百倍?”
众将轰然大笑,纷纷道:“听说公子原来只是个纨绔子弟,没想到却将我们这些戎马半生的军汉全部都比了下去。”
任天翔心知旁人实在难以理解心术之妙,他也无法向旁人说清心术的秘诀,面对众将的嘲笑和质疑不禁无言以对。李光弼断然一挥手:“大战之前临时改变计划,实为军中大忌,从现在起任何人再妄言变阵,立斩不饶!”
众将收起嬉笑,轰然答应。李光弼令旗一挥,昂然下令“:照原计划加速推进,务必在正午之前,突破叛军第一道防线。”
众将轰然应诺,纷纷领令而去。任天翔心知李光弼治军极严,稍有违令就要受军法处置,暗忖道:“或许只是巧合,司马瑜就算再精明,也不可能仅凭猜测来调动大军,也许我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激越的战鼓在旷野回荡,唐军以突击的楔形阵向史思明的防线缓缓推进。随着两军距离的接近,唐军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犹如一股奔涌的激流。当他们接近叛军阵前,就见一阵弩箭犹如飞蝗从敌阵中飞出,铺天盖地落在冲锋的人群中,还好前锋士兵都有盾牌护体,损失并不算大。当叛军两轮箭雨过后,唐军冲锋已冲破叛军的鹿角障碍,与叛军厮杀在一起。声嘶力竭的呐喊声,即便是在中军的任天翔也清晰可闻。
史思明摆出的是一个以防守为主的环形阵,依托预先的工事进行抵抗。唐军人数虽然比叛军多出不少,但是分属四个节度使指挥,四支队伍战斗力参差不齐。李光弼和老将王思礼的部队战斗力与叛军精锐不相伯仲,但许叔冀和鲁炅的部队战斗力却明显比叛军差了一大截,加上唐军是主攻方,面对有营寨和工事依托的叛军,一时间竟占不到半点便宜。
李光弼焦急地遥望叛军中军大营方向,按约定当前方激战正酣之时,包抄到史思明后方的骑兵将向其中军发起冲击,只要令史思明中军动摇甚至混乱,叛军的士气定受到打击。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后方的战况很难及时通达全军,有时候来自后方的一个谣言,就可以动摇守军的信心,到那时叛军的防线就将土崩瓦解。
叛军后方终于传来隐隐的马蹄声和呐喊声,李光弼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轻松,他相信以唐军最精锐的三万骑兵发起的突袭,定会让史思明手忙脚乱。现在史思明理应将对付骑兵的长枪队放在了防守的前线,其后军面对骑兵的突然袭击,即便不会一触即溃,也难以挡住骑兵的冲击。
李光弼正待下令部队全力进攻,但以他现在所在的位置,仅能听到那隐约的马蹄声。他不禁奇道:“公子从何得知远方的战况?”
任天翔指向天边道:“尘土起处止于一线,说明骑兵根本没能突破叛军后方的防线,而且他们被困一偶,说明叛军早有准备,骑兵危险了!”
李光弼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但见叛军后方弥漫着依稀的尘土,他心中正有些将信将疑,突听前锋传来阵阵欢呼,原来叛军开始退缩,环形阵出现了一个口子,唐军正从缺口蜂拥而入,声威大震。
“任公子好像看错了,咱们的骑兵受到了奇效,叛军军心开始动摇。”一名将领呵呵大笑,转向李光弼道,“下令发起总攻吧,机会难得!”
此刻李光弼神情却凝重起来,他多次与史思明交过手,知道史军的战队里,这么快就防线动摇,实在令人生疑。加上任天翔的提醒,他隐约感觉到其中有诈。
但是现在唐军已不受他节制,除了他的中军未动,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的兵马,已争先口后越过叛军防线,向史思明的中军大营突进。
“不好!叛军后方的尘土,开始逐渐散去。”就在唐军震耳欲聋的欢呼呐喊声中,忽听任天翔失声轻呼、李光弼连忙举目望去,就见叛军后方再无新的尘土扬起,侧耳聆听,先前那隐约的马蹄声和呐喊声也都消失,李光弼心中一凛,脸上微微变色。他知道这意味着三万骑兵很可能已被叛军消灭。不过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他一时还难以接受。
在李光弼和任天翔看不到的叛军后方战线,司马瑜正在心满意足地看着叛军打扫战场。犹豫有窥天珠之助,他预先在后方阵线设下了一个由各种战车和骡车组成的口袋阵。当三万唐军骑兵发起突袭时,正前方是骑兵的克星,由无数长矛方阵组成的防守阵线,后方则是战车和骡车合围,将三万骑兵包围其中,成为弓箭手的活靶子。司马瑜亲自指挥了对这三万骑兵的屠杀,他知道只要消灭这三万精锐,李光弼就只剩下挨打的份了。
“报!唐军前锋已突破第一道防线!”传令兵飞速来报,这让司马瑜十分得意。本来像这样的战报,史思明完全可以不必派人来报告他,只要按原定计划行动就够了,特意派人来报,显然是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可见他在史思明心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
“很好,你回报史将军,就按原计划执行,我即刻率军赶去增援。”司马瑜令副将挥动令旗,调兵遣将,让后军尽快赶到中军增援史思明。
唐军前锋突破叛军第一道防线后,不约而同地直扑史思明中军大营,但见前方一道高约一丈,宽数十丈的营寨巍然伫立,寨前鹿角森然,寨上弓箭手林立,不等唐军士兵靠近,箭雨就倾泻而来。要想以步兵破此营寨,无疑以卵击石。前锋将领见状急令后撤,但见此时叛军骑兵已从两翼包抄,截断了唐军的退路。唐军前锋顿时进退失据,攻势顿挫。
李光弼见唐军前锋身陷敌阵,再不救援就将全军覆没,他略作权衡,便令中军全力出击,冒险一搏。就在李光弼中军全线出击之时,立在高处的司马瑜已将唐军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他向一旁的副将点了点头,副将挥动令旗,向史思明示意唐军突击的方向。史思明亲率精锐骑师,迎头痛击。
唐军失去宝贵的骑兵,在来去如风的范阳精骑面前,只能被动挨打。但见范阳骑兵呼啸来去,他们并不交战,只是远处乱箭齐射,不断消耗唐军的战力。唐军仅凭步卒,只能被动防守,人数虽众却对叛军构不成任何威胁。
经过数轮消耗,史思明亲率骑师全线出击,此时就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溯方军,也难以抵挡叛军的突击。
眼看战事不利,鲁炅与许叔冀最先带兵后撤。未经将令擅自撤离,顿时动摇了唐军军心,众将士争先恐后随之后撤,唐军的防线开始崩溃。
李光弼眼看唐军全线溃败,只得一声长叹,率溯方军殿后,掩护全军撤退,同时令人往鱼朝恩处求援。此时史思明的骑兵已经冲到李光弼前方,对溃败的唐军轮番截杀,李光弼派出求援的将领,也死在叛军手里。
任天翔见状,立刻率义门众士奋力突围,直奔唐军大营求援。他最先见到郭子仪,忙将战情简略汇报、郭子仪心知救兵如救火,来不及禀报鱼朝恩,便率本部人马接应李光弼。两军在半道汇合,郭子仪的生力军打退了史思明的追兵,暂时稳住了唐军阵脚。
唐军的调动很快就落在司马瑜眼里,有窥天珠之助,他比唐军统帅鱼朝恩还先一步知道唐军的调动情况,他立刻令人燃起狼烟,向邺城的安庆绪发出了反攻的信号。
安庆绪看到约定的信号,令人打开城门,亲率守军发起反攻。此时唐军若调度得当,凭其优势兵力,还可与叛军一战。但鱼朝恩从未经历过战阵,但听到四周喊杀声震天,邺城的守军竟然发动反攻,他早已乱了方寸,急令中军后撤。其余几路兵马见中军大旗摇动,不知就里,也纷纷后撤。各节度使皆有保存实力的私心,竞相撤离战场,撤退很快就变成了溃败到最后将不知帅,帅不知兵,数十万大军已成一盘散沙。到了这个时候,即便以郭子仪,李光弼之能,也是无力回天了。
叛军在史思明率领下一路追杀,不给唐军任何喘息之机。沿途州县听说唐军六十万大军竟被击溃,早已吓破了胆。而唐军在大败之后也变成了土匪,趁混乱洗劫百姓,因此沿途各州县不等叛军杀到,地方官就纷纷弃城而逃,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几万残兵一直败退到洛阳,也没得到地方的补给。而面对已经十室九空的洛阳,二人都知道仅凭这几万败兵绝对难以坚守,二人经过商议,决定放弃洛阳,由郭子仪退守潼关,李光弼则率军退守河阳,以牵制史思明的大军继续西进、威慑长安。
史思明对安庆绪的举动倒也不生气,他将司马瑜请来,意味深长地笑道:“现在,该是先生实现诺言的时候了。”
司马瑜颔首道:“将军放心,在下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办到。不过将军得先做一件事。”
史思明忙问:“什么事?”
司马瑜道:“在城外搭高台,邀圣上敬告天地,歃血为盟,兴复大燕。”
史思明大笑道:“好!就依先生所嘱,设坛祭天,共襄盛举!”
史思明一声令下,高台克日而成,他以归还玉玺为由,邀安庆绪出城结盟祭天。与此同时,司马瑜也修书一封,令辛乙悄悄送到城中。安庆绪看到司马瑜的密函,便不顾手下劝阻,立刻率五百精兵出城来见史思明。
安庆绪来到史思明大帐,但见帐下刀斧手林立,立刻心知不妙。当即对史思明躬身拜道:“叔父在上,侄儿给您老请安。”
史思明并不还礼,只懒懒道:“陛下乃大燕皇帝,这不是折杀老夫么?”
安庆绪忙赔笑道:“大燕国的江山乃是叔父与先皇联手打下,侄儿不过是窃居此位。侄儿早有诺言,只要叔父解了邺城之围,侄儿便将这皇位禅让叔父,并以玉玺为凭,叔父难道怀疑侄儿的诚意?”
史思明手抚髯须冷笑道:“你先告诉我,你这皇位是如何而来?我义兄安禄山是如何死的?”
安庆绪一愣,正不知如何回答,就听史思明一声厉喝:“是你联络内侍李猪儿,以下犯上将我义兄弑杀。你以为此事办的天衣无缝,却不知我手中已有确凿证据,看你还能如何抵赖!”
当初安庆绪确实是将杀害安禄山替身的任务,交给负责服侍他的内侍李猪儿。这事办的十分隐秘,按说不该有人知晓,而且事成之后,安庆绪又听从司马瑜的建议,将李猪儿杀了灭口,而且是交由司马瑜亲自去办。这事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史思明怎么会知晓?
安庆绪正在狐疑,就见史思明拿出一封密函,展开在他面前。但见密函上将安庆绪下令杀害安庆绪的时间、地点、经过,等等细节交代的详详细细,密函下方的落款正是李猪儿。安庆绪愣了半晌,终于有所醒悟,急忙一跳而起,厉声喝道:“司马瑜那小子在哪里?快叫他出来见我!”
安庆绪身形方动,左右刀斧手已一拥而上,将他摁倒在地,他拼命挣扎,声嘶力竭地大叫:“我杀的只是先皇的替身,父亲在起事前就已经死了,有父皇的贴身侍卫可为我作证!”
史思明冷笑:“这种谎你也编的出来,好,你就告诉我谁可为你作证?”
安庆绪忽然想到,那些知道实情的侍卫,早已被自己尽数灭口,现在知道这隐情的除了司马瑜,就只剩下辛氏兄弟。他忙转脸向一旁的辛乙乞求:“阿乙你快告诉他们事情,告诉他们父皇早就已经死了,跟我没有关系!”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辛乙,他们虽然是史思明部下,但其中有不少人也是安禄山旧将,对他的儿子多少也还有几分旧情,所以很想知道真相。就见辛乙对安庆绪躬身一拜,愧然道:“陛下对我恩重如山,辛乙一直铭记在心,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望陛下恕罪。”
安庆绪一愣,跟着不禁破口大骂“:辛乙你这个王八蛋,居然在这个时候背叛我!看我不诛你九族,灭你全家!”
辛乙眼中刚开始还有些不忍,待听到诛灭九族的话,他眼中陡然闪过一丝寒芒,转向史思明道:“将军明鉴,陛下所说之事我一无所知,不敢为他作伪证,望将军为小人做主。”
史思明点点头,不再理会拼命挣扎号叫的安庆绪,转向众将问道:“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弑杀先帝者该当何罪?”
“杀无赦!”众将异口同声地道。就是先前还对安庆绪抱有几分旧情的安禄山旧部,现在也是同仇敌忾,恨不能亲手为旧主报仇雪恨。
史思明对众将的回答十分满意,不过他却故作悲戚地叹道:“虽然这小子弑父杀君,理应千刀万剐,但念在他好歹也做过几天皇帝,便留他个全尸吧。”说着他微微摆了摆手,一名心腹将领立刻心领神会,取下长弓,将弓弦套在安庆绪脖子,然后慢慢转动长弓,就见弓弦逐渐绞紧,一点点勒紧了安庆绪的脖子。
安庆绪拼命挣扎,奈何手脚俱被刀斧手摁住,无法挣脱。他只能恨恨地瞪着史思明和辛乙,带着满腔的愤懑和不甘,被弓弦生生绞杀。
“将安庆绪弑父之罪诏告三军,然后以王礼厚葬吧。”史思明似乎有些伤感,不过眼中却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他对几名心腹将领一挥手,“即刻率军入城,若遇抵抗,即刻予以消灭。”
“等等!”司马瑜从后帐中缓缓踱出,他的脸上似乎隐有悲戚,似乎在为故主的死难过。看到兵卒将安庆绪的尸体拖了出去,他才对史思明道:“请将军容我先行入城,让邺城守军开门迎接将军。”
史思明呵呵笑道:“这样最好,那就有劳先生了。”
司马瑜带着辛氏兄弟来到邺城,将安庆绪之死向大燕国幸存的将士通报后,众人虽有疑问,但也不敢与史思明大军抗衡,唯有一人径直来到司马瑜面前,涩声质问:“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
司马瑜羞惭道:“史思明假借归还玉玺,将陛下骗出邺城,然后借口陛下弑杀先皇,所以......”安秀珍一把扣住司马瑜要害,厉声质问:“你明知道父皇的死跟我哥哥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不阻止?”
辛乙见安秀珍威胁司马瑜,本能地拔刀指向其后心,安秀珍却不管不顾,只盯着司马瑜的眼眸。司马瑜示意辛乙收起兵刃,然后挥手令众人退下,待殿中仅剩他与安秀珍二人,他才无奈道:“史思明狼子之心,昭然若揭,就算没有先帝这事,他也会另找借口。”
安秀贞凤目含煞,涩声问:“我哥哥死了,为何你却还活着?”
“因为我不想做无谓的牺牲,我要留下自己这条性命,为陛下报仇雪恨。”司马瑜说到这语气一转,黯然叹道:“再说你还在邺城,还在史思明大军的威胁之下,我又岂能不顾你而去?我现在向史思明屈服,只是权宜之计,以后但有机会,我定要为陛下报仇!”
安秀贞眼中虽然还有质疑,但面对司马瑜坦诚的眼神,她最终还是缓缓的放开了手,涩声道:“但愿你说的是真话,你要是骗我,我会跟你一起死。”说完放开司马瑜,毅然转身而去。
见安秀贞要走,司马瑜忙道:“贞妹要去哪里?”安秀贞苦笑道:“我不走,难道要向史思明乞命?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我还要留着这条命,为我哥哥报仇!”
不等司马瑜再阻拦,安秀贞已飘然而去。司马瑜眼中隐约有些不舍,但最终还是没有再追,只是缓缓来到殿前,对守候在门外的将领吩咐:“打开城门,迎接史将军入城。”
史思明入城后,听说安秀贞已离去,他脸上喂喂变色,跺足道:“我忘了安庆绪还有个厉害的奶奶,虽然年事已高活不了几天,但在萨满教中她的地位无比尊崇。要是他追究起来,这麻烦可是不小。”
司马瑜胸有成竹地道:“将军不必担心蓬山老母,我向将军推荐一个人,有他在,蓬山老母和萨满教也只能对将军俯首帖耳。”
“是谁?”史思明忙问。
“魔门大教长佛多诞。”司马瑜从容道。
史思明微微变色,颔首道:“我听说过他的名号,确实可以与蓬山老母相抗。不过我与他素无交情,他凭什么帮我?”
司马瑜道:“佛多诞一直现在中原公开传教,只是苦于没有朝廷的扶持,要是将军肯将他的光明教立为国教,他定然乐意为将军效劳。”
史思明大喜道:“这有何难?只要肯为我效力,就算拜为国师也无妨。”
司马瑜颔首道:“既然将军有如此胸怀,我这就修书一封,邀他到将军帐下共商大事!”
史思明喜道:“这事便由先生替我全权处理,就让他到范阳来见我,本将军拜他为国师,奉光明教为国教。”
第二天一早,史思明挟击败六十万唐军的雄威,风风光光地班师回范阳。离去前他将邺城改为相州,留长子史朝义驻守。回到范阳后,他在手下众将的力劝下,自立为帝,成为大燕国的新皇帝。
在史思明登基,忙着肃清安氏父子影响的这段时间,大唐终于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唐帝趁机收拾残局,赏罚功罪。按说邺城会战这样的惨败,理应斩几名将帅以正军纪,但邺城会战的主帅是鱼朝恩,是皇帝不顾李泌等人劝阻亲自任命,处罚他岂不是自搧耳光?如果不出发鱼朝恩,却将责任推给旁人,又何以让人心服?所以皇帝权衡再三,最终没有追究众将责任,反而提拔郭子仪为东、山东、河东诸道元帅,知东京留守,全权负责对叛军的防御。
另外还后赏了在这次战役中不幸故亡的两位节度使——李嗣业攻城时被毒箭所伤,在营中养伤时听到李光弼与史思明激战的号鼓,奋然而起欲往助战,结果伤口迸裂而死;鲁炅则是在败逃之时,其部下沿途烧杀掳掠,被地方官告到朝廷,鲁炅畏罪服毒自杀。二人俱不是死于战场,但皇帝依旧作为战死的功臣厚赏,以安各路唐军之心。
鱼朝恩不通军事又不听众将建议,最终酿成邺城惨败,怕皇上追究,便将责任一股脑推到郭子仪身上。只说郭子仪自恃功高,不听调遣,不尊号令,其余几路节度使也都看郭子仪颜色行事,而他这个宣慰使根本指挥不动兵马。这话触动了皇帝的心中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他并不怀疑郭子仪的忠诚,但是谁能保证他帐下的将士不会有自己的打算?要是他们都股东郭子仪拥兵自重,甚至另起炉灶,岂不是又是一个安禄山?
大唐已经仰仗郭子仪太多,不能再将前途和命运系于郭子仪一身。想到这里皇帝终于下了决心。就在史思明范阳称帝后不久,他下诏就郭子仪召回京城,溯方节度使一职交由李光弼代理。郭子仪虽然位列三公,却被肃宗剥夺了兵权,从此在京中闲赋。
任天翔一向与李光弼不对付,既然郭子仪被明升暗贬,他也就没有心思再留在军中效力。而且离京日久,他也想念留在长安的义门兄弟,便与杜刚、任侠、小川流云等人一道,随郭子仪回到长安。
义安堂与洪胜堂因再香积寺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安百姓心中威望更胜从前,得知它们的门主任天翔与兴唐名将郭子仪同回长安,全城百姓竟空城而出,去十里外夹道欢迎,这成为长安有史以来最大一场由百姓自发举行的盛事。
看到前来迎接的长安百姓,郭子仪不禁感动的热泪盈眶,心中那一点怨气也烟消云散。任天翔确实忧心忡忡,他知道如果之前郭子仪还有复职希望的话,现在却再无半点可能。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放心将军队交给一个民心所向、威望无双的将领,这次盛会是郭子仪人生的顶峰,也将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结。
虽然任天翔是守卫睢阳的功臣,又是义门的门主,但在百姓眼里,显然郭子仪才是主角。
任天翔识趣地避过一旁,并不上去凑趣。随着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就在他快要被所有人忘掉的时候,却发现还有一个更为低调的人,混杂在欢迎郭子仪的人群中,一身布衣,毫不引人注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