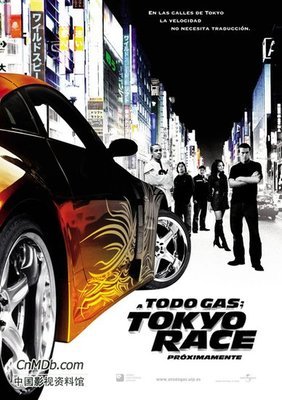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汉赋保存了大量的汉代史料,其中不乏史书所未载的细节。本书结合传世典籍、汉画像石和汉代简帛有关记载,考证了汉代乘舆、饮食、服饰、音乐、舞蹈、建筑、器物、神仙、风俗的细节,总结其特征,分析其演进,文史兼取,叙议相参,提要钩玄,颇多广益,考论沉稳而透辟,文风洗练而畅达,深可助于汉代研究的参考,浅可用于汉代文化的阅读,是了解汉代社会生活、艺术形态、风俗观念的学术性读物。
曹胜高主编《汉赋与汉代文明:汉赋与两汉史料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绪论
一
焦循、王国维等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谓一代之文学,非仅在形式,非仅在内容。以形式论,《诗经》以赋法取胜,本多赋体,汉有大赋,魏晋有骈赋、唐有律赋、宋有文赋,名虽非一,而形式相近,然常以汉赋为赋之代表。诗歌远祖古谣谚,周秦之行四言、魏晋之尚五言、隋唐七言代兴,宋明以后,不绝如潮,然论者、言者多以唐诗为诗歌之极致。小说、戏曲、词之创作亦类,其形式造就既早,其体裁变化有序,而创作之高潮、艺术之粲然者,皆在特定之时期,俟佳期一逝,则如花之凋零,虽偶有大家为之一振,终未能再成兴盛之势。虽采用先前形式,模拟既往声调,亦不能代兴,徒增余响之悲凉。以内容论,诗歌之抒离情、言不遇、叹时节、写情志,自诗骚以下,为常作常新之主题;小说、戏曲之记爱情、说英雄、述公案、传鬼神,亦为恒常题材,甚或能归纳出若干某些叙事模式与人物类型,虽细节不同,内容尚似。故曰:为一代之文学者,非以形式论,非以内容论,乃时代契合文体,文体契合时代也。以时代言之,盖某种体式适合特定时代之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为时人时代精神之所慕、审美情趣之所尚,乃成其时创作之高潮,群风扇扬,切磋有时,遂为一代文学之极致;以文体言之,则一种文体有其独特表现领域、内在审美规范和特定的艺术趣味,只有时人之艺术视角适应之、文化情趣契合之、创作感受沟通之,此种文体的客观艺术规律与时人的主观创作风格暗相默契,方成一代之文学。此所言时人,非言大家、非言局部,乃长期创作之积累、大量作者之蜂涌,为一代之风气也。
汉赋乃有汉一代之文学,概而论之,亦为汉代文化氛围之产物:其综述百家的学术风气影响了汉赋作者思维模式,汇源成流的文学融合丰富了汉赋的表达技巧,义尚光大的社会风尚左右了汉赋的结构风格,灵活开放的用人制度激发了赋家的创作激情。又为汉代人文精神之凝结:其恢弘的王朝气度拓宽了汉赋的题材容量,外向的民族视野开阔了汉赋的艺术张力,宽容的艺术襟怀延伸了汉赋的作品架构,豪壮的社会心理影响了汉赋的整体风貌。亦为汉代审美情趣之缩影,实用功利的美学目的、巨丽宏赡的美学风格、宏阔博大的美学理念、深沉浑厚的美学内涵既为汉代美学之浓缩,也是汉赋审美之特质。有此文化氛围、有此人文精神、有此审美风格,才有此独立千年之汉赋。虽后代赋作绵延,以之为式者众,虽肖其形貌、类其内容,然不能代雄。盖此时之创作,非彼时之创作也,时世变迁,人文更迭,世风难移,情趣已非,再无汉赋兴盛之土壤,若再勉强为赋,则为魏晋赋、则为唐宋赋、则为明清赋,非两汉之赋也。
汉赋既为一代之文学,自两汉以后,论述颇多,[1]常以点评、序论、诗话之形式出现,虽多精见,却不成系统。自二十世纪以来,汉赋始入现代研究,学者于汉赋之发端、之形成、之演变、之特征,皆多角度阐述,新见迭出,透辟深入,附录所列汉赋研究典籍,不胜枚举。此外,于司马、扬、班、张诸大家之研究,于其余赋家之探讨,亦多有拓展,二十世纪乃汉赋研究之新开局。此研究者多有论及,毋庸赘述。[2]然20世纪汉赋之研究,多集中在汉赋之文学特征,于汉赋之史料价值,注意不够,能用汉赋史料审视汉代制度、发微汉代未明之史实,论者不多。
一代之文学,必存一代之史料。《诗经》之写周秦社会、屈骚之记楚物楚声、晋诗之论玄学、《世说》以为史料、杜甫以为诗史、元白诗歌笺证、杂剧以影元史、小说反映明清时世,此类论著如山,皆以文学与史料之对比研究。然于汉赋之史料价值,皆未能比肩也,一在于赋法为体,本为敷陈,本为直言,诗经三用,赋法七百二,[3]多用于叙事铺陈,其文学色彩,远逊于比兴之想象夸张也。汉赋敷陈,则务求广博,务为征引,有言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4]且两汉赋家,多为饱学之士,司马相如、扬雄皆编纂字典辞书,班固亦为史学家,张衡则为科学家,故汉赋之内容,远较其前之诗骚、其时之乐府为广也,举凡两汉山川形势、物产交通、宫室建筑、礼仪秩序、舆服制度等,皆搜罗殆尽,以为铺陈之极致,令后世无以加也。故汉赋中资料,善加利用,必可资汉史之研究。二在于汉赋为文,本属官方之文学,[5]汉大赋创作,未闻者献于帝王,以博取功名,为宦者传阅于朝廷,以陈说见解。查其序言,或以讽谏、或为美颂、或为论事,多追求汉赋之实用性,若其“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则废而不作。[6]故汉赋铺陈汉代制度之细腻,皆非凭空拟造,虽有增益,不可不察也,不可不用也。
以汉赋为材料研究两汉史实,尚须明者如下:
一曰汉赋为文学作品。中国文史,自古混成,道本一元,千载而下,渐趋扬镳,至今而成泾渭。两汉之时,文学尚未自觉,文史哲尚未完全分化,其时所谓之文学者,乃文章之学,非后世之“文学”矣。且秦汉文章,若《谏逐客书》、《过秦论》、《论贡举疏》者皆注重藻饰,措辞雅丽;两汉典籍,若《淮南》、《汉书》、《论衡》者,亦铺排详赡,言语整饬,此两汉之文风,皆未以之行文之华美,废其实用也。又,查两汉大赋,其作者序言,多言其用意如何如何;汉史所记,亦云汉赋美刺之事,盖汉人作赋,亦求功用。若汉赋作者,秉持诗教,成文意在谏阻、美颂、议论,立意通于奏折,行文尚于藻饰。汉赋为体,或用于彰显学问,铺排以证其博,故引物叙事,不致太过虚妄,若司马相如写上林、扬雄写蜀都;或用于谏阻帝王,畅言以论得失,虽夸饰其气势,然于时间、地点、程序、性质之界定,亦为谨慎,以免诬而不实,以披诽谤之过,若扬雄之劝校猎、杜笃之争西迁;或用于议论国事,以明辨是非,争论得失,此用语引物更为细密,先弃不实之说,方可行文。故汉赋非“典型之文学”,乃汉代文章与文学之过渡者。既然汉赋作者视汉赋之实用,既然两汉文风皆讲求华美,既然彼时文学尚未自觉,何必拘泥于“文学”一词,而忽视汉赋所言之史实。况文学之存史料者,已多论者发微,若细加甄别,乃增史学研究之新领域也。
二曰汉赋之虚构。赋之虚构,一在结构,二在引物。结构者,当为假设议论,虚构故事,此行文之笔法,论辩之技巧,乃先秦典籍之旧式。汉赋引物繁复,奇异之事屡见,此刘勰与后代论者之所诟也。汉赋所引事物,约分四类,一为素见者,二为异名者,三为祥瑞者,四为冥想者。素见者无异议;异名者后世不察,易引为怪,且司马相如、扬雄曾编纂字书,此非作者之虚构,乃语意变迁之故。此二类,若详审而考辨,则可明解。祥瑞灾异之事,为汉人所信奉,信其实有者;且汉赋引物广博,非事事尽可验证,此类言语,两汉典籍屡现。冥想者多为汉赋作者之虚构,若游仙、祀神之类,此类虚构,汉赋造其极。然此种构思,前有《离骚》、《九歌》,时有《郊祀曲》,游仙幻化之事,乃两汉间人之固有观念,今人释而为非,时人信而为真,此类引物,非作者之虚构,乃今人知其虚妄也。此二类,历来不足为训,亦未为信事以佐证,若明其事理,何必纠缠?故用为史料,则取前者,参以后者,则不置颠倒是非,若此,汉赋之虚构,则可辨若牛马,明其虚实。
三曰汉赋之夸张。夸饰乃自古行文之法,《文心雕龙·夸饰》云:“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汉赋之夸张,或有“饰穷其要”、“夸过其理”之处,然其夸张在形容不在肢干,在枝叶不在根本,虽“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然所本所言,当宗其本事。若仅虚妄之言劝谏,则近于诽谤,《上林》、《长杨》之不存也;若多用不实之辞美颂,近于阿谀,《广成》、《校猎》之无益也;若凭空假设,恐难以成论,《两都》、《二京》何以争辉?故刘勰云:“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七八者也,“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二三者也。[7]若引以为史料,必取其质其本、其七八者。
四曰汉赋之粉饰。大赋成文,本为粉饰太平,颂扬皇威,或以为其多逢迎之辞,不足为训。查两汉赋作,立意不外“美”、“刺”二端,此自古文学与政治之关联也,历代未能超脱,从来研究文史,皆须审查其言辞之扬抑。汉赋作者,以赋为“古诗之流”,言其“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8]故成赋秉以诗教,非尽为阿谀之辞。所谓粉饰者,扬其善而隐其恶,彰其得而遗其失,多用于政治、精神与行政,其于都城之规模、校猎之程序、礼仪之秩序、乘舆之规定,未宜过分粉饰。故以汉赋所记,论其难以粉饰之史实,若立论秉中,可避此失矣。
汉赋证史,此四者,不能不辨,不能不察,汉赋史料未遑利用,须先存警戒之心,未可稍有疏忽,为汉赋文学之法、虚构之说、夸张之处、粉饰之辞所误导。此考察汉赋所见史实必先审明者。
探讨汉赋中之汉代史实,不可不慎于研究方法也。章学诚尝谓“五经皆史”,今可曰:一切传世之材料皆史料也。传世之材料,或以典籍、或以甲骨、或以木石、或以钟铭、或以器皿,典籍之流传,愈传愈少,文学不辨者,采史料以为注解,若六臣之注《文选》;史料不明者,或采诗文以为补充,若陈寅恪之“以诗证史”,[9]两相发微,则为文史互证。[10]以甲骨所记材料考证文史者,王国维成就最著,乃谓“二重证据法”。 [11]衍而广之,今之出土简、帛、木牍、墓志、钟铭,其所载文字皆可以补充以往典籍记载之不足,以为研究之参考者。推而广之,考古所见之遗址、墓葬,出土之器皿、图画,虽无文字,却多摹乃时之形制、风俗,亦可窥习以往之故事,对应文字记载,则能发明部分未详之事实,此所谓“三重证据法”者。[12]
以汉赋为材料,一要还原,汉赋有虚构之处、夸饰之法,以其为材料者,当知人论世,辨作者行文之藻饰,以察其虚实;勘志传杂史之记载,以证其详略;校简帛金石之发现,以求其真伪,剖其虚构,去其夸饰,以还原所记材料之原始形态。二要审察,凡用汉赋材料,先以赋作铺排,数见者则采用;再与史料记载相对应,两合者则引用;三要验证于考古资料,相应者则确定;四比较于前后史实,以考订其性质与变迁。如此程序,以甄别汉赋之材料,验之再三,方敢引用。
以诗证史,或曰文史互证,陈寅恪先生笺证元白诗,已为应用。今以赋证史,或言赋史互证,仿佛其原理,以为拓展。以考古资料考订史实,晋之荀勖、杜预,北朝颜之推、宋之黄伯思,明之方以智,清之顾炎武、王夫之、庄祖述、刘心源、孙诒让、王筠皆有创见,阮元以汉唐石碑校订群经,取舍讹误,至王国维而大成,其出入文史,而成规模。再验之以出土之器皿、建筑,以为三重证据。今以考古所见证汉赋、比照史实,乃延续其方法,既以研究汉赋,又以汉赋考察汉代史实,两相发微,可审明两汉史实,可阐释汉赋文本。
故本文所论,取用汉赋之记载,考以传世之史料,证以考古之发现,佐以谨慎之推断,借鉴其他学科之理论。此本书所采用之方法,于文学研究,其以历史、考古、文化诸学科之材料解读文本,以解以往未明之史实,更正部分偏颇之评论;于历史材料的收集、考古材料的印证、历史史实的研究,以汉赋作为材料,考察汉代史实,补充部分史料,皆有裨益。或可语为研究方法之延展。
[1] 参见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2]总结20世纪汉赋研究的论著包括:张燕瑾、吕薇芬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之一《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之《赋学研究》284-318页,何新文《现当代赋学研究与文献整理》(《辞赋散论》,232-273页),阮忠《20世纪汉赋研究评述》(《学术研究》2000年第四期),《20世纪汉赋研究专著综述》(《南都学刊》,2000年第3期)等。
[3]谢榛《四溟诗话》卷2:“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四部丛刊本。
[4]《北齐书》卷37《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92页。
[5]参见胡学常《汉赋与汉代政治》,焦、王所言之一代文学,非指骚体,骚体多为模拟屈骚,两汉未能出其右,其侧重于大赋也,本文所论,以此立意。
[6]语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诠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事见《汉书》卷97《扬雄传》。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夸饰》,第609页。
[8]《两都赋序》,《文选》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9]诗史互证之方法,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已成其例,其原则,一是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诗证史,必须辨别“古典”和“今典”;三是诗文证史不仅以诗文为史料,而且诗史互证,方能融会贯通。
[10]景蜀慧:《“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见《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3页。
[11]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2页。
[12]李学勤、裘锡圭:《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潘树广《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8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版。此外,或有他说,“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见王煦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本文用前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