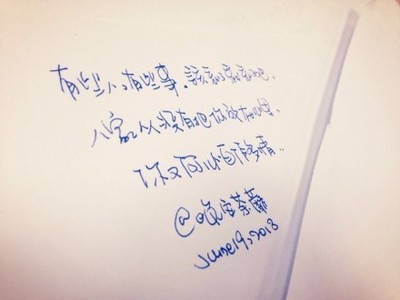导演魏德圣拍《赛德克‧巴莱》谈的是一场从一开始就知道会失败的革命,这让我想起作家龙应台说,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为了向失败者致敬」。失败者没有被扫进历史的角落里,没有被创作者遗忘,是因为这两部作品表面看到的是「失败」,核心里的议题其实是「共生」。因为历史的行进有时是这么的曲折,我们不能不保持一颗谦卑与宽容的心,试着可以一起在尚未终结的历史里声息相通,以至于埋锅造饭,让历史继续书写下去。
赛德克‧巴莱与大江大海 联合报╱彭蕙仙 2011.10.01
《赛德克‧巴莱》是求死,《大江大海》是余生。
两者都是人类面对命运时的一种「极限运动」,
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共同为人类丈量出了生命的尺度,
也就是「尊严」与「屈辱」互为表里的矛盾定义,
以及「分化」与「包容」彼此成就的复杂过程。
为了尊严而死与因为没死而拾回尊严的故事,
《赛德克‧巴莱》与《大江大海》里,比比皆是,
然而,哪个做法才是对的?
![[转载]承认吧,比起莫那鲁道.铁木瓦力斯.小岛源治.鎌 莫那鲁道遗骸照片](http://img.aihuau.com/images/02111102/02024634t014fae3f54c437d003.jpg)
为什么有人的「留得青山在」是忍辱负重,有人却是苟且偷生;
为什么有人的负隅顽抗是勇敢,有人却是困兽之斗的悲哀。
情境伦理真是言人人殊;
你的英雄可能是他的屠夫,你的胜利其实正是他的失败。
作家李敖对《大江大海》十分不满,
他认为蒋介石集团是败逃台湾,哪来的什么大江大海?
不过是残山剩水,是个笑话。
然而,在这所谓的残山剩水式笑话里,
岂不的确有「日久他乡是故乡」、好好过日子的真心?
有人对莫那‧鲁道不以为然,甚至感到愤怒。
如果日本人野蛮,妇孺皆砍的莫那‧鲁道何独不然?
然而,或许正因为莫那‧鲁道的转变,
我们才的确感受到了殖民与掠夺的强烈不仁。
历史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呢?
雾社事件八十年了,
这是《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必须在此时此刻被完成、被观看的重要理由之一吧。
或许却有人可以说:几百颗人头落地、千条人命消失,
两百多个遗族的困苦流离,到底改变了什么呢?
历史会继续告诉我们后来的故事:
八年后,泰雅少女莎韵‧哈勇被当成是高砂族的爱国(日本国,当然)样板,
〈莎韵之钟〉当年用来号召台湾人效忠皇军;
当战火渐渐远离,它会愈来愈流行,成为思慕情人的〈月光小夜曲〉。
你我的青春岁月里,都有过这首歌。
因为历史的行进有时是这么的曲折,我们不能不保持一颗谦卑与宽容的心,
试着可以一起在尚未终结的历史里声息相通,
以至于埋锅造饭,让历史继续书写下去。
所以,就承认了吧,如果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的当下与瞬间,
就不要用二十一世纪的脑袋去揣测那每一颗被出草的脑袋,
到底是否甘心情愿?就承认了吧,如果《大江大海》里有邪恶愚昧,
我们只能在彼此的眼泪里温柔地互相卸下这份不幸的遗传;
就承认了吧,不论「赛德克‧巴莱」算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
彩虹桥与太阳旗终究会在同样的一片天空里相遇,而这天空向来是不偏待人的。
但也同时就承认了吧,比起莫那‧鲁道、比起铁木‧瓦力斯,比起小岛源治、比起鎌田弥彦……
如今的我们对这些不见得明白得更多。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换取的孩子》这本小说里写着:
「在国外机场看到贴有fragile(易碎)的行李时,就想把那标签贴到自己的背上。」
啊,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