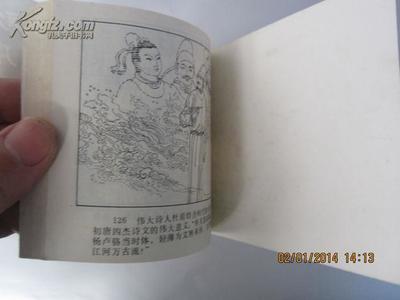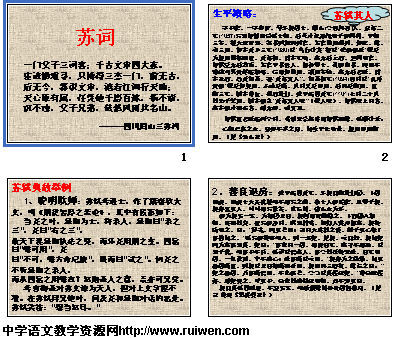“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以文章名天下”的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他们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唐诗的开创时期,却都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廷诗的狭小范围,将的题材由宫廷移到市井,由台阁移江山与塞漠,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诸如羁旅行役,言怀赠别,边塞关山,山川景物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昂扬进取与抑郁不平的情感,并在诗歌的体式与格律形式上有所探索,从而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杰”的称号在当时即已出现,但其排列顺序却有不见的说法,或云王杨卢骆,或云卢骆王杨。《旧唐书》卷一九0《杨炯传》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以为然。”可见这种排列有表示评价高低之意,而张说《裴公神道碑》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郗云卿的《骆丞集序》云:“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后来明人王世贞在《全唐诗说》中亦云:“卢骆王杨”。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排列顺序,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中认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象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他认为“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大了十岁的光景。”“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不论是王杨卢骆,还是卢骆王杨,闻氏提示出四人为两组,对认识四杰还是颇有意义的。所以他说:“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意思。”除此外,他认为在创作上,卢骆擅长的是歌行,王杨专工五律。
“四杰”的齐名,除了文章的原因外,似还有个性的原因。他们的个性都很张扬,行为都比较浪漫,遭遇也都比较悲惨。因为个性张扬,行为浪漫,因而备受时人的诋毁与唾骂,也因遭遇的悲惨,也受到了后人的同情。当时人称他们为“浮躁浅露”,不能致远。《旧唐书》卷一九0《王勃传》载云:“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馀得令终为幸。”裴言不幸而言中。关于这一点,从四人的生平遭际可以看出。
1、卢照邻(637?-689?),字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最初他作过邓王李元裕府典签,后迁益州新都尉,因患风疾去职,隐居太白山。后服丹药中毒,病势加重,足孪,一手又废。移居阳翟具茨山(今河南禹县)下,预为墓偃卧其中。后因不堪病痛,乃自沉颖水而死,有《幽忧子集》七卷,今人徐明霞点校本将他和杨炯合为一册,中华书局出版。
2、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宾王天姿聪颖,七岁能诗,其父曾任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境)令,少年曾随父至博昌,不久父死任上,他在穷极无聊中渡过其早年生活。约在高宗龙朔元年,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朝廷诏令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陈述己能,他却耻于干进(《自叙状》),不久即离开了元庆幕。后又曾任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因事被谪,从军西域,在塞外游历两三年后返回,又在蜀中游宦多年。仪凤三年(678)迁侍御史,又被诬坐赃下狱。出狱后于调露二年(680)除临海丞,后弃官居扬州,光宅元年(684),徐敬业在扬州暴动,辟骆为艺文令,写下了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不久徐兵败,骆下落不明,或云于乱军,或云出家为僧。(《唐诗纪事》载:“宋之问贬黜放逐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曰:‘鹫岭郁岧嶤,龙宫锁寂寥。’”久不能续。有老僧照明灯曰:“少年夜久不寐,何也?”之问对曰:“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即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寺僧有知者曰:“此乃骆宾王也。”)
3、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人。王绩之侄孙,王通之之孙。其生卒年说法不同。杨炯《王子安集序》云其:“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致其乐,颜氏斯殂。”据此知其享年二十八岁,当生于公元649年,卒于676年。《旧唐书》本传去其卒于上元二年(则卒时二十七岁),《新唐书》云其卒于二十九岁,恐皆误,因为杨炯与王勃同时,其记必有据也。他十四岁即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召署为修撰,因作《檄英王鸡文》,高宗以为挑拨诸王交构,即日斥之,不令入府。因漫游蜀中,一度任虢州参军。后官奴曹达犯死罪,勃匿之,又惧事泄,遂杀之,犯死罪,遇赦革职。父王福畤亦因坐迁交趾令,勃往探视,渡水溺死。王勃才华横溢,《唐才子传》云:“属文奇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选磨墨数升,则酣饮被覆而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清人蒋清翊为之作注。

4、杨炯(650-693以后),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十岁应神童举及第,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又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三十三岁任太子李显府中的参事司直,又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后因其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叛乱事牵连,迁梓州参军。又任盈川县(今浙江衢县)县令。死于任上。有《杨盈川集》,原三十卷,今有十卷,有诗30余首,全为五言。
从上可以看出,四杰的生平遭际与个性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的一生大都地位不高且遭遇坎坷。他们早期都有京城生活的经历,但又都因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京城而到处流离漂泊,这种生活经经历,对他们的创伤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如卢照邻投水自尽,骆宾王下落不明,王勃溺水而死,只有杨炯得以善终,但总体上却都享年不永。
第二,他们都是有才华而恃才傲物的人,个性都比较强,也即所谓“浮躁浅露”。杨炯在“四杰”中算是比较沉静的,但也恃才凭傲,《唐才子传》载云:“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尔!’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王勃也有恃才傲物的记录。《唐摭言》载云:“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都,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珍,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婺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不过闻一多先生认为: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他说:“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因为‘王勃在短短的二十八岁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一大堆的著述’”,计有《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而卢、骆则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他认为骆宾王“是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义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所谓“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杀人报仇,革命”的事,指的是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当时骆宾王正是由于仕途坎坷而满腹不平之时,因此徐敬业征诏他为艺文令,便一拍即合。文中对武则天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说她:“入门见疾,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武后读之,但嘻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武后变色曰:“宰相何得失此人。”而所谓“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则是指他在蜀的两桩公案,他有两诗写此事,一是《代女道士王灵妃答道士李荣》,一是《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总之四杰确是有个性的诗人,也正因此,遭到了时人的诃责与唾骂。
关于四杰的创伤上的特点及其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具有变更文坛绮艳诗风的自觉意识,并且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他们变革意识,从杨炯的《王勃集序》可以看出,其中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风,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里所说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主要指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之说,因此,他们变革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上官体”。我们知道“上官体”是当时宫廷诗风的典型代表,四杰反对“上官体”是具有重要诗风改革的意义的。
第二,在创作上,他们的诗歌的视野与题材大大开拓了。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与塞漠。我们知道,初唐前五十年的宫廷诗人,其诗歌创作的范围,不离于宫廷的宴饮、酬唱、奉和与应诏,视野比较狭小,而到了四杰,他们的创作则展现了一个宫廷诗人所不了解的更为宽阔的世界,他们写羁旅苦辛,道路险阻,写边塞立功,功名追求,人生哲理等等,把诗歌的题材领域拓展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古意”本是宫体诗惯用的题目,但他却把宫体诗原写宫廷转到市井生活。诗中既写了长安的繁盛,还有王公贵族的车马、宫阙、第宅的壮丽、权贵的竟逐豪奢,既有王孙公子,军官侠客的纵情声色,市井娼家对爱情的充满热烈而又颠狂的追求,还有统治阶级的互相倾轧,这样的内容已不是宫体诗、宫廷诗所能容纳了。而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中所写的“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等,则写到了前所未曾见过的边关生活,有了与宫廷、台阁诗人所未曾有过的感受。此外象王勃的《秋日别薛昇》,《山中》,《滕王阁诗》等,或写送别,或写羁旅,或写人生思考,都表现出了他们在诗歌题材上的新开拓,“他们终于把生活视野,把诗情,逐渐地引离了宫廷的小天地,门窗已经打开,广阔地天地就在面前了”(罗宗强语)。
第三,在诗歌的感情基调上,他们的诗歌变得更加充实,他们或在诗歌中渲泄他们抑郁不平的牢骚,或写他们追求功名的热望,都具有一种昂扬、壮大、浓烈的情感!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谈到卢、骆对宫体诗的改造即说他们的诗“背面有着厚积的力量支撑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卢、骆的到来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这里的气势、感情,正是齐梁文学所没有的,也是唐初的宫廷诗所没的。不仅卢、骆如此,王、杨也是如此,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其不论是写送别还是写对建功立业的向往,无不以充沛的感情,壮伟的气势充塞其间。这种强烈、昂扬、壮大的情感正是唐诗个性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而这些在四杰诗中的出现,也正是四杰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之一。而他们在歌行与五律两种体式的探索,也为唐诗后来在体制上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