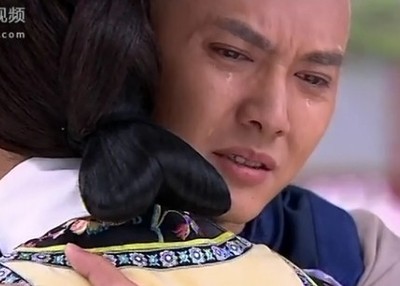《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此章论述修身与正心的关系。对于“身有所忿懥”一句,程子认为“身有之身当作心”,应该是心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当心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时,心就不得其正。然而程子又说“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非是要无此数者,只是不以此动其心”。既然一个人可以有“忿懥、恐惧”,并且心还能保持如如不动,说明不是心在“忿懥、恐惧”,而是身“忿懥、恐惧”,“忿懥、恐惧”是情绪,属于身或气的范畴。同样,这里的“身有所忿懥”,也应该是“身”而不是“心”,“则不得其正”才是“心”不得其正。
《大学》作者区分了“身”“心”“意”“物”,尤其是区分了“心”与“意”以及“身”与“心”,那么“心”就只能是“能”,而不能是“所”;只是“未发”,而不能是“已发”。“意”是心之所发,与外物发生作用,而“心”是意识的主宰;“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身”是“心”之充塞,涉及与外物的关系,而“心”则是内在的主宰,是独立不倚的。既然《大学》是析而言之,那么这个“心”就只能作主语,而不能被“对象化”,被“对象化”、涉及与外物关系的则被分别称之为“意”和“身”。例如,“忿懥、恐惧”等情绪是受外界的牵引而产生的,是“已发”,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应是“身”忿懥、恐惧,而不是“心”忿懥、恐惧。如果是“心”有所忿懥、恐惧,心就被外物支配而作宾语了。
但“心”又不是绝对独立的孤悬一物,“离外物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哉”。在《大学》中,“心”不与外物直接作用,因为一直接作用,心就被对象化而不是独立自主了,外界是通过“身”和“意”进而影响到心,使“心”外放、外驰。例如“身有所忿懥”,心“则不得其正”。但《大学》所谓“正心”,“心”不是作“正”的宾语,而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作宾语的是“其所不正”,其实即是“忿懥、恐惧”等已发之情。假如“正心”即是“正”其心,那么就有一个“能正”之心和“所正”之心,而“能正”比“所正”更应是“心”。
黑格尔对中世纪许多神学家处心积虑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一命题嗤之以鼻。因为上帝是绝对圆满无缺的、自在自为的,而“存在”是直接的为他的存在,是第三人称的,是最贫乏、最低级的一个范畴。说上帝“存在”简直是对上帝的贬低,当然说上帝不存在更是大谬。“桌子上有一个茶杯”,茶杯“存在”着,茶杯在桌子上,在房间里,被人使用着,所谓“存在”即是与他物发生着关系,所以“存在”即是相对他物的存在。而“心”是独立自主的自我性的存在,不能被对象化,所以不能说“心”存在着,也不能说“心”不存在,总之,“心”不能做“存在”或“不存在”的主语。所以,《大学》中的“心不在焉”不是“心”不在,其涵义是“心”没有被“身”所牵引而失其正。“心不在焉”即是精神内守、“求其放心”从而使心归于正。
此章前半部分的“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是阐述“身”对“心”的反作用;“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是正面阐述“心正而后身修”。视觉、听觉、味觉等是“小体”,“视而见,听而闻,食而知其味”是“物交物,则引之而已也”,是《礼记》所谓“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是息“闻见之知”而存“德性之知”,是“身修”的表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是相对前文的“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而言的,虽然“见”“闻”“知其味”与“忿懥、恐惧”等情绪有所不同,但都是被外物所引诱和驱使。这样解释“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与“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一句语意相贯通。如果按照通常的那种解释,那么本章的最后一句总结应该像“齐家”一章那样采用逆否命题的形式:此所谓心不正不可以修其身。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