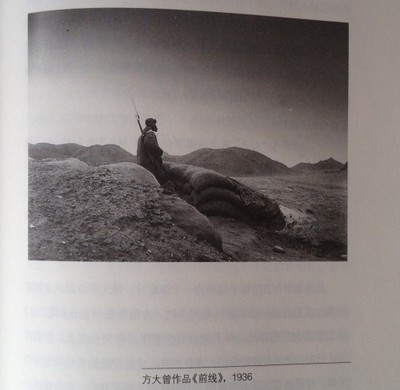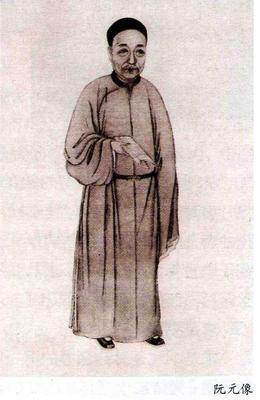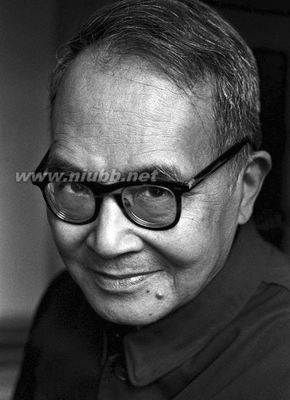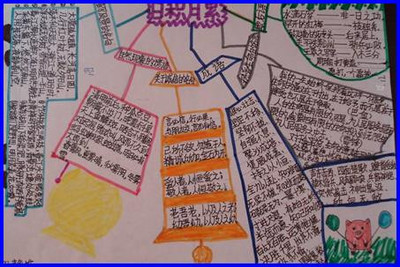《挟书律》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藏书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在中国法律史上对《挟书律》的研究,只是从法律的角度,介绍和研究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种类。至于此律产生的渊源和对历史文化、藏书文化的影响,则较少论及。即使现今出版的几部藏书的大著,如《中国藏书楼》、《中国藏书通史》等,也没有对此做更深的阐述和研究。我们认为,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中,秦代颁布的《挟书律》是有着阻碍中国典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事件,而在西汉初期及时地解除了《挟书律》,又对中国的藏书文化起着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作用,所以,对《挟书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挟书律》的起源和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开创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但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禁书史的开端。中国禁书的历史,就是发端于两千年前的商鞅。他作为秦孝公的谋士,他的治国核心思想就是以重农、重战来维护秦国的安定和发展,继而提出了典籍对于安邦治国“独无益于治”谬论: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亡国不远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1]
商鞅不仅仅提出和实施了“燔《诗》、《书》”的焚书创举,同时,也是提出并实施禁书的第一人。他携李悝的《法经》到秦国效力,协助秦孝公实行变法,由他开始,将“法”改为“律”,“律”之名由此始。我们从出土的秦简中,已经探明的有《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等等,可见“律”已成为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
在秦尚未统一六国之前,秦始皇就有了制定文化政策的思想,看到韩非抨击儒家﹑宣扬专制﹑提倡重刑的《孤愤》﹑《五蠹》等著作时﹐就对韩非刮目相看。格外欣赏:“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统一六国之后,基于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等需求的原因,即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文化发展的政策,推行了反对仁义说教,主张严刑重罚的政策。逐步将这一思想变为实际行动,对《秦律》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成为治国的根本大法。为了迎合秦始皇治国的需要,李斯建议进行一系列统一法度等立法活动。先是更改国君名号为皇帝,宣布其“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朕为始皇帝。”将其绝对权威和最高效力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再就是把原秦国的法律、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制度,强制推行于其他六国地区,使其在大秦国境内得以统一并普遍适用。
《秦律》的相关文献和原文早已散佚,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只能从只鳞片爪的文献中,管窥到部分律文的核心内容。1975年在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挖掘出土的秦墓中,墓主经考证是秦代的一名法律工作者。在他长方形棺材里拥有大批的竹简。棺材打开后,墓主的头枕着竹简,头边放着竹简,手里还拿着一捆竹简,脚下也是竹简。经清理,共有1100余枚,主要是与秦律相关的文字内容,主要包括秦国的律令、法律问答等法律文书,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唯一能够了解秦代的法律的第一手的材料。
秦除了制定六篇刑律之外,还颁行了大量单行的法律与其他形式的法律文件:目前见于秦简的法律近30种,主要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赍律、徭律、司空律、置吏律、军爵律、传食律、内史杂律、尉杂律、除吏律、游土律、除弟子律、中劳律、工人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博律、敫表律、捕盗律、戍律等;除此以外,关于文化建设方面还有一项重要的法律文件就是《挟书律》。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全盘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诏禁止儒生以古非今的言论和著述,明确规定了秦国的文化政策。为了预防全国各地执行的力度不一,专门起草出台了关于藏书的法律——《挟书律》。本律的主要内容有:
一、史官只准收藏秦国(含六国)史籍,其余一律焚毁;
二、民间所藏《诗》、《书》与百家著述者,须上缴官府销毁;
三、私人不得藏法家以外任何学派的书籍凡藏有法家以外的任何学派的著作,处以腰斩、族诛。医学、占卜、种树、农桑之书除外。
四、焚书令下达后在三十天内不焚烧、销毁者,罚作苦役;
五、敢谈论《诗》、《书》者,弃市;
六、议论时政者,族诛;
七、官吏有知情不举者,与犯者同罪;
八、私藏违禁书籍者,黥为城旦;
九、投递匿名信者,依法拘捕,审讯定罪;
十、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以上内容从目前所能发掘到的史料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可能就是《挟书律》的主要内容。当局把藏书作为妨害社会秩序的法律之一来颁布的,《挟书律》规定了全国百姓士子藏书和读书的范围,私人不得藏法家以外任何学派的书籍(医学、占卜、种树之书除外),否则将受到腰斩、族诛的重罚。颜师古注释说,凡是“挟书者族”。且处罚量刑甚重,动辄就是处以“族诛”、“黥为城旦”、“弃市”、“腰斩”的极刑。何谓“族”?在秦代的法律中,就是给予抄家甚至是把罪犯的家族成员全部处死的处罚;何谓“黥为城旦”:黥,是以刀刻凿于人的面部,再用墨涂在刀伤创口上,使其永不褪色。城旦:将男子发配至修城墙之刑,它是秦朝的劳役刑之一,城旦是指强制男性犯人去修筑城墙或者长城的苦役。何谓“弃市”?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将犯人执行死刑并暴尸街头的一种刑法。秦代执行的这些酷刑,对藏书者来说,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关于《挟书律》原作的具体条文,今天还无从考索,或许在未来的考古发现中,能发掘出土到记载《挟书律》具体条文的竹简或者帛书等文献。甚至可以猜测在秦陵中,能出土秦朝时期的文书、档案,或许通过这些文书档案解开历史、文化上的一些重大之谜。最为关键的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下令“焚书坑儒”后,不少文化典籍都被烧毁。陵墓内如存有一定的文化典籍的话,上面可能记载有完整的秦国历史。
现今我们只能根据李斯上奏的焚书令,其所奏内容,只有两大类图书是被容许保留的:一是博士官所职掌的各类图书,作为官书收藏,官书本在官府,不在民间;二是医药、卜筮、种树农桑之类的实用技能之书,为科技类书,阅览和使用的范围仅限于秦国的专业人员。法律规定了除了官府的有关部门(国家图书馆)可以藏书外,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收藏法家以外的书籍。从此,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罢黜异说、厉行法治的专制集权统一制度在全秦建立了,实现其“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的国家管理制度。司马迁曾评论说:“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秦朝律法的繁密,不仅仅是控制百姓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方面,甚至在日常生活起居、使用何种农具、如何对待牛羊、对待山野动物等方面,都有详细的律法来约束。所以汉代学者恒宽亦称其“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
二、《挟书律》与秦始皇焚书事件
《挟书律》的出台与秦始皇焚书是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的。从历史大背景来看,秦始皇一开始并不是对书籍有着天然的厌恶之心的,而是在李斯等法家上奏的所谓“国策”之后,秦始皇才开始大肆灭文焚典的: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尝恶书,观其读李斯《逐客书》,则亟毁初禁,开关以纳之;读韩非《说难》,则抚髀愿识其人,其勤于下士、溺于好文如是!其后焚书之令,以淳于越议封建;坑儒之令,因卢生辈窃议时事而下,要皆有所激而然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面临的社会问题繁多,当务之急的是各国的文字、法律、度量衡、服饰等标准五花八门,“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尤其是语言文字图书方面,汉字产生后若干年间,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急剧变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到了春秋战国末期,各地文字的形体和读音都有所不同,班固说秦书有八体六技:“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这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来讲,这么能容忍这种混乱的文化现象存在?这对于政令、国策的颁布及其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严重阻碍,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刚统一的这样一个大国,政令不通、文字多样、语言各异、货币、度量衡器不一混乱状况,严重地制约着秦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有统一的大秦国文字和国语,以便各界的文化交流和协调。为此,李斯首先看到这种经济与文化现象的落后与混乱的局面,十分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遂向秦始皇建议:颁挟书令、禁私学,有必要出台新法,那就是大秦既然一统天下,必须使天下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和秦国一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琅邪刻石》记其:“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统一是必要的,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也是严重的:
“七国之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髙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在这场“一统”的改革政策中,从文化上,对史籀大篆等文献没有任何的政策保护,而是一味地“烧灭经书,涤除旧典,”上古文献从此被彻底地湮灭而失传了。
从李斯的治国方略视角去看,其奏章(包括以后的焚书行为)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早在战国之时,商鞅携李悝的《法经》到秦国效力,协助秦孝公实行变法,由他开始,将“法”改为“律”,“律”之名由此始。我们从出土的秦简中,已经探明的有《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等等,可见“律”已成为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
由于秦国的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特殊原因,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文化发展的政策,首先,就是制定了《挟书律》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凡藏有法家以外的任何学派的著作,都会面临处以腰斩、族诛的酷刑。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实行文化专制,尊法抑儒,同时也杜绝六国的顽固分子利用书籍行复辟旧梦。
三、颁布《挟书律》的历史影响
图书一直被奉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明的载体,应该奉之神明才是,可是在秦代为什么遭到如此劫难?书籍与儒生遭受的凌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苛刻和严厉的。由此可见它的传播、教化功能的巨大。以至于在后世各代出现了各种的禁书、焚书的理由,从儒家经典著作到稗官野史、从学士文集到术士妖书,从“妖言惑众”到“伤风败俗”、从“浮语谤语”到“异端邪说”如此等等,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当某类书籍记载着执政者统治的黑暗与暴力,宣扬着的民主与进步,流露出的民怨与国殇,它们就难免遭受“燔”和“禁”的命运,著述者和藏书者也就难逃“弃市”之厄运。
从秦代的挟书律开始,导致了后世禁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频繁的禁书,对于执政者操纵国民意识形态的一家独尊,主流社会中的精英言论得以光大,而对不同声音的百家之言和思想,一律罢黜。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动辄就是杀头、坐牢、弃市、腰斩、诛族等酷刑,自秦禁《诗》、《书》以后,陆续出现了汉禁《老子》、《庄子》;北魏禁佛经;唐禁阴阳术数和《三皇经》;南宋禁野史;元禁伪道经;明代禁小说词曲;清代连民间自编词典也属违法,被满门抄斩。自秦至清,中国文化厄史事件一件比一件剧烈,烈度一朝比一朝严厉。
秦代的挟书律制度的出现,是文化专制政策的根本表现,也是法家提出并实施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等专制政策的具体体现。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韩非子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种专制现象直到北齐的颜之推才敢对此提出批评,他在《颜氏家训·书证》一文中指出:“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秦人“灭学”的政策,实际上远比焚书之举更为残酷和深远。
《挟书律》这个律法的颁布和实施,与后来的焚书事件相比,其意义和影响还要重大。首先它封杀了百姓读书识字的权利,即使你想要学习当时的文化思想,由于没有书籍可供学习,只能当作“黔首”。无疑是对百姓藏书事业的严重打击和蹂躏,同时给中国典籍的收藏、流通和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灾害。它使民间藏书成为“违法”,使百姓拥有知识变为“禁区”,相反,只有“愚民”才是合理。其次,它垄断了书籍收藏的范围和环境,民间和私人不能藏书,违者处死,这样的一个高压环境下,这种专制的文化政策,对文化的传播和书籍的流通成为不可能,包括制作书籍的工艺亦被限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和递进,这无疑是中国藏书文化史及其法律史上的一个最为莫名其妙的一个律法,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和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在秦代,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著述,进入了一个冰点时期,因此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在汉初成为稀有人才。
四、《挟书律》的废除与汉代藏书事业的发展
从秦始皇三十四年到汉惠帝四年(前213~前191),这项法律共存在了23年。由于秦朝的峻法和暴政,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仅仅十余年后即被农民战争推翻。刘邦建国后,由于百废待兴,无暇于律法制度等,基本上沿袭秦代的律法。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在平定逆臣英布的战争中受伤而死,刘邦的嫡长子刘盈继承了皇位,为汉惠帝。汉惠帝刘盈(前213~前188),西汉的第二位皇帝,惠帝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提拔贤人曹参为丞相,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很安定。但是惠帝年少不更事,加上吕后操纵,不久大权便落入太后吕雉的手中。在位后期处处受母亲吕雉的牵制,在位7年,以至最后抑郁而终,享年仅24岁。他在位七年里,所作的安邦治国的业绩,史书记载寥寥无几,主要是在吕雉的影响下,在文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在具体的国策中,将原来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酷的治国方略作了相当大的调整,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吕后执政的十六年中,陆续地对秦律加以修改,诸如实行减刑、颁赎罪法、废除三族罪、弛商贾之律、免去妨害吏民的法令等。
其中免去妨害吏民的法令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废除“挟书律”。意识到《挟书律》的实施,实在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不利于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国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于是在惠帝四年(前191),诏告全国,废除《挟书律》: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汉书·刘歆传》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一文中,对西汉初期的文化背景和藏书事业的发达,作了一个清晰的介绍:
“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冑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
《挟书律》的罢黜,无疑如一声春雷,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个文化信号:横蛮的文化专制政策已经成为过去,百姓终于可以自由收藏和阅读自己喜好的图书了。从此,百姓可以随意抄写、阅读、收藏、传播《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历史文化典籍和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自此以后,长期珍藏在民间的古书陆续开始在民间出现,为汉代的文化复兴,提供了前提条件,为后来的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挟书律》被罢黜以后,西汉的国家藏书楼和藏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萧何造天禄阁、石渠阁等,以存放他从秦收罗而来的档案、律法文书等;司马迁也无不称颂汉廷书府:一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刘歆在《七略》中称,除了天禄、石渠等藏书楼外,“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进入东汉之后,更是传承和延续了西汉的发展模式:东观、兰台即为国家的藏书之所,刘珍等著名学者校书于东观,修撰《汉记》;班固典校于兰台,著有《汉书》。所以唐代学者刘知几称:“斯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纪》,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为作,竞无它称。”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正式废止了自西周以后延续了约九百多年的官书垄断禁令,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众传播的明确观念。中国书籍从此进入了公众传播的新时代。”
“除挟书律”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它解除了自有文字图书以来,提倡官藏、限制私藏的图书流通体制,打破了数百年的官书垄断制度。章学诚在论及官府藏书与古代文化时剖析道: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这种政教合一的文化制度,一方面对图书的高度垄断,一旦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便逃脱不了被禁、被焚的厄运,一方面,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不可能起到积极的、主动的影响。尤其是民众思想的开化,百姓参与管理的意识,掌握和认识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在这种文化的高度垄断下,得不到滋润,得不到扶持,严重地阻挠了社会发展前进的步伐,延缓了人类文明的普及程度,这就是商周以至春秋以来的史官藏书文化的诟病。
引文出处: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