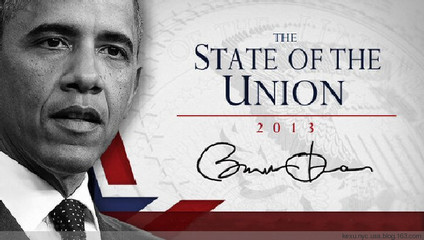纳兰性德《梦江南》
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纳兰性德
古代文人对江南的迷恋,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交通会阻塞思想的交际,在出行艰难的古代,一个北地的人,想到南边来,简直就是一件惊天彻地的人生大事。旅行宦游,不但要拿来说,而且要使劲掰开了说,说透说烂为止。有些文人虽然一再地抒发自己天涯羁客的孤独,心底却不免有得意和炫耀的意思。须知在古时某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自己所在的省,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小县城转悠,在前辈的诗文中寻觅遥远江南的影子。然而越是不可触及,“江南”二字越是频频出现在诗文中,连词牌曲名亦有以“江南”命名的。自古以来,江南便是中国文人的迷梦,沉淀着四季任何美丽的幻想。这种疯狂是让其他的地区眼红却望尘莫及的。
《梦江南》有很多别名。一个曲牌词牌因其时代迭进更替而出现众多的小名,是文化发展的需要,古典诗歌的惯例。比如《金缕曲》又叫《贺新郎》,《水调歌头》又叫《百字令》等等。我比较喜欢的《梦江南》的别名有:《忆江南》和《谢秋娘》。
如果追溯的话,写得较早而又声名在外的“梦江南”要算白居易的《忆江南》二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最早知道《梦江南》这种小令就是因为白乐天这两首写得声色俱佳,撩人得很的词。很多人中的杭州的毒也是被白乐天这老头下的,这种毒到现在好象还没什么解药,却不妨碍大家前赴后继。反正死不了人,不过是心里添了些惆怅幻想,好象西湖飘起了微雨。
词分小令,长调。小令短于长调,而《梦江南》又是小令中的短品,五句二十七个字,可见其炼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之为体 , 要眇宜修。缪钺先生在《论词》又将其深入浅显的概括为四个方面 , 即 “ 其文小 ”、“ 其质轻 ”、“其径狭”、“其境隐”。容若小令丰神迥绝,婉如清扬,正合这四个要旨,而这首《梦江南》在他的《梦江南》组词里最是出色代表。
这首词,抒写的是黄昏独立思人的幽怨之情。题材常见,容若所取的也是寻常一个小景。但此寻常小景经他描摹,便极精美幽微。尤以结句最妙,一语双关。“心字已成灰”既是实景又有深喻,既指香已燃尽,也指独立者心如死灰。很是耐人寻味。此词一般解作闺情词,是女子在冬日黄昏思念心上人,然而,解作容若思念意中人也未尝不可,他本就多情如斯。
关于心字香,有极优美繁复的做法,据范石湖《骖鸾录》记载:“番禹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开者著净器中,以沉香薄劈层层相间,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过香成。”所谓心字香,就是用香末萦篆成心字的香。
而关于心字香最美的描写,不是容若的“心字已成灰”。而是蒋捷的《虞美人》——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蒋捷生逢乱世,一生流离落魄,词意中切骨凄凉是经现实锻打后的沉重。容若的凄凉则近于轻盈,他究竟是个没吃过大苦的人。真落魄和假落泊之间,好象真品和赝品,是不能仔细比对的。
将两首词比并起来读,会感觉到容若的“心字已成灰”清稚,似年少者陷入情感时周身的缠绵疼痛,感情也真,但习惯小题大做。而蒋捷的“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抒发的是在尘世颠沛后的真切渴望,更近于人成熟后,心中对寻常温暖的思忆,一如生活本身沉着实际。
银笙声声衬着天涯游子的心香飘摇,归乡之念绵延却始终杳杳。某日醒来惊觉流光已把人抛闪。流光无情比起自觉心如死灰,更叫人心下惘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