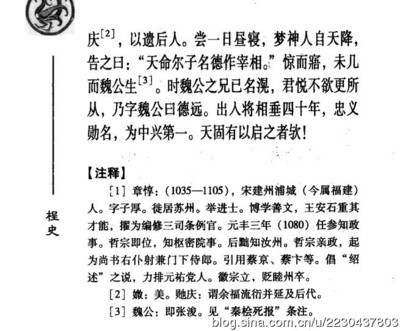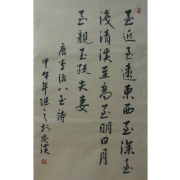迷龙、上官戒慈与龙文章
作者:译欣如一 《团长》中少有爱情戏,却有两个关于男女情感纠葛的三角关系,一个是孟烦了、小醉与张立宪,一个就是迷龙、上官戒慈与龙文章了。如果说第一个三角关系还展现出比较清楚的男女情爱关系,一种我爱的人与爱我的人之间的感情牵缠,后者则显得比较清水的止于暧昧(上官与龙),更多表现出一种吸引与伤害之间的生命意志的磨擦。
1、迷龙与上官戒慈:生与死/梦想对生活的吸引
“于是我们看见了我们所见过最美丽的棺材:它完全是原木的,在这树林中它像是就着这里的水土长出来的。…我们的鼻腔里没有死人的气息,只有树液的清甜。”
--------------------------------
在从缅甸回家的南天门上,迷龙初遇上官与雷宝儿,便即陷入了人生中最大的梦境。当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脚步向那对母子走去时,“迷龙的表情实在太过于认真,没有别的,只是认真和小心,那样过分的认真和小心、温和、悲伤、欢乐、伤逝、怀乡、心碎只该属于梦境”。他仿如梦游般的走过去,“梦见已经永远消逝的一切”,站在女人和孩子面前,用“贪婪而不是好色”的目光看着他们,想用一双眼睛同时把两个人都从眼里收进心里去。
这时的迷龙所看重的是上官母子所勾起的他在战火中化为飞灰的家园梦想,是他对曾经有过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生活的向往。他甚至还根本没看清上官的脸(因为她一直低着头),碰触她的头发也只是为了替她拿掉粘上的草叶,对去摸雷宝儿的头而被挠出的血痕也会很珍惜的用嘴去吮;他所渴望的其实是一种家庭式的亲密联系,一种相互关爱的亲密氛围。
迷龙向上官求婚,直率又虔诚的问出:“你能不能嫁给我?”虽然在孟烦了、不辣等人一旁的起哄下,他只是全心全神的贯注于这对勾起他家的梦想的母子身上,认真到对身边的一切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被迷龙的专注虔诚感染的上官也同样认真的给予了他回复,并提出自己的要求:“如果你能给我公公做一付三寸厚的棺柩,可以。”“如果你能带我们回中国,给我们一个家,我就嫁给你。”“如果我死了,你也能好好对雷宝儿,我就嫁给你。”
这些要求既轻易又艰难,轻易在它的合情合理、毫不刁难、更没有任何过分的物质索求,艰难则在它极为考验一个人的责任心与意志力,尤其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乱与饥匮的世道里、这种前途茫然而后有追兵的情形下。而迷龙回答得毫不犹豫:“就算你不死,我也会好好对雷宝儿。就算你不嫁给我,我也要带你们回中国。就算我死了,我也要让我屁股后面这帮混蛋玩意儿带你们回中国。”在迷龙看来,这些只是理所当然的守望相助,算不上什么条件,倒是做出一付三寸厚的棺材才算是份像样的聘礼。
于是,敲定了人生中第一件大事的迷龙,那种为了追逐梦想不惜豁出一切的败家散财的毛病又发作了。他用了半腕子表换了刀、斧、锯、铲、锹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家伙事儿”好用来伐木做棺材,又拆了自己装货的推车好取钉子钉棺材,而任一路搜罗的货物散了一地。他仿如树妖般快活而精力十足,仗着蛮力又借着巧劲伐树,指挥他手下的苦力们帮心忙加工木材,还犹能精益求精的挑剔。就着原木,以精细的计算、自然的审美,这个容粗犷细腻于一身的原始艺术家,硬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做出了一付仿如自然原生原长而出般的美丽棺材:完全是原木的、带着青得令人舒心的树枝、缠绕着藤蔓,“你简直觉得把它埋到土里后还会继续生长”。
这样一付充满了生机的棺材,完全消解了棺材本身所代表的死亡意味,因为制造棺材的人本身充满了生机、洋溢着因梦想而来的充沛的生命活力。正是这样一付“活”的棺材深深打动了上官,令她打消了因对颠沛流离与苦难生活的绝望而萌生的死志,“要对得住这样一份聘礼”而再次有了生命的热情,有了对生活的向往。
在怒江渡江时的哗乱,是迷龙与上官这对速配夫妻之间真正情感交融的时刻。如果说之前上官对迷龙的印象还止于对他的真诚与仗义的感激,受他生命活力所感染,在看到在怒江渡口迷龙是如何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努力护卫自己母子,如何奋勇前往东岸搭起救命的第三条渡索,如何在因西岸的枪声引得东岸守军警惕渡江无望后拼死命的游回西岸来与自己母子同患难…后,迷龙在上官眼中已在爱闹爱笑、坦荡率真的大孩子之外,建立起了一个有勇气有责任感的值得倚靠的男子汉形象。而这样一个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毫不掩示的展示出自己的情感,兼具热血与柔肠、放犷与眷恋的粗豪男人,与自小教养良好、知书识礼、恪守规矩、外表端庄而情感内敛的她真如同两个极端,却又在相通的生命意志与对生活的向往上要命的吸引着“把书读进生命里”的她。而迷龙对这个不但比自己以前的老婆漂亮上好几倍、身材好上好几倍、有文化有气质上好几倍,而且在这样一种人人争渡的慌乱中仍能保持镇定、还能给予自己安慰与鼓励的女人,也不自禁的感到钦佩,她实在是比自己这个大老爷们更坚强更有勇气。
当迷龙拼死搭起的渡索被龙文章用枪打断,渡江的希望断绝时,迷龙无力的跪倒号淘痛哭,上官先是恨铁不成钢的给了他一巴掌,再抱住他的头按在自己腿上;怔了一怔的迷龙把头拱进她怀里,搂住她的腰继续号淘。这一幕小说中没有而电视剧里加上的情形,很生动的展现出了一种男女之间在危难之下相互依靠、相互安慰的情感亲近,就在这一抱一哭之间,原本存在陌生隔膜的情感距离被拉近,亲密感慢慢的发酵,才能终至如酒般香醇醉人。也正是因为有了情感交融的一瞬,要迷龙放心去杀敌,说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母子的上官心中已对迷龙有了无言的认定。不仅是因为他在南天门上为自己甘冒被枪毙的风险造了那付棺柩敛葬死去的公公,更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令她感到值得交付身心的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然后,在经历过险死还生的南天门那场绝户仗后,回到禅达收容站的迷龙以为失去了捡来的老婆孩子,又回复了先前令人不敢招惹的收容站一霸的暴戾之气。但胖子克虏伯却护送着上官母子寻上门来,这对劫后余生的夫妻终于重逢了。前一秒还凶横的暴打克虏伯的迷龙,下一秒就拱到上官怀里哭号着:“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实在是令人觉得丢脸的难看,却又难看得令人感动。
接下来,开始了迷龙令兴奋向往、众炮灰弟兄不堪其扰的“新婚”日子,精力充沛、活力十足的迷龙又叫又唱的“夜半歌声”折腾得炮灰弟兄们彻夜不宁,直抱怨“什么世道,女人不叫男人叫”“这对黑夫妻还让不让人活了”。我朋友对这段最不能接受,认为以上官这样一个受过良好的传统家教、知书达礼、注重仪表又淡定的性子,不可能随迷龙一样不要脸的胡闹。我倒觉得,正因为上官是个受过传统教养的女人,习惯上有一种三从四德的柔顺,既然已经认定了迷龙,又是在这样的大难不死之后的重逢,会放开自己来顺从他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迷龙这样一种像讨糖吃的孩子似的无赖与燎原之火样的热情,对上官这样一个外表冷静而内心蕴藏着丰沛激烈情感的女人,有着火种般点燃他生命热情的作用。她过去所习惯的平静与矜持、教条与规矩,“都被迷龙这傻鸟钉进了棺材,随着那口棺材一起埋在了南天门”,于是一个重生的自我学着放纵自己,随着迷龙这样一匹“春天的野马”在生命的原野上尽情驰骋。
但迷龙与上官之间也爆发了争执,甚至严重到两人大打出手。争执的根源在于“一个妻子不愿意丈夫与整群不事创造,也没有破坏能力的废物为伍,她想走”,迷龙不愿丢下这群与自己共同出生入死过的弟兄和她一起离开,当然更不愿放她走。这样“走”的后果其实两个人都知道,兵荒马乱找食不易,夫妻俩还带个孩子,很可能是“三个成一家,三个死一堆”。但两人最终还是达成了“离开”的共识,就算前途未卜,也不愿为了一干一稀两顿饭窝在这个充满潦倒与颓废气息的地方混日子,蹉跎时光、浪费生命。“一个被挠得满脸花的男人正爱怜的触摸着被自己打得鼻青脸肿的老婆,这对同样有着“不切实际”的生活梦想与生命意志的男女,彼此支撑着站了起来,不愿做追逐胡萝卜的驴子,而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笃定了要走的迷龙决定避开与弟兄们的伤感告别悄悄翻墙离开,当他爬上墙头,回望这个与炮灰弟兄们共度了许多时光的小院,不禁唏嘘感怀。这种唏嘘不是懊悔畏缩,而是一种内心深藏的情感的浮现,也许连他自己都没觉察到自己对这帮“瘪犊子玩意儿”的弟兄们有着这样深挚的情谊。当骑在墙上的迷龙从高处望着禅达,将在城中四处寻找狗肉的从弟兄都收入视野中,东城的孟烦了和郝兽医、西城的蛇屁股和不辣、北城的丧门星和克虏伯,他脸上不禁又露出了梦境般的神情,绽开了笑容,“那样的笑容我们(炮灰弟兄)从来无缘得见,让墙下他老婆也看得痴迷”。
而本以为会被枪毙的龙文章却由伪团座成了真团长回来了,令迷龙离去的意志终于消散,这个能激起他沸腾的生命热血的妖孽团长与炮灰弟兄们一起,共同构成了他在“老婆孩子家”之外的另一个梦想,另一种致命的吸引。但一付励精图治、要大展拳脚样的龙文章却容不下这里有女人,要迷龙在家庭与弟兄间作出选择,迷龙无法选择,他既想要有个家过安逸的日子,又想跟随龙与众弟兄们一起杀鬼子打回东北的家乡,这两样都是能激发他生命活力的梦想所在。在迷龙左右为难时,上官主动站了出来,她淡定的看着全身脱得光溜溜的丈夫,“就如同看一个衣冠楚楚甚至全付武装的家伙”,告诉他:“你想做就好。我们没事的。”明白迷龙对弟兄们的情谊、对想打回老家梦想的渴望,她不逼他非要做出选择,为了成全迷龙的梦想,她选择了自己退让。迷龙看着上官拉着雷宝儿的手离去,当雷宝儿在临出门时终于回转头来向他叫出了那声他期望已久的“爸爸”时,“迷龙的脑袋像被狠槌了一样的转开来”;他愧对孩子的这声充满依恋与信赖的呼唤,愧对这个自己答应了要给她一个家、好好照顾她,却一再要她来体谅照顾自己的温柔而坚强的女人。
放任自己在雨中淋得全身湿透的迷龙,想着无处栖身而在人家屋檐下躲雨的上官母子,暗暗下定了决心,不管如何困难、不论什么手段,一定要给他们母子一个“不委曲”的家。这个既有着孩子般的率真执拗、也同样有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担当的男人,真的豁出去做了,他借龙的军饷搞黑市交易、吝啬抠门的拼命攒钱、玩套子以劈柴价买了家具、耍无赖磨人半赖半感动人而得到了一幢大宅子…迷龙是幸运的,连老天爷都似乎特别眷顾这个有着赤子之心、敢于为梦想拼搏的的男人。迷龙终于有了一个家了,家庭与弟兄,温情与豪情,他二者兼得。而这也正因为他不但有着一群贴心的好弟兄,更有着这样一个懂得他、欣赏他、并且支持他的好老婆,这朵“生机旺盛到不要脸的狗尾巴花”才能如此幸福的招摇。这对天造地设的“奸夫yin妇”终于在这战火纷飞、充满仇恨与杀戮的乱世里,奇迹般的建立起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生活梦想的令人艳羡的美满家庭。
2、迷龙与龙文章:痞子与汉子/信仰对生命的吸引
“我恨我的团长。他几句话就让迷龙回复成一条汉子而不是一个痞子。我们更喜欢痞子迷龙,因为我们中实在不缺汉子。”
-------------------------------------
阴间的赌鬼痞子迷龙与“在怒江边上迷了路的秃尾巴黑龙”的汉子迷龙,是迷龙所身具的两面性。但无论是他散财败家、孤注一掷的赌性,还是他作为最好的机枪手、仗义的东北大老爷们的“龙样”,从根本上都是对自身旺盛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为了能加入到缅甸打鬼子的队列,他可以用一把骰子输光自己相当于一个禅达中产人家的全部家当,且不顾此行根本与自己打回东北家乡的梦想是“俩方向”,是一种渴望改变颓废现状、寻求自我生命绽放的心灵本能在驱使着他做出这样的行动。
然而豁出一切赌注在这一把上的迷龙,收获的是再一次的失望。人肉罐头般的空运,半路遇到日军战斗机的袭击坠落在缅甸大地,立即便成了被抛弃的溃兵,除了一条裤衩一无所有的炮灰们在日军追击下只好一再撒丫子逃跑,令迷龙气得直怨“跟你们一伙还不如跟耗子认亲戚”。龙文章的出现扭转了这种沮丧的局面,他自称是他们的团长,将这伙溃兵聚集起来,化身为黑皮山魈,当真作到了凭一条裤衩杀敌。“绵羊在几分钟内撕碎了豺狼”,“杀人者原来如此虚弱”,这场胜利无疑大大鼓舞了向来与日军交战履履溃败的而逃的炮灰们,让他们感到日军也并非不可战胜的。
接下来,龙又带着他们打了几场胜仗,这个损德的妖孽总是采取避开正面硬撼而从侧面击破的方法,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更大的胜利。而这种不拘一格、仿如游戏般的战斗形式对于炮灰中最为好强又具孩子气的迷龙,更是极具吸引力的。在得龙传授了机枪的短点射击技巧及作战时的几个损招后,迷龙已完全被这个说话嘴欠但又确实总能直指人心的戳到点子上、打起仗来不怕死又确有真本事的妖孽团长折服了。先前对这个“疯子”的不忿与警惕之心已完全被一种胜利的憧憬所替代,虽然听了孟烦了“他会害死我们”的警告,也仍然带着做梦似的微笑说“我整死他”,那样的口气,全无威胁,只显得亲昵,“像是终于撞上了一个他流亡十一年来从未遭逢的精彩游戏”。对生存的焦虑与失去唯一的同乡的伤感,都被龙所给予的“希望”的幻像所盖过了。
然而接下来,龙假团长的身份被英国老绅士揭穿,弹药物资的供应被断绝,龙终于决定带他们回家。而回家是一场灾难,一路难辨方向的撤退,被日军在屁股后面追着打,要麻等弟兄的死去,所过之处又是一片主力部队撒退时留下的尸骸,充满令人恐惧绝望的无力感。看着这令人恐惧到麻木的由尸体点缀的长路,“迷龙好像忽然恢复了记忆”,他离开收容站时曾说过自己来缅甸是为了发洋财的,现在他似乎要把自己的话付诸实践。抛下机枪的迷龙,开始大肆搜掠死人的手表、钢笔、戒指、长命锁什么的,捡了一辆推车装了被主力部队抛下的罐头饼干,雇了康丫等人做苦力推着走。曾经被龙所激起的对胜利的憧憬破灭了,寻求改变的生命热情熄灭了,迷龙迅速变成了一个令炮灰弟兄们感到陌生的人,又再回复了一个霸道市侩的黑市老板形象。就连龙文章叫他一起返回头去杀鬼子一个回马枪,他也宁可当个活死人,而不愿“被人忽悠死”。在迷龙看来,既然胜利已经远望,再怎么打还是得撒退逃跑,那不如惜命聚财,好回去继续当他的黑市老板,过自己的安逸日子。
接着在南天门上,迷龙遇见了上官戒慈母子,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被重新勾起了对战争中失落的家园憧憬的迷龙,不惜孤注一掷以搏取自己梦想的赌徒性子又再发作了,他再次舍弃了自己一路上辛苦搜罗的货物家当,而专心致志为上官打造一口三寸厚的棺材作聘礼,一种“老婆孩子家庭”的新生活的向往再次点燃了他的生命热情,让他的旺盛的生命力再次有了释放的方向。
而迷龙一再升级的逾矩行为终于触到了龙文章的底线,在龙看来,迷龙之前的行为还只是自己所鄙视的“爱安逸”,现在却达到了“协迫同胞姐妹”“为了点淫乐之心鸡一样苟且”的不堪,所以为了整肃军纪、杀鸡给猴看,龙下令要枪毙迷龙。但龙治军的苦心却不但得不到孟烦了等老炮灰们的认同,更不被他所维护的“同胞姐妹”上官领情。上官严厉的讽刺了龙是自命为拥有高人一等的天才而为实现自己理想讨他人之命的“鬼婴”,会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的“霸王树”;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大道理(包括军纪)可以用来剥夺一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也没有什么理想值得凌驾众生而以人的生命作肥料。这与迷龙不拘于一切规则形式的强韧生命意志是一致的,却对龙将生命献祭给国家民族以实现“招魂”目标的英雄主义信仰是一大冲击。而且相比孟烦了更具思想性的“人道”原则,上官的话则显得更具个人感受性,符合龙所认同的心灵原则,因此对龙的冲击也更大。
而差点丢了小命的迷龙却并不记恨龙文章,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逾越军纪该受处罚的,只是以为也就是军棍或皮鞭教训一下的事,认为凭他们与龙穿一条裤衩杀敌的交情怎么都不到要丢命的地步。就算眼见到枪毙是来真的了,也只是央求弟兄们再回去帮自己求求情。迷龙心中认定了龙“不是东北人,可是个好人”,对于龙在绝境中救了他们并认真履行带他们回家的承诺,他是心存感激的,对龙领军打仗的才能也是膺服的,也愿意跟他干,只是在看不到希望的愤闷中忍不住想闹闹性子发泄一下。
在迷龙被放回来后,见到龙因心力交瘁而昏倒,他抱着雷宝儿走近,“看起来他好像想把雷宝儿当一颗硕大无朋的药丸喂给死啦死啦”,大概在迷龙看来,孩子所代表的天真活力是治疗一切绝症的灵丹妙药。只可惜被雷宝儿所讨厌的龙,这个时候还不能领略到孩子的天真活力所代表的希望。令龙重新振作起精力来的是他对“做眼前所需要的实事”的信念,而不是如迷龙般被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所唤起的生命活力。这是迷龙与龙文章在关于人的生命认识的价值观上存在的根本分歧。
在怒江渡口一片哗乱拥挤的争渡中,龙想出了牵第三条渡索整建制过江的办法,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为除去混在中国兵中的日军斥候而打响的一枪,引起了对岸中国守军的怀疑,平安渡江的希望破灭了。南天门峰顶上出现的日军前部更导致了中国溃兵们恐慌拥向渡口,只求一线逃命的生机而拼命拥挤。在这危机关头是龙文章独自挺身而出,硬是以一人之力阻住了这些像无头苍蝇般乱作一团的溃兵,又破釜沉舟的打断了迷龙拿命换来的渡索,又激又骗又逼,以一人抽几百人耳光的气势,终于使得这批惯于不战而逃的溃兵们被激起了血性和勇气,跟随龙重又返身回去迎战日军,以掩护妇孺伤员过江、为对岸中国守军布防争取时间。舍不得老婆孩子、一心盼望回禅达过安逸日子的迷龙,终于也抗不过这种血勇豪情的吸引,捡起被龙抛在面前的机枪,跟随着他冲上了南天门。在龙悍勇无畏的英雄气慨感召下,溃兵们拿出了自己从所未有的勇敢豪情,奋不顾身的冲向一场注定要输的战争。
这场惨烈的绝户仗,最终以一千余人中仅二十余人得以身免,逃得性命回到禅达而告终。但经过这打得人露出最原始的兽性、唤起人最根本的赤果果的生命感觉的一仗后,幸存者再无法回复以往灵魂昏睡的浑浑噩噩,他们有了自己是“人”的觉悟,向往有人能引领他们做出一些真正有意义的实事,才不致浪费自己难得一次的生命。而能令他们相信的交托自己生命的人,只能是龙文章--这个被他们所认同的、会“招魂”的妖孽团长。
在庭审之后,不但得以保命,还由假成真,真成了川军团团长的龙又回来了,在祭旗坡建立起了不被虞师主力团所待见,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炮灰团阵地。自此迷龙开始了在禅达的家与祭旗坡的炮灰团阵地间两头奔忙的日子,一面牵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和大小活计,一面操心着炮灰弟兄们的温饱生计;一边是家庭生活的温情,一边是袍泽情谊的豪情,两者都是引发他生命活力的梦想来源。比谁都热爱生活的迷龙,作为唯一一个有老婆孩子有家的人,却没有如别人所求之而不得的那样整天只想腻在家里粘着老婆孩子,他总是在阵地上疯狂的想家里的老婆孩子,回到家里又疯狂的想阵地上的团长和弟兄们,匆匆忙忙的赶回家来腻歪一阵,又匆匆忙忙的赶回阵地,以致于连和老婆说好了的再生三个孩子的繁殖计划都难以好好落实。就像上官对小醉说的,打这个仗的人都着了魔了,他们无法正常的生活,而从来都只能有半个人在这里,另半个则被战争勾走了。
如果说勾走孟烦了在小醉之外的另半个魂的是对南天门上那一千座坟的亏欠,是对如何令弟兄们的生命不致虚耗的未来的希望的寻求;勾走迷龙在家庭之外的另半个魂的则是龙文章所展现的为国家民族“招魂”的信仰,是与弟兄们一起争取“胜利”的希望。“人命真他妈短,人真他妈短命”,迷龙总是这么念叨着然后在一天内榨取一百天的快乐。正因为对生命有着超越常人的热爱、对燃烧自我尽情绽放生命热情有着超越常人的渴望,龙文章能唤醒他人生命感觉的“招魂”对迷龙分外具有吸引力。正因此,比谁都惜命爱活的迷龙却总是追随着龙,过怒江、去铜钹、上南天门,每一趟危险之旅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不只是因为他是最好的机枪手,也因为他是他的团长“招魂”信仰的最忠实追随者。除了龙之外,在炮灰团弟兄们中,迷龙最看得起的是孟烦了,这也是因为他看出这个聪明的瘸子是个难得的有着自我生命意识、而不会听死教条“装犊子”的人;而孟也是少数几个懂得欣赏迷龙恶霸赌鬼、无赖痞子外表之下,比谁都旺盛的生命意志与活力的人之一。
而致力于唤醒国家民族魂魄,眼中只见大“魂”而不见个人小“魂”的龙文章,却无法体会到这一点。因此,龙的信仰虽可以唤醒迷龙“汉子”的一面,让他由一个会撒泼耍赖的大孩子,变成一个敢于迎对死亡冲锋、有血性有担当的爷们;但龙却不知道,“汉子”迷龙不过是迷龙用以保护自己以迎对外在残酷环境的一付盔甲,“痞子”迷龙才是更能贴近他内在天真本质的一面。看似勇猛凶横的迷龙其实并不真的好斗,他的暴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与保护自己所重视的东西,这一点与迷龙最为亲近的迷龙老婆上官了解得最清楚,“其实迷龙从来就不爱打仗,他怎么也要跟你们一块待着,就因为他喜欢跟你们一块待着。”
迷龙最终的死,并不是在战场上“成仁”,而是失手打死了军部陈大员的侄子、那个当逃兵的炮长,于是由一个刚被奖赏的战斗英雄一下子成了“恃功自傲、抢械行凶”的不赦罪犯,在费尽心力而迎救无望之后,被龙亲手用枪处决。而导致迷龙失手杀人的,是一种由南天门上那38天煎熬苦守所带下来的条件反射般对着一切活动的敌人扣板机的惯性,就如同一个赌鬼克制不住自己的赌性赌了最不该赌的一把,却赔上了自己的小命。所以对迷龙的死,不只是龙文章,所有炮灰团弟兄都是于心存愧疚的,就如同丧门星所说的:“我们和害得赌鬼上吊的一帮子赌棍差不多啊。”而以自己的信仰,将迷龙拖进了战争这个大赌场,给了迷龙赌赢的希望,却最终令他丢掉了性命的团长龙文章,则最是首当其冲的受到迷龙老婆上官所憎恨。
3、上官戒慈与龙文章:毒与魂/爱恨对心灵的吸引
“不成人形,但眼睛像疯子一样炽热,他(龙)现在去迷龙家脚步都不带犹豫的…我觉得迷龙老婆的怒气不会歇止了,摧毁八百里长城也不会歇止,可他总会告诉我某个他认为大有希望的细节。”
如果说在南天门初遇时,迷龙一开始就以他强韧的生命意志与对生活的热情对因生活颠沛、前景黯淡而心生死志的上官产生了吸引;而拥有与上官的前夫同样“恨天无柱恨地无环的强人”特征的龙文章,则从一开始就令她产生了排斥。再加上龙摆出一付官架子,要处死刚为她造了那么样一付令人感动的“活”的棺材的迷龙,无疑只会令她在心里将这个冷血的男人与那些她看多了的迷恋杀戮、不懂珍惜他人生命的“为了理想要凌驾众生,为了凌驾众生再把理想当肥料”的霸道英雄划上等号。但龙在她尖锐言辞下被堵得面红耳赤,仍显得颇为讲理的并不为难她反而下令放了迷龙;接下来在怒江渡口时一片各人自顾自逃命的杂乱拥挤下,又是龙挺身而出、激励乱成一团的溃兵们返身拒敌、掩护妇孺过江,这些作为也无疑会使上官对龙的印象有所改观,虽然仍不认同龙的英雄主义理想,却会感觉他与她以往所见那些草菅人命的长官有所不同。
当上官与雷宝儿在禅达收容站与迷龙团聚之后,本打算一家三口一起离开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新生活,却因当上真团长的龙重又回来了,一下子栓住了迷龙的脚步。为了不让被逼着非要在老婆孩子与团长弟兄间作出选择的迷龙为难,上官主动选择了退让。当她牵着儿子的手走出来时,“她装作没看见死啦死啦,死啦死啦也装作没看见她--他们真是世仇的样子。”除对这群欠收拾的炮灰弟兄们缺德外,一向注重自己在外人面前的形象,不会对他人失礼的龙,却在上官这样一个女人面前如此有失风范,可见那篇“鬼婴论”给他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令他感到这个女人既不可小觎的思想深刻尖锐,又是对自己实践理想与探索信仰的一大阻碍;但他也曾对担心老婆孩子而不能专心战斗的迷龙说过:“顾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老婆比你强比你横”,可见他内心对这个坚强镇定、有自我见解的女人是不乏钦佩欣赏的。而对龙印象已有所改观的上官,也不再像先前般与他毫不容情的针锋相对,说自只己是来替丈夫洗衣服的,马上就走。她理解迷龙对他的团长与弟兄们的眷恋,也愿意去相信与维护他所重视的梦想,纵使面临被赶走无处可歇宿的困境,她也愿意为了这个带给自己生命热情的男人承受。
做为一个“将书的精华读进人的生命里的少数派”,又是一个从小受过良好教养、嫁入家世殷富的大户人家并生了个孩子的有足够生活阅历的女人,从过往的生活经历与书本知识的融会贯通中,上官懂得了人的生命才是高于一切世俗教条规矩的最高原则的道理,一切理想、规则、秩序归根到底都应该是为人的生命而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要人生命来作为这些死东西的牺牲品。但是从小所受的教育、出嫁从夫的现实处境、又是在这样一个没有道理只讲暴力的乱世,使她习惯了不把这种种内心的怨忿不满表露出来而表现出一付仿如对一切漠不关心的淡定性格,但内心隐藏的丰富感受却在这样的自我压抑中蕴酿出了深刻的思想与激烈的情感。
而仿如孩子般率真放犷的迷龙那旺盛的生命力就如同一颗点燃她深藏情感的火种,“在迷龙挥汗如雨的钉棺材时,天雷地火,她就同时成了少女少妇妻子和妈妈”--既受迷龙的天真热情感染而恢复了渴望爱情的少女心态;又有着与迷龙尽享男欢女爱的少妇一面;还要尽一个妻子的职责打理好家里,并替在思维上粗枝大叶的迷龙考虑生活细节;并且还要如应付顽皮的雷宝儿般,对孩子气的迷龙带着母亲式的宠溺而进行安抚照顾……集情人、女人、妻子与母亲四重角色与四重的“爱”于一身,上官对迷龙的感情也是异常复杂而深刻的,深到刻骨铭心。
受迷龙的天真热情感染,上官一度收起了锐利的思想锋芒而去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她会在炮灰团弟兄们面前照顾到迷龙的大男人尊严,会为了迷龙而退让做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就算几次被龙文章赶走,她也只会想“我真幸福,男人对于我就是迷龙与其他男人”。在迷龙眼中他的团长是个了不起的“将才”,“打没了一个团又划拉出一个团”;而在将个体生命看得比一切都重的上官看来,这种“将才”只是“疯疯颠颠打打杀杀”的好战狂,最爱做的事就是“什么都没有,可顶天立地又能翻天覆地”,会用诱人的理想图景把一帮子人聚集在自己身边,“让他们把你当他们,把你的想入非非当他们的想入非非”,然后心甘情愿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死。但上官知道无法阻止迷龙、也不忍阻止迷龙追随龙文章那令他着迷的“招魂”信仰,她只能在每次迷龙要去冲锋前叮嘱他“别冲得太前,那不是对得起你弟兄”。然而迷龙的死打破了这种幸福的景像,再次将战争的残酷杀戮之罪、崇高理想蛊惑丧送生命的可疑摆到了她眼前,无可回避的痛彻心扉。
迷龙死后,龙文章终于鼓起勇气借还债之名上门,上官“冰冰有礼”的接待了他,平静淡定若无其事般与他寒喧,只是母子俩都有着一双冰冷的眼睛。这份冰冷的平静令龙既松了一口气又若有所失,他不禁忏悔的说出自己连对孟烦了都没说出过的话:“我差劲得很,总是逼他们去寻死,其实一直是在觅活”,“其实我很想跟他(迷龙)去…这话我不敢跟别人说,一说出来剩下的几个就都完了。”从南天门树堡之战后,龙已领悟到自己坚持的信仰是如何的不切实际、自己这个所谓的团是如何势单力孤,只能任由“上边”的脑袋们予取予舍,曾经的满腔热血在现实的功利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但为了给幸存的弟兄们保留一个虚假的精神支撑,他仍得撑住自己挺下去,哪怕明知自己已是个空心人了。所以,在喝出上官递来的茶有不对劲,他一怔之后反倒“笑得开怀了”,一口气将那杯还烫嘴的茶喝了个精光,连茶叶都一起嚼了。上官的恨意终于随着这杯毒茶一起显现出来了,令他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承接对方给出的惩罚以赎回内心的安宁。
当龙走出迷龙家后又拼命的抠着喉咙催吐,这不仅是求生的意志使然,也是他知道自己还不能死,否则不但炮灰团的弟兄会感到天塌地陷的不知所措,也会让上官担上“谋杀阵地长官,还是一个功臣”的罪名。被孟烦了与林译碰见,送到全国协助那里洗胃后,好不容易终于保住小命。龙在昏迷中仍念叨着炮灰团的弟兄们,集合着他已化为炮灰的团,“毒药于他是酒,是可以渲泄悲伤与快乐的良药。”
在喝过一次毒茶,终于揭开了那种深刻到要自己命的恨意之后,憔悴失形到“像个鬼”却有“一双越来越像人的眼睛”的龙反倒有了再去上官家的勇气,虽然对于“炮弹可能会再落进同一个坑”不是没有顾忌,却仍不自禁的要上门自讨苦吃。这一次上官表现得与上次的“冰冰有礼”截然不同,仿如一个体贴得无微不至的女主人,再次奉上的茶中也没有了毒药。龙反倒感到有些失望,如果就此被原谅他又如何能原谅自己?但原本调皮捣蛋的雷宝儿却阴郁而彬彬有礼给他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藕粉,在那甜丝丝的热气中有着那他吃过一次而熟悉之极的刺鼻气味…再一次的喝下仇恨的“毒”,再一次的催吐洗胃的折腾,像蟑螂一样耐命的龙再次逃出鬼门关。虽被警告洗胃的药已经用完,再来一次就只好灌大粪了,龙仍坚持要再去,对他来说这不是求死而是求活,是令自己枯萎濒死的心灵得以存活得救的必要仪式。
被折腾得“不成人形”的龙,“眼睛却像疯子一样炽热”,再次前去迷龙家的脚步都不再犹豫了。他一次又一次例行般前去喝下上官所奉上的毒茶,喝下她心中深刻的恨与因恨而滋生的阴冷之毒。上官这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深刻爱恨情感,深深吸引着重视心灵力量的龙,令一向“现实得令人发指”的他感受到从所未有的心灵震撼。在承受着上官的恨与毒的同时,他也关注着她从一些细节所表现出的心理变化:她一直使用他已经喝出抗体来了的同一种毒药、她为儿子裤子上的破洞补了朵花、她在家门上挂了面小镜子…这些细节说明了上官心中对他一再上门来自讨苦吃的行为不是没有触动的,他的以身试毒也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令原本从迷龙死后就刻意将家里保持着迷龙死前样子的上官,内心有了一些“活”的迹象。
当孟烦了问龙是不是看上上官了时,他回答得毫不磕巴:“恐怕是。这辈子打过交道的女人怕也有几十号,拢在一起怕还比不过人家一根小指头。”当孟烦了问他“有希望吗”时,他回答得同样毫不磕巴:“没希望。”深深吸引龙的正是上官那种敢不顾一切的爱也敢不顾一切的恨的强烈情感,她的“摧毁八百里长城也不会止歇”的怒气背后,深埋着对迷龙深刻的爱,和与这种爱相反却同样深刻的对龙的恨,有多爱就有多恨,有多恨正说明有多爱。所以承受着这种深刻恨意的龙,清楚明白毫无希望。
在被虞啸卿邀往温泉共浴,许以“三万铁甲”、诱以“结束落后,结束贫穷,结束焕散”“粉碎积弱的命运”的光辉前景,龙死去的英雄之志再次被激活了。在温泉中洗得“脱胎换骨”的龙再次例行的来到迷龙家“喝茶”,这回心情已大为不同的他已有了心情对孟烦了老爹再次的讨书投其所好的以“名垂青史”的虚荣糊弄过去,还逗着雷宝儿玩。心思细密的上官从这些细节中敏锐的看出了蹊跷,一针见血的点出了龙心境转变的根由所在:“一个草菅人命的男人找回了自己的野心…心里装了很多事,再不用为小事计较。你又有了一个团,是不是?”龙如看一个巫婆般的看着上官,被她对人心理情感的洞悉而惊愕。上官再次尖锐的讽刺了龙以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蛊惑他人的“将才”,其实不过是一种忽视他人自身生命意志的意识强加,最终不过是剥夺了他人寻求自我生命意义的权利;就像从来不爱打仗的迷龙,却因为被他的信仰和许诺的希望所蛊惑一再的奔向死亡的战场,一再投身除保家卫国的本份事之外的“找死”的疯狂,而他真正想完成的家庭生活的梦想却成了永远的未竟之志。
这番话比那篇“鬼婴论”对龙的打击更大,已从南天门树堡之战中得到了对个体生命感受的深刻体悟的龙,再无法如当初那样将这些逆耳之言当“妇人之见”抛开不理。他“抱着头,一双肘子做支架,撑着颗迷茫得就要化作青烟的脑袋”,陷入了生平最大的思想迷茫中。终于明白自己一直以来所并不了解的迷龙内在本质的一面,龙第一次看到了迷龙的鬼魂,其实是个无神论者的他一直以来只是借“招魂”为手段唤起人的尊严与士气,并不真正敬畏神秘。这种对人的灵魂本质的全新认知,强烈的冲击了龙以往所有建立在“招魂”信仰之上的价值观,颠覆了他的信仰根基,“不是害怕,而是冰凉--一个世界被颠覆了,却又不给任何新的,那样一种冰凉。”
凭着最后一点对自己“看不出人怎么死,可看得出人怎么活”的坚持,龙劝说上官离开禅达,不要待在这种地方和死人一起过日子,“人活了,心倒死了”。上官则回应他,“和死人一起过日子就是你这种人给我们的赏赐”“是你的心死了。快走吧,趁着你还是个好人”“毒药喝完了,我原谅你了…我在你身上闻到了迷龙的味道,死人的味道。”被推出大门外的龙看着迷龙的鬼魂在掩上的大门后打量着自己的家,“这个爱死自己小命的妖孽”生动鲜明得一如生前。在这扇关上的大门后,一个活着的妻子、活着的孩子却与他们死去的丈夫、死去的老爹一起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心结囚笼中,再无法得以解脱的过正常的生活。这种令女人伤痛刻毒、令孩子阴郁怨恨、令死人无法安宁超脱、令活人无法看到希望的结果,就是自己所想要的“招魂”吗?就是自己所坚持的“对”吗?
如果说虞啸卿在南天门38天里失信的背叛还只是摧毁了龙对英雄主义的幻想,使他对一种体制内的救世英雄的期待幻灭;上官的“毒”与迷龙的“魂”则从根子上动摇了他对灵魂认知的自信,令他猛然醒悟到自己原来从没有触摸到过个人的“魂”;以往一直自以为是的“招魂”不过是一种“该遭天谴的狂妄”,一种忽视个人之“魂”而强加于他人头上的信仰,最终不过是一种使生命无意义的被浪费、使他人化为炮灰的“挖坟”。除了迷龙的家、除了上官母子,还有多少因战争而破碎的家庭、多少失去亲人的未亡人,要在“与死人一起过日子”的“赏赐”中痛苦煎熬;又有多少活着的生命要在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战斗中为一个充满诱人前景的光辉未来而光荣献身,其实不过是化为长官意志与英雄理想感染之下的炮灰,而“好像从来没活过”…
所谓“招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谓“事情本来该有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所谓“希望”到底在哪里?…当“被原谅了”的龙扑倒在禅达郊外的坟地上,抱着一座不知名的死人的坟头号淘痛苦时,这些找不到解答的疑问一定仿如刀子般在他心口上割裂着、翻搅着,令他早已千疮百孔的信仰、早已伤痕累累的心灵,更加的鲜血淋漓……
当在誓师授勋大会上,龙听到将要在西进打日军之外,北上剿赤匪,他仿如大难临头般的恐慌,说“老头子打不过年轻人,会输的”“请师座放我们回家吧”。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他明白红脑壳所代表的“年轻的”底层力量充满了因个体之“魂”的觉醒而来的天真活力,而不同于他们这些看似精锐实则失魂落魄的“衰老的”军队;更因为这种在保卫家国的本分之外的争夺权力的内战,不过是一种打着理想高调的幌子,而“把人变成炮灰,把炮灰变成荣誉”的生命浪费。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们显然已身不由己,为了不让弟兄们被迫成为内战下的炮灰,也不至成为杀戮生命的刽子手,龙想出了又一个绝户计,对自己的绝户计,他当众大叫“请师座让我带着共党的军队去荡平日寇吧!”这一下这帮蒙上红色嫌疑的“利刀快刀”再没人敢用,也就可以保住了弟兄们的小命,而代价是他自己绝对的死路一条。
在龙被判枪决的前夜,虞带着孟烦了、张立宪前去看他时,龙在面对死亡而放下一切现实的烦恼后终于得到心灵的平静,并从这种平静的思考中终于超脱了一直以来困扰着自己的信仰的痛苦与迷惑,找到了能令自己安然放心赴死的希望所在--“永远也不要想通。四万万个脑袋拼出来的世界,有生有死的,每天都在变。做该做的想做的就好了。”“错一定输给对,年轻一定取代年老,只要它是真的年轻。”“到头了,会年轻起来的。…我们会等来个想不到的东西,它终究会比我们好。”
经历过最艰难的死中求生的战斗、感受过最深的心灵的创痛、走过最漆黑迷茫的暗夜,龙终于从崩溃的信仰废墟中,重建起一种超越短视的人类理性与一时一代的社会体制架构的、更恒久而长远的人的灵魂感觉与天地自然相通的而必然导致的“让人更像人”的“进化”趋向的信心,一种对与自然精神相通的个体灵魂的信仰。只有这样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个体灵魂的苏醒,才能真正令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与民族之魂也随之苏醒,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世界,才是“事情本来该有的样子”。
足以令龙的在天之灵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在他的出殡之日,上官母子终于离开了禅达北上,不再陷溺于那种“与死人一起过日子”的绝望中,而试着听他所言,把死人放在心里,开始新的生活。这也是龙敢于坦露自己灵魂的反省与坚持的心灵力量,终于慢慢消解了这对母子心中的“毒”,重新唤醒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的证明。
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上官的话对龙文章的确有很大的触动(打击)作用,但不能说龙是被她害死的。其实,我觉得上官的话也多少带有些仇恨之下的偏激,至少龙并不是个真如她所指责的为了自己出人头地的野心而“草菅人命”的无良者;恰恰相反,龙是个具有极强大心灵力量的人,这一点从书中一再强调他的眼睛很亮(也许是最亮的一双)可以看出,因而对战争中人命贱如草芥般的深切悲悯趋使着他致力于想为国家与民族“招魂”,想让这些被当作人渣子兵垢子般被精英轻忽的炮灰们“有个人样”。在这一点上,他与面对家国沦丧“愤怒但不心痛”的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同样有着英雄的救世情怀,但虞想要的是强国厉兵,注重的权力与实力,龙想要的则是强民壮魂,注重的是人的尊严。
正因为龙这种从根子上注重“人”的心灵力量,孟烦了等炮灰们才会与他一起去做明知是疯狂的找死的举动,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把命交给他;上官也才会终究被他一再自找苦吃来喝毒的灵魂真诚所打动,最终听从了他的劝告而离开禅达过新生活。
龙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他的“招魂”信仰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认知缺陷,即只见国家民族的大“魂”而轻忽个体的小“魂”,也就是关注整体局势需要而忽视个人的生命意志。这样必然造成以代表整体的长官意志强加于个人的“以理想而凌驾众生”,在战争的极端状况下便必然酿成“把人变成炮灰”的悲剧。这种信仰认识上的局限性,造成了龙以往行事的许多无意的过失,最终收获了难以下咽的苦果,迷龙之死就是一颗最大的苦果,就如孟烦了所说的“你给了我们不该的有的希望”。但这并不是他良心与良知的问题,而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根本许诺不起这些梦想中的前景。
同时炮灰们也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而忽略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算有着超过常人的心灵与精神的力量,但作为一个与虞啸卿截然不同没有任何体制内背景所赋予的权力的人,他也根本负担不起为他们的未来谋求幸福的希望。所以唐基才说龙是活生生被炮灰们拖死的,是他们所寄予的过大的希望压垮了他。
其次,龙对炮灰们的“招魂”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感觉的唤醒,让他们能感觉到自己一直以来昏睡的魂的“开窍”;但龙能唤醒他人的灵魂感觉,却不能真正触及他人的魂,甚至对自己的魂也并没有摸透。上官的话可说真正给他开了窍,让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灵魂,认识到自己在心底真正注重的东西--不是一种虞所许诺的“粉碎积弱命运的力量”,而是一种能引领着世界趋向“让人都像人”“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的终极信仰。正是因为有这种灵魂的底蕴,他才能在心灵被刺伤得千疮百孔、痛苦不堪的同时仍骄傲的坚信自己是个“天才”,不是短兵相接或偷鸡摸狗的天才,而是拥有特殊灵魂感悟秉赋的天才。
所以,龙最终的死,我认为是应该算是他忠于自己灵魂信仰的殉道行为。因为在现实中“条条路都走不通”的绝望处境,却又太过于执着于灵魂的“对错”无法妥协去同流合污,又为了帮助可能会被当作磨砺战争机器的“快刀利刀”而送上内战战场的炮灰弟兄们摆脱这种生命无意义浪费的命运。说到底这仍然是他对自己“灵魂”信仰的坚持。而最后,在死亡来临前的日子里,他终于收获了自己一身所追求的终极信仰的果实,才能感到生命有所价值、不虚此生而坦然的赴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