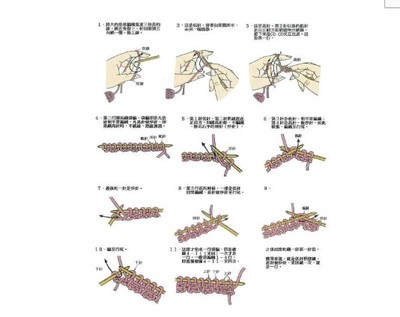凤尾花之死李晓琳发表于《激扬》
壹)
门半敞着。厚实的印花布窗帘紧拉,密不透风,使整个房间都被掩映在灰暗里,人和摆设便都模糊得仿佛实体的投影。暗陈的大沙发上,素喜盘腿而坐,看到我推门进来,才不慌不忙地起身穿鞋。
“你来了,默默。”她的语气很平淡,不像老友久别重逢的样子,这多少是出人意料的。
她也并不迎向我,只是转身移步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了。光线瞬时填满了房间,我这才看清她的样貌。暌违五载,时光真能改变一切吗,素喜全然不是五年前我所认识的那个单纯、羞涩的小女孩了。潮蓝的眼影,艳红的嘴唇,烫成大卷的头发散漫地披散着,瘦削的身体罩一件绣花薄缎睡衣,跻一双粉棉拖鞋,单薄里自有一种妩媚。若她手里再叼一支烟,就真是张爱玲小说里的民国女子形象了。
来此之前我曾做过心理准备的,一个毕业后未工作就嫁给富商过起上层生活、不出三年却被逼离婚的女孩会变成什么模样。但素喜的转变仍是让我吃惊不小。不单外表,她的眼神里添了浓墨重彩的颓废。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情同姐妹的。只是毕业后一个嫁人于外地,一个辗转受累于生计,渐渐便断了联系。
见我愣着,她便先开口笑说:“默默,你怎么竟有空到洛城来了,若早一天打电话,我也好去车站接你。”
我笑了,觉得这才像几分我所认识的素喜,答道:“来得匆忙,到了才想起打电话给你。电话里也没来得及说,其实我是辞了从前的工作,到洛城来找些发展来了。”
她的脸上掠过一层犹疑的神色,只一闪而过,使我倒怀疑自己看错了,停了停她便说:“哎,我这两年也很难了,全靠离婚时拿到的那点钱过活,想帮你,却也帮不到什么。”我便明白她是误会了,忙说道:“什么帮不帮的,我在来之前已经跟这里一个公司签了合同,过两天便可以去上班了。今天就是来看看你。”
素喜的脸由白转红,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我开始搜肠刮肚地想些别的话题。
“这两年一个人住还过得惯么?总没有人说话,也是够苦的。”
“那倒不是,一个乡下来准备考研的女孩跟我合租,她住里间小屋,摊三分之一房费。没人说话倒不会呀,但也不见得不苦。”她苦笑着加上一句,“日子总是苦的。”
素喜真的变了,但我张了张口,却无从安慰她。也曾从过去的同学口中听说她离婚的原因,结婚不多久,她小城里的亲戚便都纷纷找上门来,希望她帮忙给子女安排工作。她也是经历过苦日子的人,对亲戚自然倍感同情,便在丈夫跟前絮聒了几回。她丈夫偏是最讨厌走关系跑门路的人,对素喜便多了一层轻薄,渐渐地疏远了她,而她三年内竟也没有怀孕过,最后便离了。
我能理解素喜刚才的犹疑,对我的来意产生误会也是合情合理的——任何人经过她的景况,心上大概都会添上一层敏感和悲观。尤其这两年,在我经历了工作和生活的诸多不顺后,更是对这种悲观深有体会。然而我的失落仍像被沛雨激活的芽眼,不动声色地破出土层来,蹲伺在这段友情的旁边。分明有什么原本颠扑不破的东西在心里松动了。
正想着,房门突然吱呀开了,进来一个圆脸盘、肤色偏黑的女孩。脑后草草地扎一个马尾,脸颊上有终年不去的冻疮红,身上一件暗橘黄夹克衫,黑布裤子,个子不高,人却一点都不瘦,带着一丝壮实感。看见我,非常朴实地一笑,又将眼睛转看素喜,我便明白她就是与素喜合租的女孩了。
“凤妮,这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你叫默默姐就好了。”素喜的语气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傲气,并且未将凤妮介绍给我,仿佛一同将我也划为高人一等的范畴了,这使我感到有些不悦。
凤妮却殷勤地叫我一声“默默姐”,丝毫没意识到这种不公的样子,径直走到靠墙的木椅子上坐下了。空气有一刹那的静,我看看素喜,她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倒是凤妮先主动开口了:
“默默姐你从哪来的?你们是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么,不过我搬来这么久了,怎么没有见过你哩。”
我只好客气地向她解释原由,并询问她准备报考什么学校,有几成把握之类。
“还有几个月就要考了,紧张得很!我现在在那所学校上最后的考研冲刺班呢。”说到这里她像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睁大眼睛看着我们说:“对了!今天我去上课的时候,亲眼看到一个男孩从五楼上跳下来,当场就摔得血肉模糊,把我吓死了!他们说他是学哲学的,走火入魔了。我想不管你是学什么学,也不能这样想不开吧,真傻!学得越多反而越倒退了。”
我见素喜紧蹙着眉头,面露嫌恶之色:“什么越学越倒退了,不懂你别净乱说!”
凤妮呆愣住,完全没料到别人在这点上会跟她意见不同。“本来就是嘛,我爹不识字都还说过,‘死都不怕,还怕啥子活着?’这样死了太傻了,不值,你说不是吗,默默姐?”
我觉得尴尬,但我的确不觉得那个哲学系男孩很傻,只好说:“这说不好,要看他是为什么自杀。苏格拉底也说过,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嘛,死对那男孩是一种归宿也说不定。”
凤妮很惊讶,脸上凝聚着不知如何辩驳的表情,最后她轻轻说,“你们这些城里的知识分子,太让人搞不懂了。”
素喜从鼻子里一哼,笑道:“你看,我以前就说过,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这样的针锋相对让我觉得难受,却不太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于是我匆忙地起身说道,“那么我先走了,东西放在宾馆,还要回去收拾。”
“啊,默默姐,你要在宾馆长住么,这么贵,不如搬来跟我们一块住得了,里面还有一间小屋的!”她伸出一只手指起劲地朝里指着,喜滋滋地瞅瞅素喜,仿佛深谙了她的心思似的。
我料到素喜脸上会有不悦之色,她以前一直是喜清净的人,何况五年苦境之后呢。就算是对“最好的朋友”。这些凤妮都是看不出来的。
想不到素喜却说:“搬来住……也好。”
我万分惊喜。素喜补充一句:“三人平担房费……倒也好。”我的心冷了一下,转念倒反而因她的话放下心来:悭刻些是不怕的,怕的是遮掩悭刻。所以我非常高兴地答道,先看看公司附近有没有合适的房子,若没有再搬来也不迟。
贰)
再到素喜的房子去是一个多月之后的事了。这期间我住在单位附近一栋楼顶层的阁楼里,挺自在,但是没有暖气,冬天越来越迫近了,在夜里我常常被冻醒,手脚冰冷。于是我想到再到素喜那里去一趟,同她商量可否入住的事情。
下班之后,正是饭时,我特地绕到水饺店,买了三鲜馅的水饺带去。想起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小姑娘常常一下课就抢着去一家水饺店吃饭,那一家生意兴隆,去晚了便要心急火燎地排队等,素喜总是点三鲜馅的,像个小动物一样口味单一。
进门的时候恰巧凤妮在换鞋,也是刚回来。我笑着拉她一起来吃水饺,她生硬地瞥了瞥素喜,最后低声说,“不了,默默姐”,便走到自己的小屋里关上门。片刻后一种劣质收音机的声音“滋滋拉拉”从里面传来,播的是英语广播。
“又放开了,天天的不让人清净一会儿!”素喜的嫌恶同那天一模一样,不,应当说比那天更甚了。这一个月里,她们之间一定是发生过什么正面的冲突,使粗枝大叶的凤妮都明显有些不快了。
“你可以告诉她,让她戴上耳机嘛。”
“耳机?我哪能没告诉过她?人家说了,俺老师说,戴耳机练听力的效果最不好!人家不干!”这最后的一句素喜故意提高了嗓音。
收音机“嘎”得一声停下来,空气倏然静得让我毛骨悚然,小屋的门开了。
出乎意料,凤妮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来为自己辩白,或者同素喜大吵一架,她只是沉默地走到门口穿鞋,拧着眉头,表情严肃,这让我既是感动,又是同情。
“凤妮,水饺正好剩了一碗,你过来吃点吧!外面太冷,你就别出去了……”我尽量让语气温柔些,素喜却打断我说道,“默默,你让她去吧。”又自言自语地说:“房费里又不包伙食费。”声音奇小,但我还是听见了。
凤妮出去了。我低头吃着饭,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素喜,为什么你的心变得这么坚硬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提想搬进来的事呢,就算你同意,心底也一定是极不情愿的。
之后我主动提出去洗碗,素喜没有强劝我,帮我把碗筷端到水龙头去。我听到她打开电视来看,不停地调换频道,后来又听到凤妮回来,一言不发走回自己房去了。
我暗暗下着决心,要真诚恳切地同素喜谈一谈。现在五年的时光横亘在我们之间,使我跟她是如此隔膜而生疏了。五年的变迁就像刀刃般划伤了素喜的心,一定是伤口太深,才使她到现在还耿耿于心,难以释怀。然而素喜,人若要生活下去,是不可能没有伤口的,你可以无法让伤口愈合,但一定不要让自己因此变得怯怯,并且刻薄——这一点,请你一定要记得。
我洗净手坐在她旁边,见她愣愣地看着电视,思忖该如何开口。偷偷瞄她一眼,却发现她的眼里全是泪,脸上已经满是泪痕,妆都花了。但她的哭竟是那么静,没有声音。
我感到自己的泪也滚下来,扑簌簌的,我伸过一只凉手,在黑暗里握住她的手——那只手也是那么凉。我仿佛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黑发及肩的小女孩,干净姣好的面孔上嵌着一对清亮的眸子,傻气地、顽皮而无忧无虑地朝我笑着。然后我看见我自己——年轻的我自己,悄悄走到那女孩的身后,在她肩上拍一下,又嬉笑着跑开了。
“我变了。”素喜开始絮絮不止地说起来,她所说的,正是我想说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会这样了,每次想起来就觉得害怕,绝望。从五年前毕业时候起,我就像一截花梗一样,一寸一寸地变了。先是结婚,变骄傲,变浮躁,到后来离婚,变颓废,变悭刻……现在我是完全地腐烂了,默默,我再也活不了了。”
我都懂的,素喜。但我没有告诉她,只是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她这才转过脸来望着我的眼睛。

“凤妮是好女孩,我是知道的。我也不想那么对她,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一见到她,就同情她,然后痛恨她。她是那么愚鲁,无可救药,可是又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愚鲁!无论你怎么说她,她都是一样不疼不痒的,就知道学习,学习,学习!学那么多习,还是只知道上学是为了工作、嫁人、传宗接代,还是会那么粗俗的说学哲学的人自杀就是傻瓜,是倒退,而且说的那么肯定!”
我抬头瞧瞧凤妮的房间,门是紧闭着的,但灯光从上面透出来,怕她早已经听见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怕”,像凤妮这种女孩,我在电视与书本上都见过许多,我确信自己一丁点都不欣赏她们,而她们也确实需要一些残酷寡情的点拨,方能觉醒过来。
“素喜,经过了这几年,你还没想开么,有些事和人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没办法,你只能宽容。何况凤妮这样的性格对你的影响也不至于到难以忍受,毕竟……毕竟你的伤口又不是她造成的。你不能把委屈转嫁到她身上呀。”我本来该站在素喜这边的,但同样不知为什么,我最终帮了凤妮。
“不是她造成的……向林跟我离婚,就是因为有了跟她一样的一个农村来的女人!她们身上都有那样一股子劣根性,除了安分朴实还能有什么优点……我永远永远也想不通……”安静的哭泣变成抽噎,使素喜话都说不成了。我再不知该站在哪边,两个人都让我同情,而且细究起来,其实世上每个人都多少值得同情,每一个人的故事中都多少掺带些悲剧色彩。
但将心里话倾吐出来,素喜似乎好多了,我去用热水洗了毛巾,慢慢地给她擦脸。有几秒钟我恍然觉得她依然是个小孩,有委屈就可以无助地哭,没有变过。渐渐地她停下来,蜷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在黑暗中枯坐了许久,像独自在茫夜里乘一只漂泊的船,没有岸,而周围是那么安静,我的内心却像翻腾的海水一样,一刻不停地汹涌、搅动着。凤妮的灯竟还微微亮着,我知道,像一只倏然看见灯塔的小船,无论如何我将要朝那灯塔而去了。
叁)
我没有在她们那里住下来,因为不想让素喜哪怕有一丁点觉得我开始的到来是有图谋的。但在下班或周末的空当里,常常会跑去看她们。事情并不像我想象里那么好,她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多少改观。我不知道是双方都碍于面子,还是素喜依然忘不掉她的伤口,抑或凤妮也被深深刺伤了。
那一晚同凤妮的交谈使我意识到,这个女孩其实有着那么强的羞耻心。羞耻使她意识到自己存在着遭人轻视的不足,愚钝却又使她不明白自己究竟不足在哪儿。揭掉遮羞之物,她环顾周身,丝毫没有找到症结所在,而只是揪出了自童年时便因穷困而潜藏在骨子里的,深深的自卑感。
“默默姐,我不知道为啥素喜姐就那么看不惯我。你们城里人为啥都看不惯我。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又没有破坏过你们的生活。我只不过是要来考一个研究生而已,我真不知道,我有啥错?”长久的沉默之后,凤妮终于痛苦地对我说。
后来我突然发现她不再听英语了,而是抱一本哲学书来读,紧蹙着眉读得入神,有很强的求知欲。我有些担心,但不好说什么,只好劝她最好不要读萨特,有关自杀的也不要读。
“你还是好好准备考研再说,这些书现在对你没多少用的。”
她似乎反而以为我是觉得她不可能读懂,偏专门借了萨特等人的书来。“存在是虚无的”、“自杀是唯一的哲学命题”这类话题,似乎最大程度地带给了她烦恼,使她日日思索而没有结果。
“默默姐,我还是搞不懂,你来给我解释解释这句。”她手里攥着一支2B铅笔凑过来,厚厚的书页上满是波浪线与歪扭的标注。这些都让我望而生畏。
“我也不是学哲学的,哪里懂这些。真的,凤妮,你不要再看这些了,”我伸过手把她的书掩上了,“这是没有用的,至少,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你根本用不着这些,原来的你不是挺好的么。”凤妮非常生气地把书夺回去,扭身走了。
也许我本应当向她解释的是,没有人能真正读懂哲学,因为没有什么能证明你懂了。哲学系男孩的自杀不能——或许他只是处在将懂而未懂的关口上,便匆匆死去了;我们这类人在粗知哲学后,依然选择如此充满尴尬与痛苦地活着也不能——是那些微小的快乐抑或对死亡的恐惧将我们留住了吗;少数人看淡一切选择隐居出世也不能。然而对这一切我所以为的“不能”,我都不够确定。或许哲学就是一种不确定,谁又能说得清呢。
肆)
后来我回想起整件事,还是不可避免地想到那次凤妮的受伤,以及素喜出嫁时穿过的那条红色真丝裙子。这个故事的结局,或许多少与那件事有关。
那一天我去的时候,素喜两根玉指捏一瓶烫伤膏之类的东西,神色匆忙地奔来给我开门。素喜开门本就是稀奇事一桩,进门后,果然瞧见里面的小屋内,凤妮裤管拢到膝盖处,正支着一只红肿的腿靠在床上。
素喜顾不上招呼我坐下,就重奔到床前给凤妮敷药,额上粘着一层轻细的小汗珠。
“以前说她笨她还不肯承认呢,真是的,打壶热水还能把脚烫了。”刀子嘴豆腐心,我突然发觉专注的素喜真美。
看出来凤妮有些受宠若惊,格外老实地看素喜给她敷药,一动也不敢动。她张了张嘴,最后憨实地吐出一句话来:“素喜姐,别担心……拐杖钱和药钱我都会给你的……”
素喜噗嗤一声笑道:“当然得给,又没说白送你的,可是你现在能不能不跟我提这个,真俗气死了。”
那一刻我清清楚楚看到,素喜和凤妮脸上洋溢着同样的满足与幸福感。
素喜帮忙把我买来的菜运到厨房,我们二人开始准备午餐。她突然从冰箱里拿出留了很久的排骨来,开心地举给我:
“炖这个!吃这个凤妮好得快!”
看来没有什么隔膜是无法消除的,再苦再难素喜也无非是善良人中的一个。我忙来忙去地切菜炒菜,凤妮极少下厨,在一旁总显得碍手碍脚的,我却依旧兴致勃勃,高兴极了。一盏明亮的小灯在黑暗的路上悬着,我看到了希望。
“默默你看”,她伸出两只手举到我眼前,“佩服吧,昨天我自己洗了一大堆春天的衣服,手又开始过敏了。”
“细皮嫩肉的,真难得你也洗衣服,怎么心情这么好啦?”
她笑道:“当然心情好啦!你知道么,我跟向林结婚时候那件真丝连衣裙给找着了!可是镶钻的!向林那时就是那么舍得为我花钱!离婚时找了半天,还以为丢了呢。”
她突然沉默了一霎,轻声说,“默默,昨天早上向林来找我了。他离婚了。”
我心下一惊,抬起头盯住素喜的眼:“你还爱他?”
素喜似乎在心不在焉地摆手指玩。最后她说:“你知道的,默默,大学四年我都没恋爱过。这些年,我是再没有爱过别的人了。”
从凤妮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凄厉而惊恐的尖叫,我和素喜都以为是凤妮摔倒了,慌张赶过去看。
房间里凤妮正一手拄着拐杖,呆立在写字桌的前面,另一只手悬停在空气中,握着一只黑色的电熨斗。一打熨好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旁边。
桌子的正中间,我看见了素喜刚才提到的那件连衣裙。华贵的玫瑰红,裙裾上缀满亮闪闪的钻石,平整地在桌子上铺展开来。然而,前胸的真丝布料却整个被烫焦了。
我慌神地忙去看素喜,她的眼睛还紧紧盯在那件裙子上,脸色白得怕人。几秒钟之后,房间里第二次传来凄厉而惊恐的尖叫声。素喜冲动地上前一步,响亮地给了凤妮两记耳光,又一把将她重重推倒在床上。
“乡巴佬!!”她愤怒而恶狠狠地指着凤妮吼道,“乡巴佬,你不知道真丝衣服是不能熨的吗?你根本赔不起,你这个白痴!”
素喜瘫坐在地上,绝望地嚎啕大哭起来。
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令人心酸的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素喜的绝望的嚎啕,以及倒在床上的那个女孩那般复杂的眼神。仇恨的然而矛盾的,羞愧的然而无助的眼神。
伍)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从电视上看到新闻,说是研究生考试已经正式结束了。我想着也有许久没有去看素喜与凤妮,不如趁此机会顺便去一趟也好。
敲了很久的门都没有人应,这在往常是没有过的,素喜尚未找到满意的工作,这个时间段不太有可能出去。房东听见敲门声出来,很惊讶地看着我,压低嗓子说:“你还来这里做什么?中午跳的楼,现在早送去中心医院了!”我感到五雷轰顶,木楞在那里,浑身出了一层冷汗,待要问,房里却有一个男人走出来,朝女人使了个眼色,拉进屋里去了。
我忙转身下楼,打了车去中心医院,只觉得腿都有些瘫软,脑子里一直重复着三个字,不可能,不可能。
是素喜吗?这段时间尽管她整个人蔫蔫的,一言不发,但显然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刻薄计较了呀……难道,正是这样才表明了她的绝望,完全失掉了生活的动力,以致对一切都不太在乎了?不,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过她要自杀,就算她说过她是“再也活不了了”,也不应当绝望到自杀的地步的。
那么,是凤妮?她的确苦钻哲学,表面上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可是近来她表现得颇为平静,甚至凤妮的两记耳光与无情的咒骂都没有再去计较。况且我清楚得很,她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已经觉得世界没有出路而要自杀的地步的,对她来说,世界有无出路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自己能切实而本分地活下去,给故乡的父母一个满意的交代就够了——事实上,活着的我们大部分人,哪一个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呢。
急救室门外的灯光有一种可怖的森冷。也许只是因为长长久久或者此时此刻,它离死亡太近了,近到一种不近人情。女孩独自在绿椅子上坐着,黑大衣歪歪扭扭地罩在身上,敞着襟,里面是未来得及换的睡衣。她的眼神完全直了,处在还未完全反应过来的状态里。
一看到我,她的眼泪才汹涌而出,抓住我歇斯底里地喊道:“你知道吗,她死了!默默!她死了!!”她一定觉得是自己一手害死了凤妮,现在她真正变成罪孽深重的女人了。半晌,素喜眼里仅剩的一点光亮逐渐黯淡下去,又骤然“啪”地一下熄灭了。泪腺里涌出的最后一滴眼泪浇灭了它。然后她像彻底下了决心一般,从口袋里掏出卫生纸狠狠地擤了擤鼻子,又胡乱擦干了眼泪,站起身来蹒跚着向医院门口走去了。从头至尾,她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没有向我表明她的惊惧、自责,甚至在她决定破罐子破摔从此就这么掖起心活下去之后,也没有对我说一句。
我是后来才打听到那件事的。
女孩站在空旷的阶梯教室的最前面,面对着坐在她对面的一排西装挺括的教授。两只汗黏黏的手时而绞在一起,时而向下牵牵衣角,这一系列动作使她显得那么局促、慌乱,根本逃不过考官敏锐的法眼。黝黑的肤色与脸上暗红的冻疮掺在一起,给人一种粗浅感,任何人都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的头脑里,究竟能装有多少深邃的学问和思想。因为羞耻心的觉醒,她突然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不美,甚至算得上一种丑陋。这种丑陋如此恶劣而深刻,像纹身一样刻进她的皮肉里,基因一般植在她的骨血里,而她在之前活过的二十年中,为此倍受歧视却浑然不觉。此刻她的脸上没有丝毫为了奉承考官而勉强露出的喜色,只是一种单纯的、浓重的忧愁。
考官的提问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最后她呓语般地说道:“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我是这么庸俗,真的。我只知道照父母那一代人给我的思想活着,学习、赚钱、嫁人、生仔,可我自己根本没有思想,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我想了很久,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如果这些都没有意义,我这些年的生命也根本没有意义,以后的日子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候,哭泣也许能博取一些同情,使人们温存地劝慰她一番。但她似乎根本不会哭,因为她自小便被告知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最后的时间里,她永远是那样严肃地紧蹙着眉,一个劲儿地想着。教授们都觉得这个学生让人无奈,但更让人厌烦,她一脸的卑怨有一种奇异的丑陋。他们都建议她不该来考什么试,而应该回家去休息休息。
其实,是在很久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死去的是凤妮,而不是当时同样无比绝望的素喜。品尝过大繁华与大富贵生活的人,无论陷入怎样灰颓的境遇之中,始终在潜意识里怀有对人世的一份眷恋。她知晓人世之中,总有一些可以满足人欲念的或深或浅的东西。一件华贵的衣服,或者一支音乐,一本书。甚或对它们的回味与向往就足以支撑一个人活下去。
然而对于凤妮,一个从未见过世界开启之后是何模样的姑娘,生命的残酷与荒芜猛然向她展开的时候,她所面对的仅仅是一份毫无意义的生活,以及一个赤裸裸、孤单单、荒谬而蒙昧的自己。她发现竟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能帮助她再次鼓起希望。
花梗腐烂了,顶上的凤尾花,才是真的死了。从此我再不同人妄谈哲学,生命的戏剧化简直像一个谎言。
(完)
2009年4月 于吉林四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