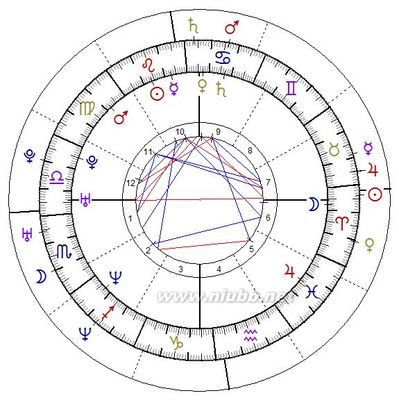奥柏伦·马泰尔死了。死得不堪直视,践踏审美,以及午饭。“多恩壮士密如沙,为此一人甲天下”。青春少年的他已早早环游维斯特洛,提利昂说他和七国一半的女人上过床,他被多恩男女老少无尽地宠爱,他俊朗的形与不羁的神,他王的身份、气质、着装品味……好吧,可他还是死了,valar morghulis……若是在大陆编纂的各类神剧里,亲王殿下或许应得一个唯美些的结局。可在权力的游戏中,寒光一闪头颅落地,拳头一锤脑浆四溢,无论一个人多么高贵、冷艳或美丽,都只是一块偶尔会思想的肉而已。所以,欢迎来到冰与火的世界,当七神的歌声响起,愿乔治·马丁保佑你早早坦然、百毒不侵,最终毫不在意。
然而,还是之前在看小说的时候,早早思索过一个问题。若奥柏伦在决斗时不去选择他心中最正义的处决方式,结局是否会不太一样?很多人开始凭此嘲讽红毒蛇,他的傻不拉唧,他的刚愎自负,他的死有余辜。在其置换叙事里,奥柏伦理应在魔山跪下去的一刻,操起长戟刺穿他的狗头,而不是为死去的伊莉亚追诉可谓“虚无”的正义,以致最终被敌人有机可乘。毫无疑问,奥栢伦斩下了魔山的狗头,奥栢伦继续狂吻他的情妇,奥栢伦恶狠狠地嘲讽令人厌恶的兰尼斯特们……可我不知道是否他还是那条令人着迷的多恩毒蛇?在一个良知论斤买卖、灵魂一折出售的世界里,令人着迷的东西太多又太少——理智的太多,审美的太少——多恩毕竟是虚拟架空的世界,而人类或可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些许昂扬。
这便是为何我想说的,是“最后的罗马人”而非“最后的多恩人”。奥栢伦让我想起了两个罗马人:凯撒与布鲁图斯。在莎翁构建的文学形象里,罗马共和的死亡归于两具神像的坍塌:“弑君者”布鲁图斯同“暴君”凯撒。前者象征着守卫罗马共和精神最后的天使,用凯撒的话简单概括,是没有比布鲁图斯更高贵的人;而后者则是罗马英雄精神所浇筑的最后的王者,连共和派的敌人都如是说:“要是我们能直接战胜凯撒的精神,我们就可以不必戕害他的身体。”。在布鲁图斯的个人生涯里,凯撒是最好以及最具权势的朋友,然而其祖先卢克休斯·布鲁图斯的血统召唤他刺杀凯撒,虽罗马共和已无法匹配其个人理想:“并非我不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这驱使他完成那项足以使他“蒙羞”的刺杀。两个充满个人理想的人迎头相撞,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成为令人感伤不已的悲剧。与奥栢伦相似的,是凯撒与布鲁图斯的死亡方式。当凯撒看到布鲁图斯站在行凶者的中央,他放弃了抵抗,以血布掩面,静待临终;当布鲁图斯看到共和派在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夹攻下大势已去,他命仆人操起刺杀过凯撒的匕首,呼唤着凯撒的名字,刎颈而亡。此处虽然不排除莎士比亚的写作揉入了一些个人的情感偏好,但作为英雄的死亡方式,依旧足以震撼阅读者的心灵。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目睹过罗马;但是每个人,都正在并且终将归于死亡。而莎翁伟大的地方,正是以死亡带给每个人物真正的平等,又以面对死亡的态度来赋予另一些人物伟大。所以,无论是凯撒还是布鲁图斯,都难言是屋大维式的胜利者;而屋大维式的胜利者,却无资格与荣誉妄自评论那两位“最后的罗马人”。
所以,死亡带给每一个个人的平等,是他将在世俗的法庭与心灵的法庭接受双重审判,互为一种接近于正义存在的补充。然而,在死亡之前,同等重要的,是对于生的态度。贡斯当曾言,古代人的自由是公共事务的自由与个人事务的压迫之混合物,现代人的自由则是公共事务的压迫与个人事务的自由之中和物。个人自由,是捍卫人类灵魂神圣不可侵犯之域最强有力的自然基础,也往往成为逃避公共责任与灵魂谴责的自我解嘲。作为个人行为基础源泉的“理性”,在中国无限度文化压迫却并无等量中立制度救济的社会生态中,被异化成巨大而丑陋的畸形恋物,尚不及我们常常无法理喻的落后部落中之生殖器崇拜来得纯粹。在情怀缺位的世界里,单向度的标准管控着从商品到灵魂的自我生产,难以为其他语系留存一个自我表达的空间。比如一名教师在地震中抛下学生逃走,似乎能够以“个人自由”(虽不详知其对个人自由的理解为何)作为行动的正义佐证,但希望其能铭记世界尚存在“职业道德”与“良心”等并行的价值语系,若有时间自我辩解是否更应花时间自我沉默与自我忏悔?;又比如复旦教授谢百三为投毒案的犯罪者求从轻判处,其自我行为的感召似乎是在于为中国废除死刑立法而抗争。然而如此崇高的目标之下,其对待学生签名上吁过程中种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其事发后以“未料及事态发展如此之大“态度令人困惑的担当,选择忽略林森浩作为医生身份进行实验品投毒的谋杀方式,以及最令人无法理喻,是如此目的高尚之下却逻辑推演拙劣毫无现代司法困境启示意义的求情书……如果真心对黄洋和林森浩包含珍重其生命如此高贵的价值预设,而不是仅求哗众取宠,那么是否能理性而周全地赋予更与之匹配的行事之道?再比如当你目见他者使用不论是刀枪还是拖把对弱势者的生命进行威胁时,站在无法相互呼应的集体行动困境中,你保全了你所相信的个人自由的同时,能不能不去夸大自己的聪慧与少数行动者的愚昧,而多一些对自身不作为的反思?假设你现在作为最后的决定者,去选择是否击落一架被劫持撞向民用目标的客机,在以少数人的代价而换取多数人的安全之后,你是否会自觉胜利并欢心鼓舞?我想很难,有时候你清楚你天真的行为会伤害爱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有时候你清楚你自认的英勇很可能为法律与正义的价值所不容,有时候你清楚诸如“权衡利弊”“整体利益”“多数人的幸福所在”一系列概念构造,可就是无法对眼前触手可及生命的逝去,如此坦然的视而不见……我并非站在一种不可仰望的高度批判一些人,只是仅仅希望站在他或她的面前,告诉他们:看到与你们不同的另一种人,请不要嘲笑他愚蠢;看到与你们不同的另一理解,请不要双手推开,然而视而不见。
罗马已经离我们远去。当西方以近代国家和普遍主义的混沌之姿进入以外的世界,构筑了现代性迷惘的根本之义。“先进—落后”的历史叙事,理性主义的勃兴,与自由民主话语构建,在推动着世界文明步入新的伟大时代的同时,也因其类同质化的过程而产生了不可抗的毒性。从泰勒斯到圣奥古斯丁,从边沁到伯林,从哈耶克到罗尔斯,伟大的哲学家们都自负“出埃及记”式的先知使命,但普遍主义理解显然比埃及的综合生态要恶劣许多。以多元容纳之姿进入现代语系中的民主价值,却杂糅了“上下”同“敌我”认同的理解方式,在一国传统文化制度压制之下尚能较为理想的运转,若无此点便会放大毒性。东亚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峙僵持,很大原因便是如此。安全化的环境压迫之下,难以自我思考便投身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谈何以生命与命运透支为代价为“他者”预支话语与行动的空间?想来必是尤为困难了。然而,我觉得多一种理解角度,并不妨碍秉持自己的道路。就像最近外交部发言人以“中国早就做过世界老大”反击美国霸权之姿洋洋得意,又是否转换角度,清楚理解一个国家真正的生命所在?浅层次说,中国五千年的断裂历史叙事尚无法与美国名为两百年实似传承罗马千年精神的政治肌体横相睥睨,地区朝贡体制的世界性意义同样尚需论证;而作为一种世界和地区霸权,其责任担当远远超过其力量挥霍,并非心有所想便事有所成。问题的一题两面,接受政治或私利的断裂解释与蒙蔽试听,便易于走向了误区与迷惘。毫无疑问,当从个体到标准都在自视甚高,现代的迷惘,便是在如此汲汲追求普遍主义式的自我确证,却以“进步—落后”、“非此即彼”式的独断叙事代入而成,并未对世界无穷尽的多样性现实给予一丝温情的宽容。而我想象中的那个罗马,那种真正的自由,乃是一种过程。它并非急不可耐地以独我标准去取代他者,而是闭嘴、聆听、思考、交流、反证一系列动作与谨慎的组合。没有人能界定自由的具体形态与精神所在,但自由一定是发生并生长在这样的过程中。
三岛由纪夫曾言:“一双手拥抱人生,一双却触及永远,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在人生无数闪过的镜头中,总是被追问相似的问题:“你做这件事有什么用?”物以致用,学以致用,无所不“用”其及。我想起亲爱的奥柏伦,满含热泪的凯撒,眼神坚毅的布鲁图斯……他们大概也会无言以对。一如我心中的罗马,有何种用途,是什么概念?它不能吃,也不能骑,写成论文发表不了,连自慰都不如有码无码……可人类或许需要它才能“活”下去。罗马是一种想象,一种忘却,一种忧郁。或许是因为远离,你才觉得它瑰丽唯美不可言喻……好吧,请不要嘲笑或者戏谑这份想象、忘却以及情怀,请你先靠近它,看着它,思索它。让它苟且但无畏地活下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