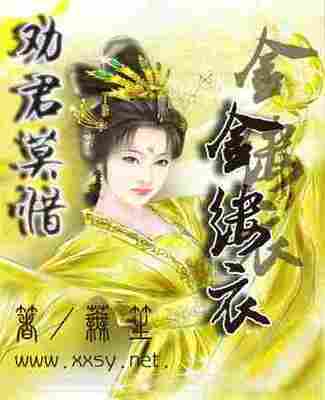——顾梁汾《金缕曲•赠吴汉槎》之一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偢。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催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顾梁汾《金缕曲•赠吴汉槎》之二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琢,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纳兰容若《金缕曲•赠顾梁汾》
顾梁汾,名贞观,清代文学家,曾祖顾宪成是晚明东林党人领袖,家族为无锡名门望族。梁汾禀性聪颖,幼习经史,尤喜诗词,结“云门社”于家乡惠山,会聚诸多江南名士,并与吴江才子吴汉槎结为生死之交。康熙五年中举,官至内阁中书。康熙十年,受同僚排挤,落职归里。康熙十五年,与纳兰容若相识,交契笃深,二人曾合力营救以“江南闱科场案”蒙冤而被流放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的吴汉槎,并有赎命词《金缕曲》相和,一时轰动朝野。
吴汉槎,名兆骞,生于官宦之家,少年时即声震文坛,恃才放旷,常拿同学的帽子小便,说,与其放在俗人头上不如给我做溺器。年岁及长越发狂傲,曾对好友夸口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顺治十四年考中举人,后来朝廷发现吴中考场大有弊端,于是皇帝命令把考中的举人们全部缉拿进京,批枷上锁参加复试,“令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押赴菜市口刑场无异”。科考作弊本与吴汉槎无关,但他向来娇宠,哪里受过如此非遇,惊吓中竟战栗不能握笔,未把文章写完(一说是惊怒之下负气交白卷),结果以“不学无术”获罪,杖责四十,家财充公,与家人一起发配到宁古塔戍边。
作为挚友,梁汾为吴汉槎蒙受不白之冤感到怨痛,立下“必归季子”的誓言,遍求满朝权贵,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但清人入关伊始,正想借此毁灭江南文气,压制文人们高涨的斗志,此案件为顺治亲定,是一件株连极广的敏感政治大案。多年过去,顺治换成了康熙,康熙虽然通晓吴汉槎的文名,有赦免之意,却也不能翻案。
后来梁汾接到吴汉槎从戍边寄来的信:“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镝呼风,哀笳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梁汾读罢,凄然泪下,深怜身处绝塞的吴汉槎所受的雨雪风霜摧残,救他生还已是刻不容缓,因而连日奔走于权贵之门,但仍毫无希望。近乎绝望的梁汾挥笔写下了两首《金缕曲》,悲之切,慰之深,无一不是肺腑之言。
康熙十五年,权相明珠慕梁汾才名,聘请他为其子纳兰容若授课。容若与梁汾意气相投,遂成忘年知交。此时梁汾为救吴汉槎奔波已近二十个年头,他以两首《金缕曲》示之容若,容若读过后泣下数行,也作《金缕曲》一首赠之,肝胆相照。但容若深知此事不易办,许诺十载为期,曰:“何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需兄再嘱之”。

可是,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梁汾恳求以五年为期,容若再次应允。其后,在梁汾的鼎力相助下,纳兰父子与徐乾学等人从朝中斡旋,以千金赎之,吴汉槎本人亦献《长白山赋》取悦皇帝,终于在康熙二十年被放归。吴汉槎被释归来后,不久因一些小事与梁汾生出嫌隙,梁汾亦不辩解。一日,吴汉槎到明珠府上拜谢,在一房间内壁上,见到题字:“顾梁汾为松陵才子吴汉槎屈膝处”,方知梁汾给他的是云天高义,不由愧恸难当。
吴汉槎虽然绝塞生还,却已年过半百,不复是当年的轻狂公子,苦历经了二十年多苦寒的边塞流放,费尽了多少友人心血的搭救,竟不适江南的温软气候,三年后心神俱疲一病成终。容若为其料理事后事,抚恤孤寡。康熙二十四年暮春,在一个风雨相摧的葬花天气,容若英年早逝,梁汾在讣词中感叹“此其知我之独深,亦为我之最苦”,次年,梁汾黯然归隐故乡,发誓从此“不复拈长短句”。
斯人已去,留于后世的是顾梁汾与纳兰容若《金缕曲》的文采风流,从见古人重义守诺,友道之厚。而顾梁汾自己曾说,吾词独不落宋人圈套,可信必传。此言不虚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