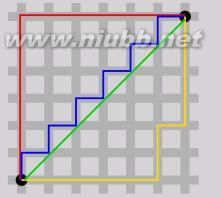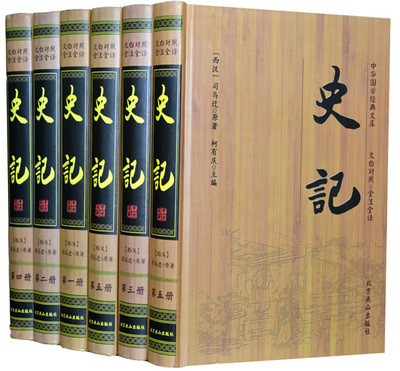地主之殇
--土家野夫(有删节)
----------------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的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石板村被派驻进一位姓宋的干部,他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祖父哪里知道最高指令要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了。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新社会。但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3000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