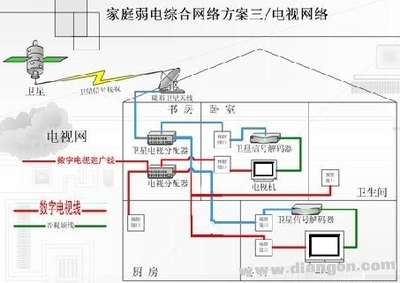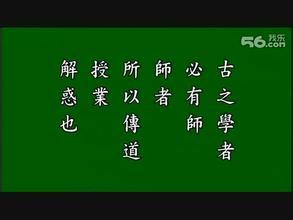(一)未遂犯和不能犯的概念
按照我国目前的通说,所谓未遂犯,是法定的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的一种,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况;而不能犯并不是法定的概念,而只是刑法理论上用来对未遂犯进行分类的一种概念。一般认为,所谓不能犯未遂是指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因所使用的工具、方法不当,或犯罪对象的不存在,因而犯罪未能得逞。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不能犯未遂的情况之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客观上具有该种犯罪故意支配下的行为,虽其行为不能发生犯罪结果,但仍具备了犯罪构成主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本质上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须负未遂犯的刑事责任。但是,上述学说,近年来已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认为,首先,上述观点将客观上完全不可能侵害法益的行为也成立犯罪未遂,不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其次,上述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只要行为人对实行行为有认识(有故意),不管客观上有无实行行为,都认为有危险,这实际上是主观归罪;再次,上述观点将客观上完全没有危险性的行为,仅因为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就被作为犯罪来处罚,必然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
最后,通说一方面认为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又认为行为人误将尸体当作活人而射杀时不存在犯罪客体,因而成立故意杀人未遂,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基于上述主张,上述观点的论者认为,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罪过,其客观上实施的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时,才能认定为犯罪未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其客观行为没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任何危险时,就应认定为不可罚的不能犯即无罪。至于客观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则应以行为时所有的客观事实为基础,站在行为时的立场,根据客观的因果法则进行判断。
我国现行通说对不能犯和未遂犯的理解上存在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以及犯罪构成理论,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观要件的结合。首先,在客观方面,必须有危害行为,即对受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律利益具有现实的危害或危险的行为。如果行为本身并不足以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或法律利益造成现实的危险或威胁的话,该行为就称不上是危害行为;
其次,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刑法分则中的某种犯罪所规定的主观要件。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刑法也是秉承了近代刑法所坚持的行为刑法(而不是行为人刑法)的特点,因此,在主客观要件的关系上,应当说,行为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起主导作用。换句话说,行为人仅有恶的意图,而没有实施足以危害社会的危险的行为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认定其有罪。而我国目前有关未遂犯和不能犯的通说恰好在这一点上有问题,将一些从一般人看来完全不具有危险或不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也看作为犯罪(未遂),这显然是不适当地扩大了刑法的处罚范围。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同意上述论者的批判意见。但是,对上述论者所提出的行为的危险性的判断标准的见解,笔者却持有不同见解。实际上,这一问题涉及到国外刑法学争论日久的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分标准以及对刑法中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评价问题。
(二)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区分
1.有关区别标准的学说。在刑法学上,关于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区分标准,历来有客观的危险说、主观说、抽象的危险说、具体的危险说之争。
(1)客观的危险说。客观的危险说,也叫绝对不能、相对不能区分说,认为不能犯之中,有一般来说,根本不可能实现犯罪的场合,和由于有特殊情况的存在,所以,不可能实现犯罪的场合之分。的场合是绝对不能,所以是不可罚的不能犯,的场合是相对不能,所以是应当受到处罚的未遂犯。作为属于这种学说的见解之一,有将不能犯分为对象不能和方法不能的见解,并认为只有方法相对不能的情况才是未遂犯,而其他情况都是不能犯。所谓对象的绝对不能,如把死人当活人而开枪的场合,所谓对象的相对不能,如为了杀人而向他人宿舍的床上开枪,但碰巧对方外出的场合。所谓方法上的绝对不能,如出于毒杀的目的而让他人喝糖水的场合,所谓方法的相对不能,如出于杀人的意思而开枪,碰巧行为人的枪里没有子弹的场合。客观危险说,在德国是自费尔巴哈以来的学说,又称为旧客观说,在以行为和行为后所判明的全部客观事情为判断基础,以裁判时为标准,从事后的、客观的立场来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危险的一点上有其特点。
(2)修正的客观说。修正的客观说,以所有的客观事情为判断基础,主张在行为没有发生利益侵害的场合,作为现实存在的事实的替代,考虑在存在什么样的事实,在科学法则上,就会发生侵害利益的结果,从科学的一般人的立场出发,以假定事实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存在为基准,在事后对危险性进行判断。
(3)主观说。主观说认为,只要将实现犯罪的意思表现为行为,不问该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都成立未遂犯。但又认为迷信犯,由于没有真正的犯罪意思,只是单纯地表明希望而已,或者是由于行为人性格懦弱不具有性格的危险性等理由,所以应该是不能犯。
(4)抽象的危险说也称主观的危险说,它以行为人的犯罪意思的危险性为出发点,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认识的事实为基础,从客观的角度来判断有无危险,即从一般人的立场来看,如果按照行为人的计划向前发展,就会有发生结果的危险的话,就是未遂;如果没有危险的话,就是不能犯。
例如,在出于杀人的目的而让他人喝下肠胃药的场合,如果行为人误认为肠胃药是农药的话,因为让人喝农药,一般来说,具有发生结果的可能性,所以是未遂犯;但是,如果是误以为肠胃药可以杀人的话,就是不能犯。抽象的危险说,只以行为人的犯罪意思中所认识到的事实为判断危险的基础,认为其对法秩序具有抽象的危险,所以,又称为行为人危险说。
(5)具体的危险说。具体的危险说,以行为当时一般人所认识到的事实、以及行为人所特别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以行为时为标准,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考虑在该种情况之下实施行为,是否能够实现构成要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就认为有发生结果的具体危险性,构成未遂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就成立不能犯。
客观的危险说将事后所认识的事实也列入考虑之内,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危险性的判断,相反地,具体的危险说在将判断基础限于行为当时一般人所能认识到的事实以及行为人所特别认识到的事实,以行为时为标准,来判断行为有无危险。如,在行为人误以为死尸是活人而用日本刀刺其心脏的场合,按照客观的危险说以及修正的危险说的话,对死尸的杀人行为是对象的绝对不能犯,所以是不能犯。但是,按照具体的危险说的话,在行为人以外的一般人也认为该尸体是活人的话,就是未遂犯;在一般人看来也是死尸的话,就是不能犯。
2.学说的探讨。上述有关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分标准的学说,实际上涉及到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作为犯罪客观要件的危害行为的认定问题。
我国刑法学的通说认为,危害行为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危害。凡行为造成了社会危害,并且这种危害已经达到了刑法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就被认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社会危害性。但问题是,行为人所实施的某种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性,即是否足以对现实的社会关系造成危害或危险,同用以判断危险性的事实依据,以及用以衡量危险的有无及其大小的标准是密切相关的。如人食用了少量硫磺粉是否具有死亡的危险?根据一般人的观点,硫磺是对生命有害的物质,所以能肯定此时存在侵害生命的危险,也即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根据专家的判断的话,则可能会否定该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科学证明,少量硫磺并不足以剥夺人的生命。
我们认为,刑法学中的危险只能是社会一般人所理解的危险。理由是:虽然刑法中的犯罪必须以实际侵害或足以侵害法益的行为为限,但是,刑法保护法益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除了对侵害法益的行为即犯罪行为的惩罚之外,更主要地是通过事先明确规定犯罪和刑罚,向社会一般人提供行动的准则和指南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对于刑法上的观念或内容的理解,不能脱离一般人的理解,否则,通过罪刑法定来为一般人提供行动的指南的理念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时,刑法规范是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复合体。所谓行为规范是指禁止人们为一定的有害行为或命令人们得为一定的有益行为的法。如果人们没有遵守一定的命令或禁止规范,被判定为违法,就会给予其一定的制裁,这便是裁判规范。刑法一经公布,便是一旦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会被处以某种刑罚的表现,其中包含着国家国家禁止人们实施某一行为的强烈愿望。一般人意识到这一愿望并依此采取行动,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极为自然的。因此,刑法在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判断标准的裁判规范之前,首先应看成是一般人预测自己行为后果的指南的行为规范。
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于刑法中的规定的意义的理解,首先必须以社会通常观念即一般人的理解为标准来判断。根据以上立场,我们认为,以上各种有关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分标准的学说之内,客观的危险说,将科学的危险作为前提,从刑法规范首先是行为规范的角度来看,难以支持,另外,在不能明确区分绝对不能和相对不能一点上,具有致命的缺陷,因此,难以支持。修正的客观说,试图以科学的危险性为中心进行考虑,但是,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如前所述,是从社会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具否具有危险性的情况,因此,这种学说也不妥当。主观说是由来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学说,按照主观主义的话,迷信犯也应当受到处罚,但是,该种学说却将它作为不能犯,这意味着该种学说自身并没有彻底贯彻主观主义的主张,因此,即便支持这种学说也是不妥当的。抽象的危险说,为了纠正主观说的缺陷,将危险性的内容作为犯罪实现的危险性客观地进行把握,但是,对该危险性的判断,仅以行为人的认识内容或计划内容为基础,所以,也并没有逃出主观主义的范围。从这一意义上讲,从一般人的立场来判断行为的客观危险性的具体危险说是妥当的。同时,即便是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并不危险的行为,例如,在一般人看来是稻草人,但行为人本人知道是真人而向该人开枪的话,就应当说具有发生结果的现实危险,所以,行为人特别认识到的情况也应当作为判断的基础。这么说来,不能犯中危险性的判断的有无,应以行为人特别认识到的事实以及一般人能够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以行为时为基准,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认为具有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危险性的场合,就是未遂犯;没有的场合,就是不能犯。
关于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的判断,有应当以科学的一般人为标准进行判断的见解,和应以社会的一般人即普通人为标准进行判断的见解,之间的对立。见解,是以刑事诉讼法中设立的鉴定人制度为根据的制度,但是,不能犯中的危险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物理的危险性自身,而是一般人所具有的恐惧感,是社会心理的危险性,因此,它虽然以科学的、物理的危险性为基础,但最终仍要以社会上的一般人即普通人为标准来进行判断,所以,的见解妥当。因此,随着一般人的科学知识的提高,未遂犯和不能犯之间的界限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四、结 论
根据上述见解,上述被告人的第二个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
本案中,陈新将杨红抱进自己的猪屋时,可以肯定并不确知杨红是死是活。不然,就不会出现“第二次进猪屋时,见杨仍躺着未动,即解散一捆稻草盖在其身上”之举,更不会实施:“怕杨又活了,顺手拾起一块大石头向杨的头部砸去,并用一块石磨压在杨的身上“的行为;而且,就上述案例所交代的情况来看,一般人也都会认为杨红还活着(因为当事人陈新“好像见覆盖的稻草动了一下”),或者至少不能确切肯定杨红已经死亡。在这种在行为人实施杀人行为的当时,一般人和行为人本人都相信被害人可能还活着的情况下, 出于杀人的故意而实施了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显然是完全符合刑法中所规定的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的,成立故意杀人罪。只是,由于从事后的判定来看,在行为人实施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的当时,被害人已经死亡,即出现了被告人意志以外的、不可能实现故意杀人罪的犯罪结果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本案中,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未遂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