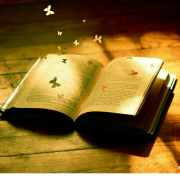#千里共良宵#腊八,北京的气温降到了入冬以来的又一个低点,干燥的空气里却没有要飘雪的迹象。冬天了,你在哪呢?你那里下雪了吗?…
【节目歌单及文章】
背景音乐:《彩云之南》林海
背景音乐:《TrueLove》(Instrumental)(日剧《爱情白皮书》配乐)
第一首:《北极雪》陈慧琳&冯德伦
第二首:《Snow》梁晓雪
第三首:《认真的雪》薛之谦
第四首:《雪人》范晓萱
第五首:《宁静雪》张信哲
第六首:《两个人的下雪天》许慧欣
第七首:《下雪》阿杜
第八首:《两个下雪的夜》尚雯婕
第九首:《雪の华》(雪之花)中岛美嘉
文章一:《雪的印记》文/小钊
文章二:《寒风吹彻》文/刘亮程
文章三:《你那里下雪了吗?》文/章元
文章四:《世界尽头》文/村上春树
文章一《雪的印记》
文/小钊
在刚刚过去的农历腊月初八,北京的气温降到了入冬以来的又一个低点,可惜的是空气干燥,丝毫没有要飘雪的迹象。冬天了,你那里下雪了吗?
从小在南方生长的我,雪对我来说是稀罕的。搜索记忆,依稀记得在很小很小还需要大人抱着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的故乡下过一场雪。
其实,已经没有记忆了,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姥姥抱着我在屋顶上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好像是小学一、二年级吧,应该是二年级的时候,那应该算是我此生记忆当中第一场清晰的雪,下得也足够大,雪花大片大片,真的像是羽毛一样,并且落在并没有马上融化,积雪在我们居住的区域停留了一两天。
那天是那么的兴奋,以至于学校都有一段时间暂停了上课,让大家出门到户外去玩雪。但从那以后,我的故乡就再也没有看见雪落下了,谁让我们是南方呢?在我的记忆当中,下雪的冬天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美丽,当雪落下,一切都干干净净,散发着冬天特有的亮光。
于是,后来我来到北京,来到这一座北方的城市,期盼着每年冬天的瑞雪落下,只是并不是每年都如愿。在我来到北京的十几年当中,好像真有那么一两年似乎是没怎么见着雪花的影子,但愿今年别这样吧!
文章二《寒风吹彻》
文/刘亮程
雪落在那些年雪落过的地方,我已经不注意它们了,比落雪更重要的事情开始降临到生活当中。三十岁的我,似乎对这个冬天的来临漠不关心,却又好像一直在倾听着落雪的声音,期待着又一场雪悄无声息地覆盖村庄和田野。
我围抱着火炉,烤热漫长一生的一个时刻。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就在前一天,我似乎已经预感到大雪来临。我劈好足够烧半个月的柴禾,整齐地码在窗台下;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无意中像在迎接一位久违的贵宾--把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扫到一边,腾出干净的一片地方来让雪落下。下午,我还走出村子,到田野里转了一圈。我没顾上割回来的一地葵花秆,将在大雪中站一个冬天。每年下雪之前,都会发现有一两件顾不上干完的事情,被搁一个冬天。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年的事情,像我一样用自己的那只冰手,从头到尾地抚摸自己的一生。
屋子里更暗了,我看不见雪。但我知道雪在落,漫天地落。落在房顶和柴垛上,落在扫干净的院子里,落在远远近近的路上。我要等雪落定了再出去。我再不像以往,每逢第一场雪,都会怀着莫名的兴奋,站在屋檐下观看好一阵,或者光着头钻进大雪中,好像有意要让雪知道世上有我这样一个人,却不知道寒冷早已盯住了自己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
经过许多个冬天之后,我才渐渐明白自己再躲不过雪,无论我蜷缩在屋子里,还是远在冬天的另一个地方,纷纷扬扬的雪,都会落在我正经历的一段岁月里。当一个人的岁月像荒野一样敞开时,他便再无法照管好自己。
就像现在,我紧围着火炉,努力想烤热自己。我的一根骨头,却露在屋外的寒风中,隐隐作疼。那是我多年前冻坏的一根骨头,我再不能像捡一根牛骨头一样,把它捡回到火炉旁烤熟,它永远地冻坏在那段天亮前的雪路上了。
那个冬天我十四岁,赶着牛车去沙漠里拉柴禾。那时,一村子人都是靠长在沙漠里的一种叫梭梭的灌木取暖过冬,因为不断砍挖,有柴禾的地方越来越远,往往要用一天半夜时间才能拉回一车柴禾。每次拉柴禾,都是母亲半夜起来做好饭,装好水和馍馍,然后叫醒我,有时父亲也会起来帮我套好车,我对寒冷的认识是从那些夜晚开始的。
牛车一走出村子,寒冷便从四面八方拥围而来,把你从家里带出的那点温暖搜刮得一乾二□,让你浑身上下只剩下寒冷。
那个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
只是这次,是我一个人赶着牛车进沙漠。以往牛车一出村,就会听到远远近近的雪路上其他牛车的走动声,赶车人隐约的吆喝声。只要紧赶一阵路,便会追上一辆或者好几辆去拉柴的牛车,一长串,缓行在铅灰色的冬夜里。那种夜晚,天再冷也不觉得,因为寒风在吹好几个人,同村的、邻村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好几架牛车,在这条夜路上抵挡着寒冷。
而这次,一野的寒风吹着我一个人,似乎寒冷把其他一切都收拾掉了,现在全部地对付着我。
我掖着羊皮大衣,一动不动趴在牛车里,不敢大声吆喝牛,免得让更多的寒冷发现我。从那个夜晚,我懂得了隐藏温暖--在凛冽的寒风中。身体里那一点点温暖,正一步步退守到一个隐秘的有时连我自都难以找到的深远处--我把这点隐深的温暖节俭地用于此后多年的爱情生活。我的亲人们说我是个很冷的人,不是的,我把仅有的温暖全给了你们。
许多年后有一股寒风,从我自以为火热温暖的从未被寒冷浸入的内心深处阵阵袭来。当这阵寒风袭来后,我才发现穿再厚的棉衣也没有用了,生命本身有一个冬天,它已经来临。
天亮的时候,牛车终于到达有柴禾的地方。我的一条腿却被冻僵了,失去了感觉。我试探着用另一条腿跳下车,拄着一根柴禾棒活动了一阵,又点了一堆火烤了一会儿,勉强可以行走了。腿上的一块骨头却生疼起来,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疼,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又狠命往骨髓里钻--这种疼感一直延续到以后所有的冬天,以及夏季里阴冷的日子。
天快黑的时候,我装着半车柴禾回到家里,父亲一见就问我:“怎么拉了这点柴,不够两天烧的。”我没吭声,也没向家里说腿冻坏的事。
我想,那个冬天要是稍短些,家里的火炉要是稍旺些,我要是稍微把这条腿当回事些,或许我能暖和过来。可是,现在不行了。隔着多少个季节,今夜的我,围抱火炉,再也暖不热那个遥远冬天的我;那个在上学路上不慎掉进冰窟窿,浑身是冰往回跑的我;那个跺着冻僵的双脚,捂着耳朵在一扇门外焦急等待的我……我再不能把他们唤回到这个温暖的火炉旁。我准备了许多柴禾,是准备给这个冬天的。我才三十岁,肯定能走过冬天。
但是,在我的周围,肯定有个别人不能像我一样度过冬天。他们被留住了,冬天总是一年一年地弄冷一个人,先是一条腿、一块骨头、一副表情、一种心青……而后是整个人生。
我曾经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把一个浑身结满冰霜的路人让进屋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带着许多个冬天的寒冷,当他坐在我的火炉旁时,炉火须臾间变得苍白。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在火炉的另一边,我感到迎面逼来一个老人的透骨的寒气。
他一句话不说。
我想,他的话肯定全冻硬了,得过一阵才能化开。
大约坐了半个时辰,他站起来,朝我点了一下头,开门走了。我以为,他暖和过来了。
第二天下午,听人说村西边冻死了一个人。我跑过去,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躺在路边,半边脸埋在雪中。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被冻死。
我不敢相信,他已经死了。他的生命中肯定还深藏着一点温暖,只是我们看不见;一个最后的微弱挣扎我们看不见;呼唤和呻吟我们听不见。
我们认为他死了,彻底地冻僵了。
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靠什么去留住。他的烂了几个洞、棉花露在外面的旧棉衣?还是,底磨得快透了一边帮的已经脱落的那双鞋?还有他的比多少个冬天加起来还要寒冷的心境?我们都看不见……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我有一个姑妈,住在河那边的村庄里,许多年前的那些个冬天,我们兄弟几个常手牵手走过封冻的河去看望她。每次临别前,姑妈总要说一句:天热了让你妈过来待一待。
姑妈年老多病,她总担心自己过不了冬天。天一冷,她便足不出户,偎在一间矮土屋里,抱着火炉,等待春天来临。
一个人老的时候,是那么渴望春天的来临。尽管春天来了她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要半瓣将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中,但她还是渴望春天,她害怕寒冷。
我一直没有忘记姑妈的这句话,也不只一次地把它转告给母亲。母亲只是望望我,又忙着做她自己的活。母亲不是一个人在过冬,她有五六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要拉扯着他们度过冬天,不让一个孩子受冷。她和姑妈一样,期盼着春天。
天热了,母亲会带着我们,趟过河,到对岸的村子里看望姑妈。姑妈也会走出蜗居一整个冬天的土屋,在院子里晒着暖暖的太阳和我们说说笑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春天,好像姑妈那句话中的“天”一直没有热起来。
姑妈死在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回家过年,记得是大年初四,我陪着母亲沿一条即将解冻的马路往回走,母亲在那段路上告诉我姑妈去世的事。她说:“你姑妈死了。”
母亲说得那么平淡,像在说一件跟死亡无关的事情。
“咋死的?”我似乎问得更平淡。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说:“你大哥和你弟弟过去帮助料理了后事。”
此后的好一阵,我们再没说这事,只顾静静地走路。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母亲说了句:“天热了。”
我抬头看了看母亲,她的身上正冒着热气,或许是走路的缘故,不过天气真的转热了。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冬天已经过去了。
“天热了,过来···”我又想起姑妈的这句话。这个春天再不属于姑妈了,她熬过了许多个冬天,还是被这个冬天留住了。我想起爷爷奶奶也是分别死在几年前的冬天,母亲还活着,我们在世上的亲人会越来越少。我告诉自己,不管天冷天热,我们都要常过来和母亲坐坐。
母亲拉扯大她七个儿女,她老了,我们长高长大的七个儿女,或许能为母亲挡住一丝的寒冷。每当儿女们回到家里,母亲都会特别高兴,家里也顿时平添热闹的气氛。
但母亲斑白的双鬓分明让我感到她一个人的冬天已经来临,那些雪开始不退、冰霜开始不融化--无论春天来了,还是儿女们的孝心和温暖备至。
隔着三十年这样的人生距离,我感觉着母亲独自在冬天的透心的寒冷,我无能为力。
雪越下越大,天彻底黑透了。
我静坐在屋子里,火炉上烤着几片馍馍,一小碟咸菜放在炉旁的木凳上,屋里光线暗淡。许久以后,我还记起我在这样的一个雪天,围抱着火炉,吃咸菜啃馍馍想着一些人和事情,想得深远而入神。柴禾在炉中啪啪地燃烧着,炉火通红,我的手和脸都烤得发烫了,脊背却依旧凉飕飕的,寒风正从我看不见的一道门缝吹进来。冬天又一次来到村子里,来到我的家。我把怕冻的东西一一搬进屋子,糊好窗户,挂上去年冬天的棉门廉,寒风还是进来了,它比我更熟悉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缝。
我围抱着火炉,烤热漫长一生的一个时刻。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文章三《你那里下雪了吗?》
文/章元
仝童吃着苹果走进这所全市最著名的高中,门口负责迎接新生的高年级男生看了她一眼,她伸了伸舌头,迅速把手藏到身后。
布告栏上登着每个人被分配到哪个班,仝童望着那黑压压的一片脑袋,远远地站在人圈外悠闲地继续啃苹果。一个男生用好听却又高八度的声音,指着一个名字跟旁边的人说:“你看这个人的姓多怪啊!‘人工’?是不是写错了?这人姓‘全’吧?”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女生用很小声却很清晰的声音纠正说:“那个字念tóng!”
说话的女孩就在仝童的身边,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仝童看着她,苹果放到嘴边,竟然忘了吃。
这个女孩实在是太美了!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嘴唇、还有她那条淡蓝色的裙子,没有一处不彰显着她的美丽。那种美丽,高不可攀,世界上真的有那样的完美吗?
男生也回过头来,寻找着说话的人,仝童的目光落在男生的脸上。他很高,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白色的棉布衬衫,桀骜不驯的眼睛装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愤怒。他的眼睛扫到淡蓝美人的脸上,那抹愤怒即刻消失了,甚至还有一点点惊慌、一点点害羞,和一丝不知所措的柔情。
站在旁边的仝童似乎明白了什么,心里涌上一股怪怪的感觉。为什么那个男孩的眼睛扫过自己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为什么那感觉就像雪花飘到脸上,融化了,留下那么一丝凉意,一点失落,自己却还不忍心怪到雪花头上?
他一定没有见过真正的雪吧?仝童想。这里怎么可能下雪呢?只有北方才有雪啊!可是,我为什么会想到雪呢?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错别字男生叫齐宇,坐在最后一排,距离仝童两米半,这是仝童后来无数次用鞋子测量过的距离。淡蓝美人叫李维维,坐在仝童的旁边。齐宇距离李维维两百八十公分,这是齐宇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对仝童说起的一句话。
“仝童,你和李维维换一下吧!老师不会看出来的!”齐宇总是这样恳求她。
“我为什么要换座啊?我不!我就不!”仝童负气地把自行车骑得更快了。
“仝童,你就换一下吧!换一下就近了三十公分呢!我立定跳远就能跳过去了。两米八,我实在跳不过去啊!”齐宇追上来说。
“那你自己找老师说去,让我和你换座,那样你们离得不是更近了吗?”
齐宇不明白,仝童不是他的“哥们儿”吗?怎么连换个座的小忙都不帮呢?
转天,仝童在操场练长跑的时候,赫然发现几乎天天踩着上课铃进教室的齐宇,竟早早地来到学校练习跳远。那一刻,她才明白,原来一个人为了自己喜欢的人,是什么都肯做的,即使是没有用的事情。
仝童围着操场,跑啊跑啊,脸上粘着的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累了吗?还是觉得疼痛?呼吸里为什么弥漫着酸与涩?为什么目光还在情不自禁地搜索着那个一跳一跳的身影?原来啊,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真的是什么都肯做的。
仝童和维维换了座位,齐宇望着维维的时候,目光再也不会从她身上滑过了,那束热切的目光,现在连余温也无法让仝童分享到了。
放学的时候,齐宇请维维和仝童去吃冰淇淋。理由是,由于她们调换了座位,他上课的时候视线再也不受阻隔了。但仝童知道,那是齐宇的借口,可她还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极力怂恿维维一道前去。
有时候,仝童会盯着化学老师的背影问自己:“我这是在干嘛啊?难道我真的是喜欢他么?如果不是,知道他喜欢维维的时候,我心里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呢?如果是,那我为什么还要帮助他追维维?”
冰淇淋店里,齐宇问她们喜欢什么口味的。维维说香草,仝童说苹果,于是齐宇捧回了三个香草冰淇淋。望着齐宇手里毫无分别的冰淇淋,仝童的心一点一点地塌陷。
她说不出来那冰淇淋是什么滋味,应该很甜吧?不然维维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仝童静静地看着他们,找不到自己继续坐在这里的理由。一个是篮球队长,一个是超级校花,他们的学习成绩永远霸占着年级的前两名。自己又算什么呢?连丑小鸭都算不上!丑小鸭还有变成白天鹅的那一天呢,维维也是喜欢齐宇的呀,维维脸上的红晕就说明了一切,自己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呆下去呢?
可是,仝童还是坐在那里,像个傻瓜,吃着平生最难吃的冰淇淋。酸的、苦的、无望的,还有那么一丁点靠想象才能感受到的模糊的幸福。他坐在她们对面,齐宇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而维维正感受着那炽热的光芒。仝童心里明白,那光芒不属于她的光芒。
为了这束光芒,她愿意痛一点,痛一点,再痛一点!她相信自己足够坚强。
在这样一所名校里,禁止早恋是被写进校规的,齐宇和维维的恋情只有仝童一个人知道。仝童好像是他们的救世主,也是他们的通讯员,同时也是他们的挡箭牌。他们之间无论有什么事都靠仝童传递,即使放学回家也是三个人一起走。
“真好笑啊!这到底是几个人在谈恋爱啊?”每次把维维送回去之后,仝童都要这样抱怨一下。
“为朋友两肋插刀!全童,这话你总听说过吧?”维维不在的时候,齐宇是爱开玩笑的,他总是故意把仝童的名字叫错,逗仝童生气。维维一出现,齐宇就像换了一个人,变得那么拘谨,那么小心翼翼,拿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好像生怕配不上维维的高雅和美丽。仝童喜欢松弛下来的齐宇,她觉得那样的他才真实。
其实,仝童又和齐宇有多大的差别呢?愿意为一个人做很多事,甚至愿意改变自己,委屈自己,隐藏自己的感情。喜欢一个人是很辛苦的,而把这份喜欢掩藏得滴水不漏,就更加辛苦了。
寂静无人的教室,把课桌椅搬开,用鞋子量出他们之间的距离。一共是十二脚,比原先多了不到一脚半。但仅仅一脚半的距离,却已经远过了天涯海角。
高二的时候,维维选了文科,齐宇和仝童继续呆在理科班。这样的日子对齐宇来说是一种折磨,对仝童来说就更是,她简直无法忍受齐宇只要一有空就和她念叨维维了。
仝童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属于别人的恋爱里,她究竟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高三的学生是陀螺,只会围着高考打转。大约是老师“良心发现”吧,破例决定在圣诞节这一天举行联欢会。那天,大家玩得都很高兴,从教室里出来都十点多了。
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飘起了冬雨,让人跟着一块儿心寒。没有了老师的监督,齐宇变得大胆了很多,拉着维维的手冲进雨里,笑着叫着。仝童盯着他们紧握在一起的手,觉得心变成了一张纸,被一只大手猛地攥紧,揉成一团儿丢到地上。
“仝童!你傻愣着干什么?快来呀!淋雨可好玩呢!”维维像个快乐的小天使,站在雨中冲仝童叫着。
“淋雨去喽!”不知道什么时候,齐宇已经跑到仝童身边,一把拉过她的手,把她带进雨中。仝童的身体像一只摇摇欲坠的风筝,被齐宇那么牵引着,奔向雨,奔向稍纵即逝的幸福。
就这样被他拉到了么?仝童感受着那只手传过来的温度,有一种不真切的幸福。多少个睡不着觉的夜里,她幻想过被他牵手的感觉。她以为那种感觉会很奇妙,会让她脸红心跳,会让她莫名其妙地激动上好半天,会让她甜蜜得忍不住发笑……可奇怪的是,她只是在那一刹惊了一下,没有奇妙,没有心跳,没有激动,也没有发笑。她看着他们的手拉在一起,仿佛要看着一双眼睛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真的!
这就是她的幸福了吗?
维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复旦,而仝童考到了北京——她梦想中可以看到雪的地方,只有齐宇发挥失常,留在了本市一所普通的大学里。维维安慰他,只要努力,研究生考到复旦来,她在上海等着他!齐宇却只是无所谓地笑一笑,开学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喝酒抽烟旷课追女生,还差点因为打架被学校处分。
维维给仝童的E-mail里总是写满了对齐宇的担忧与失望,她反复地问仝童,“我该怎么办?”
仝童知道,像维维那样一个走到哪里都要被人呵护、宠爱的女孩,能对齐宇这样关心,已经是难得的了。可她又能怎样呢?除了把一封封表面“正义凛然”,实际上藏满深深爱意的E-mail发到齐宇的信箱里,她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齐宇始终没给仝童回过信,连他是否收到仝童都不知道。但她就是那样固执地写着,每周两封,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一些无关风月的爱情。
北方的雪如期而至了,仝童终于有机会在雪地里撒欢儿了!雪啊雪!一个南方的小孩儿终于知道雪是什么样子的了!它没有想像中的美丽,却是那么美好。满世界全是耀眼的白色,齐宇最喜欢的白色!
“如果你看到雪,你一定会高兴起来的。整个世界都是你喜欢的白色……”仝童在E-mail里对齐宇说。
“我和维维分手了。”这是齐宇惟一的回复。
分手的理由没有任何创意,因为距离。曾经,齐宇为了短短的三十公分,那样锲而不舍。可如今六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却已经改变了一切。
寒假里见到了齐宇,问起维维,他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仝童再次在这场爱情里扮演起她熟悉的角色,她似乎已经忘掉了自己的感情,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她只希望他们可以和好。
齐宇问她:“仝童,你不觉得我很累吗?我为了喜欢她而喜欢她,我觉得我都已经不是我了!我知道你们会觉得我是受了打击,以为我堕落了,可你想过没有?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我!一个身上有各种各样坏毛病的人!我真的没有维维想的那么完美,为了她的‘完美’,我这个男朋友做得很辛苦。”
在暑假里头,齐宇和同宿舍室友到北京玩,仝童作为“地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齐宇的同学吴畏喜欢围着仝童说话,他虽然高出一届,但因为是高中校友,无形中亲密许多,他总是开仝童的玩笑:“仝童,你有没有男朋友啊?要是没有的话,仝童,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仝童根本不把吴畏的话当回事。她是有镜子的,知道自己长什么模样,这样的恭维话听起来,和讽刺没什么差别。可是有一天,当仝童换上一条雪白的连衣裙站在阳光下吃苹果的时候,齐宇忽然跑过来说:“仝童,我发现你真的变漂亮了!”
齐宇说完之后,就跑掉了,留下一个脸颊发烫的仝童。她宁愿相信是齐宇在开她的玩笑,仝童的字典里的“漂亮”永远属于别人,怎么会和自己有牵连呢?
但是,无论如何,事实还是使仝童慢慢地相信了——自己也是可以漂亮的。身边献殷勤的男生多了,吴畏的电话邮件狂轰乱炸,就连一向不回复邮件的齐宇也开始给仝童写信了。难道自己真的是一只丑小鸭吗?真的已经等到变成白天鹅的这一天了?
身边的男生,仝童总是拒绝着,说不清为什么。对吴畏,她也是淡淡地回应着,没什么热情。奇怪的是,吴畏对她的一切情况似乎都了若指掌。在圣诞节前,吴畏寄来了贺卡,里面只有一句话:让我给你幸福好吗?
仝童明白了,吴畏是喜欢她的,这种喜欢就像齐宇喜欢着维维,就像她喜欢着齐宇一样。她应该接受吗?齐宇的邮件还印在脑子里——他说,现在,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现在你才知道么?可是你知道吗?对你的好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与爱情无关了。
南方没有WhiteChristmas,在北京,仝童迎来了她生命中第一个白色圣诞节,仝童编导的小话剧在礼堂里首演成功,作为幕后英雄的她,收到了一束漂亮的玫瑰花。没有卡片,不知道送花的人是谁,嗅一嗅,闻到一股淡淡的苹果香味。是谁这么了解自己的心思?难道是齐宇吗?
玫瑰花拿到宿舍就被室友“打劫”了。电话像跟踪一样地响起来,果然是找仝童的。
“MerryChristmas!你那里下雪了吗?”劈头盖脸的就是这么一句,好半天仝童才听出这个声音是吴畏的。
“当然下了,羡慕吧?”
“还行,不是很羡慕,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浪漫。”
“你想像的?”
“快快快,打开窗子,看看下面。”
仝童疑惑地把身子凑到窗子跟前——天啊!他怎么在这里啊?雪地里站着一个小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却可以看见他奋力挥舞的手臂,难掩的兴奋。
“感动吧?我可是坐了19个小时的火车才到了这儿!”
“谁让你来了?”
“因为我想见你……”吴畏的声音变低了,接着又马上嘹亮起来,“喜欢苹果香味的玫瑰花吗?”
“是你送的?”这可让仝童吃惊不小,“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苹果?”
“咳,你报到的时候就吃着苹果啊!”
“你连这个也知道?”
“嗯,我从那个时候,就喜欢你啊!”
“你骗人!我那时丑死了!”
“仝童,骗没骗你不重要,关键是,现在有个人,愿意花心思用天底下最美丽的谎言哄你开心。而且这个人还会向你发誓,他愿意一辈子这样‘骗’下去!只要你能开心!”
眼睛里好像有水。仝童感到奇怪,雪又没滴进眼睛里,怎么会融化呢?有一个人对自己这样傻傻的好,还有什么要求呢?难道真的要像齐宇那样,等到别人已经不爱的时候,才体会到这种“好”吗?
“仝童,你怎么不说话了?”
“没事。”仝童吸了吸鼻子。
“感冒了?流鼻涕?快擦一擦,要不要我把袖子借给你?”
“你讨厌!我才没有流鼻涕呢!”仝童被他逗笑了。
“那就把眼泪擦干吧!我是要给你幸福才来的。”他一字一顿地说。
吴畏的声音让她的眼前再次升起一团雾气。她乖乖地擦干眼泪,找出很久以前就买下的苹果味口红涂在唇上。她一直幻想着有这么一天,可以有雪,可以穿着白色的衣服,可以站在干净的雪地里,涂着苹果口味的口红,和一个人……
雪地里的人,不是她幻想中的人。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她已经知道了什么才是幸福。
文章四《世界尽头》
文/村上春树
到南水潭时,雪下得又急又猛,几乎让人透不过气。看这势头,仿佛天空本身都变成一枚枚碎片朝地面狂泻不止。雪也落在水潭,被深得近乎骇人的蓝色潭面吮吸进去。在这染成一色纯白的大地之上,惟独水潭圆圆地敞开俨然巨大眸子的洞穴。
我和我的影子瑟瑟地立在雪中,默不作声,只顾久久凝视这一片光景。同上次来时一样,周围弥漫着令人惧怵的水声。或许因为下雪的关系,这声音沉闷得多,仿佛远处传来的地鸣。我仰望未免太低的天空,继而把目光转向前方在纷飞的雪片中黑乎乎隐约浮现的南围墙。围墙不向我们诉说任何话语,显得荒凉而冷漠,名副其实是“世界尽头”。
木然伫立之间,雪在我的肩上和帽檐上越落越厚。如此下去,我们留下的脚印必将消失得无可寻觅。我打量一眼稍离开我站着的影子。影子不时用手拍落身上的雪,眯细眼睛盯视潭面。
“是出口,没错。”影子说,“这一来,镇子就再也不能扣留我们,我们将像鸟一样自由。”
影子仰脸直视天空。旋即闭起眼睛,俨然承受甘露一般让雪花落在脸上。
“好天气,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说罢,影子笑了。看样子影子如被卸掉重枷,原来的体力正在恢复,他轻快地拖着脚步独自朝我走来。
“我感觉得出。”影子说,“这水潭的另一方肯定别有天地。你怎么样,还怕跳进这里面去?”
我摇摇头。
影子蹲下身,解开两脚的鞋带。
“站在这里都快要冻僵了,尽快跳进去好么?脱掉鞋,把两个人的皮带连在一起,出去了再失散,可就白白折腾一场。”
我摘掉大校借给的帽子,拍掉雪,拿在手里望着。帽子是过去的作战帽,帽布有很多处都已磨破,颜色也已变白,想必大校如获至宝地一直藏了几十年。我把雪拍净,又戴在头上。
“我想留在这里。”我说。
影子怔怔地看着我的脸,眼神已经失去了焦点。
“我已经考虑成熟了。”我对影子说,“是对不住你,但我从我的角度仔细考虑过,也完全清楚独自留下来将是怎样的下场。如你所说,按理两人应一道返回原来的世界,这点我也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这才是我应回归的现实,而逃离这现实属于错误的选择,可是我不能离开这里。”
影子双手插进衣袋,缓缓地摇了几次头:“为什么?最近不是讲好一齐逃走的吗?所以我才制定计划,你才把我背到这里,不是么?究竟什么使你突然变心的?是女人?”
“当然有这个原因。”我说,“但并不完全如此,主要是因为我有了一项发现,所以才决定留下不走。”
影子喟然长叹,再次仰首望天。
“你发现了她的心?打算同她一起在森林里生活,而把我赶走是吧?”
“再说一遍,原因不尽如此。”我说,“我发现了造就这镇子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有义务,也有责任必须留下来,你不想知道这镇子是什么造就的?”
“我不想知道。”影子说,“因为我知道,这点我早已知道。造就这镇子的是你自身,你造出了一切——围墙、河流、森林、图书馆、城门、冬天、一切一切,也包括这水潭、这雪。这点,我也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一旦告诉你,你岂不就要这样留下来?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带到外面,你赖以生存的世界是在外面。”
影子一屁股坐在雪中,左右摇了好几次头。
“可是,在发现这点之后,你再也不会听我的了吧?”
“我有我的责任。”我说,“我不能抛开自己擅自造出的人们,和世界而一走了之,我是觉得对不住你,真的对不住你,不忍心同你分手。可是,我必须对我所做之事负责到底,这里是我自身的世界,围墙是包围我自身的围墙,河是我在自身中流淌的河,烟是焚烧我自身的烟。”
影子站起身,定定注视水波不兴的潭面,纹线不动地伫立于联翩而降的雪花中的影子,给我以仿佛渐渐失去纵深,而正在恢复原来扁平形状的印象。两个人沉默良久,惟见口中呼出的白气飘往空中,倏忽消失。
“我知道阻拦也无济于事。”影子说,“问题是森林生活,远比你预想的艰难,林中一切都不同于镇子。为延续生命需从事辛苦的劳作,冬天也漫长难熬,一旦进去,就别想出来,你必须永远呆在森林里。”
“这些通通考虑过了。”
“仍不回心转意?”
“是的。”我回答,“我不会忘记你,在森林里我会一点点记起往日的世界。要记起的,大概很多很多,各种人、各种场所、各种光、各种歌曲……”
影子在胸前几次把双手攥起又松开,他身上落的雪片给他以难以形容的阴影。那阴影,仿佛在他身上不断缓缓伸缩,他一边对搓双手,一边像倾听其声音似的将头微微前倾。
“我该走了。”影子说,“也真是奇妙,往后竟然再也见不到你了。不知道最后说一句什么好,怎么也想不起简洁的字眼。”
我又一次摘下帽子拍拍雪,重新戴正。
“祝你幸福。”影子说,“我喜欢你来着,即使除去是你影子这一点。”
“谢谢。”我说。
在水潭完全吞没影子之后,我仍然久久地凝视水面。水面未留一丝涟漪,水蓝得犹如独角兽的眼睛,且寂无声息。失去影子,使我觉得自己恍惚置身于世界的边缘,我再也无处可去,亦无处可归,此处是世界尽头,而世界尽头不通往任何地方。世界在这里终止,悄然止住了脚步。
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有镇子,有河流,有她和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鸟越过围墙,消失在南面大雪弥漫的空中。之后,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
【注】以上文字均来自节目中出现的部分文字的整理,可能有些作者或朋友的名字以及文字与原文不符,欢迎朋友们指出,如有分享或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名字,谢谢合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