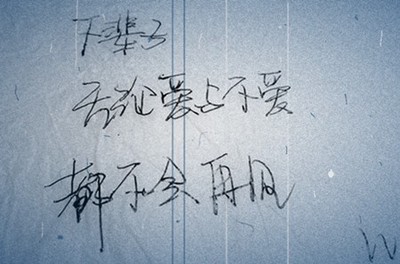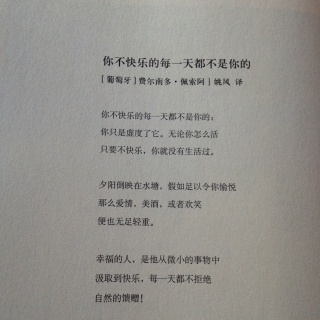记得那个2003年的愚人节吗,那个众人心中的哥哥,就那样迫不及待的纵身一跃。王家卫说张国荣是一个传奇,而他这一跃,提前结束了这个传奇,一个本应是童话的传奇。
在那个4月1日,在这么一个戏剧性的日子里,那只一直不停息地往高处飞翔的无足鸟陨落了,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愚人节的雨中,隔空传来张国荣坠楼的消息,愚人节的戏谑成分旋即被悲壮所掩盖。张国荣曾与辛晓琪在《深情相拥》中合唱,“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而在香港文华酒店楼前的晚风中,46岁的张国荣却永远地松开了拉扯尘世的手。
陈凯歌说,哥哥是另一个程蝶衣,一部《霸王别姬》,几乎是张国荣的谶语。
一转身的苍凉,浓墨重彩的繁华,倾国倾城。他的眼神,如此迷醉痴狂。是怎样的爱怎样的痛,怎样的悲伤,才会有这样的哀怨。
程蝶衣的光彩与寂寞。在台上的他,是万人瞩目的焦点,灯火辉煌,众声喧哗。在台下的他,卸去妆容的他对镜自揽,寂寞的只有自己的影子相陪而已。
燃烧所有的华服戏衣,燃烧蔓延的火光,他的迷醉的眼神,嘴角一丝嘲讽的笑。
程蝶衣的伤痛,他是戏中最美丽又最可怜的一个角色,三千宠爱于一身,锣鼓喧天,海市蜃楼。曲终人散,只是一个人,怀着一份永远不可能的爱。
在这场爱里,他注定是输家,他爱的是他,在社会约定俗成的绵延千年的规定中,她是他的妻,是她而不是他。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纵有爱深似海,又有什么立场去表达。
他在暗处,一次一次,被对他的爱,噬咬得撕心裂肺,在榻上让鸦片的烟雾缭绕笼罩一切,笼罩一切现实的世界——他是他在现实中永远不能名正言顺得到的爱。
于是只有在《霸王别姬》的二胡西皮里,在油彩华服千年永恒的经典里,他是他的妻,他是他的夫,他可以含着他所有的深情凝视着他,直到看进时间的尽头,是他们两人的舞台,再没有别的人。
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爱是他生命的唯一,没有政治,没有别人,从来没有。他爱他,所以为日本人唱戏,为国民党唱戏,为共产党唱戏,只是唱戏只是爱他。此外什么也没有。
可是,即便如此,他连最后的仅有的可以爱他的地方都已经失去,著着虞姬装,浓妆的他还是看着他和另外的“虞姬”而去,这个场景大概是整部片子里最惨烈的了,甚至更甚于文革期间的相互揭发,赤裸裸的伤害。落寞的“虞姬”亲手把冠冕给他的“霸王”戴上,推着他上台——那台上并没有“她”,他在暗处,在幕布的彼端,看着幕布上的翻腾华丽的剪影,没有他的《霸王别姬》依旧歌舞升平,锣鼓喧天。他绝然而去,身影依依,弱柳扶风,留给我们无限的心痛。
最后的舞台,两个人经历了岁月一次一次的变革,最后无欲无望的站在舞台上唱这最后的一出,程蝶衣望着段小楼,痴痴的望着他,他的矢志不渝的唯一的爱,他笑了,是虞姬唇边绝望的笑或者是一种欣慰,这一次,再也没有别人,只有他们俩,他死在这出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戏里,虞姬的姿态或者是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他微笑着自刎,死在他的怀里,或者这就是他的最好的归宿。
听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歌,那种吟哦,低回缥缈,仿佛电影里程蝶衣的百转千回,眼波流转,欲与还休。
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
再没有人能把程蝶衣演得如此深刻,分不清到底是张国荣还是程蝶衣 ,没有张国荣就没有倾国倾城的程蝶衣。再没有哪一个男人会有他这样的媚眼如丝,如他这样的风情万种,纵使是女人又怎及他一分。
很难说这部电影是成就了张国荣还是摧毁了他,因了程蝶衣,他成为电影画册上不朽的凄艳绝美,而这结局竟预示了他的结局。
张国荣是入戏很深的演员,说他在演戏,不如说他在投入,他在沉醉,在阐释着自己对世间的理解。在《阿飞正传》里的颓废,他的目光游离不知何处,一直在远方,远方就是梦想中的一切,他的游离一如所有人会有的迷惘。在《春光乍泄》里的迷醉,在《胭脂扣》里的醉生梦死,在他的光影里,仿佛是蒙了一层纱似的世界,那么的华美那么的不切实际又那么的真实的贴近了我们的心灵深处,让我们为他叹息为他痴狂,为他扼腕。
那一年,他纵身一跃,在繁荣的香港中环文华酒店,完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次华彩的演出,一如片中的蝶衣。
蝶衣,蝶衣,这一次,张国荣终于化蝶而去。是耶非耶。
还记得《东邪西毒》重回荧屏时,虽然被冠上“终结版”的噱头,它也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来。
《东邪西毒》的英文名字叫“Ashes oftime”,时间的灰烬,谁也抓不住。人们可以一遍遍的重温你的经典,但你,终究已经离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