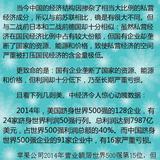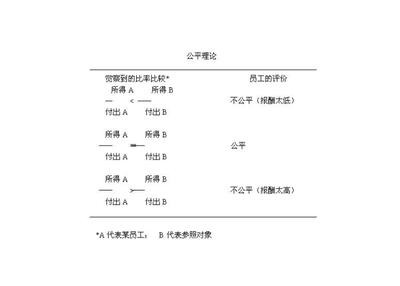阶级分析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和韦伯奠定了经典阶级分析的基础。曾经有一段时间,“阶级概念看起来已经逐渐被包围在一种衰败枯萎的气氛中了”(Giddens,1973:1),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面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当代社会学界又出现了阶级理论的复兴高潮,一大批社会学家开始重新关注阶级问题并试图发展或重建阶级理论(Lockwood,1958;Dahrendorf,1959;Aron,1964;Ossowski,1963;Lenski,1966;Parkin,1971;Giddens,1973;Braverman,1974;Poulantzas,1974;Wright,1979;Bourdieu,1984)。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后工业主义阶级理论和后现代主义阶级理论为代表,出现了大量反阶级分析的呼声,很多社会学家都在谈论阶级的瓦解和死亡,预言并呼吁从阶级分析中“撤退”(Lipset,1981;Pakulskiand Waters,1996b;Holton andTurner,1994),但坚持和发展阶级分析的学术努力一直持续到了当代(Bourdieu,1984;Goldthorpe andMarshall,1992;Goldthorpe,1996,2000;Wright,1996,2002;赖特,2004;Sorensen,1996,2000;Gruskyand Sorensen,1998;Grusky and Weeden,2001;Weeden andGrusky,2005a)。本文对阶级分析理论的关注集中于马克思和韦伯之后的当代发展。人们一般根据这些理论的知识起源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分析范式: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和新李嘉图主义等。其中,无论是从理论的完整性还是从理论的应用性来讲,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新韦伯主义阶级理论和新涂尔干主义阶级理论都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范式。本文着重讨论阶级分析理论最重要的几个理论支点。首先,本文将分析阶级理论的共同内核,即共同的前提假设和核心理论视角,以区分阶级分析理论和非阶级分析理论;其次,以上述三种阶级分析范式及其代表性人物为对象,分别从研究对象、分析思路和解释逻辑三个方面揭示不同分析范式的差异;最后,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对阶级分析理论做一个小结和讨论。本文的分析表明,阶级理论既有共享的理论“硬核”,又有不同的分析范式,这恰恰符合拉卡托斯(Lakatos,1986)对所谓“科学研究纲领”的描述,[1]而这也正是阶级分析理论具有相当学术“韧性”,面对经验事实的挑战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一、阶级是社会学中唯一的自变量吗?
“社会学只有一个自变量,那就是阶级。”1973年,当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斯廷奇科姆(ArthurStinchcombe)对他的学生们说了这一句话,这些学生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家”赖特(Erik OlinWright)。当然,赖特承认,斯廷奇科姆的这句话“是在故意地做出一种夸张的陈述”,或者说有点儿“自命不凡”,但赖特仍然认为,这句话也确实抓住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深刻地结构化的不平等问题,一般来说(即不仅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而‘阶级’就是谈论这一问题的众多方式之一”(Kirby,2001。参见Kirby对赖特所做的学术访谈)。说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是被深刻结构化了的社会不平等,这很可能会引起争论,但要说阶级分析是社会学中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理论方式,则很少会受到质疑。也就是说,阶级当然不是社会学中唯一的自变量,但是对于分析社会不平等以及相应的社会现象来说,阶级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要恰当地理解这一命题,首先必须要回答阶级分析的核心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阶级为什么会被一些人看作是社会学中的唯一自变量。
(一)分析视角的核心: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
研究者曾经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阶级分析视角和非阶级分析视角之间的差别,以揭示前者的核心特征。例如,类别的/连续的和多维/一维的(Ganzeboom,Graaf and Treiman,1992)、阶级的/等级的(Goldthorpe,1983)、关系的/等级的(Wright,1979:5)以及奥索斯基(StanislawOssowski)的二分、等级、功能三范式(转引自Giddens,1973:64-65)等。所有这些说法中最为核心,也最能代表阶级分析视角核心的,是阶级分析中的“关系论”和非阶级分析的“等级论/分配论”之间的差别,或者说是“分类别的阶级模型”(categoricalmodels of class)和“分等级的分层模型”(gradational models ofstratification)之间的差别。克莱克尔较为精确地揭示了这种差别,他指出,当“各个个人、团体或社会在一个社会或普世结构中所占据的(归属或成就)地位具有不平等的行动或互动权力或可能性,并因此长期不利或有利于相关者的生活机会”,此即为关系的不平等;而当“普遍可供使用且有追求价值的社会财富的获得持续受到限制,并因此不利或有利于相关的个人、团体或社会的生活机会”,此即为分配的不平等(Kreckel,1992:20)。虽然马克思和韦伯在阶级概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都采取了关系的阶级概念。如赖特所说,“他们都没有把阶级简单地定义为是在某些等级次序(gradationalhierarchy)上的名义水平。对这两人来说,阶级概念源自于对彼此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的各社会行动者的系统互动所做的解释”(Wright,2002)。同样,尽管现代阶级分析理论在分析范式上存在不同,但这种对关系性存在的关注一以贯之地体现他们的理论中。例如,赖特(2004)强调生产领域中的剥削关系,戈德索普(Goldthorpe,1982)强调劳动力市场和生产领域中的权威关系和雇佣关系,索伦森(Sorenson,2000)强调市场交换过程中的剥削关系,而格伦斯基(Gruskyand J.Sorensen,1998)强调各阶级之间基于职业“裁决权”的相互斗争。阶级分析就是这样一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借用赖特的话来说:“一个给定的阶级定位是借助把它与其他阶级定位相连接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的”(Wright,1996)。这意味着阶级不是简单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无论这种关系指的是阶级双方(或各方)之间的生产关系、雇佣关系、剥削关系还是统治关系,也无论这种关系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中还是发生在组织内部。有学者曾批评说,也可将地位等级看作是处在某种相互关系之中(例如,高低、多少的关系),因此关系论并非是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相反地,冲突论和功能论才构成了阶级分析视角和非阶级分析视角的本质区别。这是一种对量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差别的误解。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阶级分析都强调社会不平等建立在社会关系不平等基础之上,同时,并非全部阶级分析都强调阶级间的冲突(这在本文后面将有集中讨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阶级分析所关注的“结构性的不平等”:第一,这些不平等不是简单地由个人禀赋上的差异决定的,例如,个人在财产、教育、技能和劳动力上的差异。在阶级分析看来,阶级不平等和一般社会不平等的区别在于,由阶级所引起的差异是独立于在某一时点占据各阶级位置的那些人的个人特征而形成的(Sorensen,1991)。财产、教育、技能和劳动力等个人禀赋之所以反映了阶级差异,是因为存在一些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如生产资料所有制、财产制度、权力结构)及结构性机制(如社会封闭机制、再生产机制、剥削机制等)。简单来说,“结构既比个人获得更加重要,而且在逻辑上还先于个人获得而存在”(Baronand Bielby,1980)。第二,这些不平等根植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尽管社会学理论中的“文化转向”已被看作是一种潮流,在阶级分析中用文化分析取代结构分析也“甚嚣尘上”,并且在一部分阶级理论家看来,阶级“同样是一个文化和政治概念”(Wright,1996;Devine,1998),阶级的文化和符号维度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但是,阶级的“故土”仍然是在经济制度中(韦伯,1997下卷:260),社会秩序、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秩序和阶级利益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1960:1845-1846,1847-1848;Parkin,1971:26-28),[2]即使是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也不过是阶级“场域”和“惯习”的产物(Bourdieu,1984)。正因为阶级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结构的表现,所以基于阶级结构的不平等是一种稳定的、基础性的社会不平等。这体现了社会学所强调的结构首位,即“社会存在中被称之为结构的那些特征倾向于被物化,并被看作是最为基本的、硬的和永恒不变的,就像是一座建筑的大梁一样,而它们所构造的那些事件或社会过程则倾向于被看作是次要的和表面的”(Sewell,1992)。在这个意义上,还有必要澄清阶级分析和利益群体分析之间的差别,以凸显阶级作为一种结构性视角的性质。简单地说,“利益”指社会中值得追求的东西(包括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而利益群体就是基于这种“追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利益群体模式和阶级模式的差别在于:由于利益追求是经常改变的,因而利益群体通常是不稳定的。借用格伦斯基等人的话来说,利益群体只是“一群凑巧在给定议题上具有相似利益的个人”,因此他们只能聚结成若干“暂时的”集团,而不是“始终如一具有根本性的社会群体”(Grusky,WeedenandSorensen,2000)。当然,在一些阶级理论家看来,阶级也是一个基于利益而形成的利益群体,但阶级这样的利益群体不同于一般的利益群体,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分化所形成的利益群体,由此它和其他的利益群体有了本质的区别。“阶级分析的目的就是要确认具有始终如一重要性的社会分化”(Grusky,WeedenandSorensen,2000)。所以,我们将基于阶级分化而形成的利益群体称之为“阶级”,而不是笼统地称之为“利益群体”。
(二)阶级分析是一种系统的结构性视角
必须承认,即使是结构性的不平等也存在多种分析视角。例如,众所周知的以“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为代表的所谓“新结构主义”,同样强调各种结构性要素而非个体特征对持续的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包括对收入不平等、贫困、失业等的影响。尽管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导致该理论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从来没有形成一个连贯一致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科学研究纲领”,不同研究者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使用了大量不同的描述性概念,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核心概念,并提供形成机制方面的证明,因而无法有效地揭示社会不平等的形成和影响。阶级分析理论则不同,尽管其传统中也存在大量竞争性的分析范式,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和批评,但在核心概念上,即在“阶级”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分化而形成的结构性位置的集合这一点上还是达成了“共识”,从而为阶级分析理论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和系统化、理论化的基础,形成了一个由阶级基础、阶级结构、阶级形成的过程和机制、阶级关系、阶级的社会后果和阶级的未来等内容所构成的相对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阶级分析虽然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着巨大的挑战,但仍然能够保持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一种“科学研究纲领”式的理论系统。这一“硬核”的存在使得阶级分析视角能够在多元化的范式中捍卫自己的价值和相关性,延续自已的生命力。当然,阶级分析不是社会不平等研究的全部,更不是社会学乃至社会分析的全部。过多的赞誉和过多的诋毁都是不恰当的。“无论如何,对于想要构建一个值得追求的研究项目的阶级分析来说,只要它能够确认重要的因果机制就足够了;我们没有必要说,阶级是社会现象的最为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决定因素”(Wright,1996)。在共享一个“内核”的基础上,阶级分析理论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分析范式。下文将从分析对象、分析思路、解释逻辑等不同方面揭示前述三种主要分析范式之间的差异。
二、阶级分析对象:宏观与微观
阶级分析范式的差异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层次界定上。一般来讲,阶级分析的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宏观层次的现象和微观层次的现象。格伦斯基等人在区分阶级分析的宏观对象和微观对象时指出,阶级分析的任务一是在宏观层次上解释转型事件和大规模社会变迁,一是在微观层次上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Grusky,WeedenandJ.Sorensen,2000)。宏观层次的研究典型地表现为各种基于阶级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如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kocpol,1979);微观层次的研究则表现为各种基于个人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在当代社会学中,一个趋势是阶级分析的议程从宏观分析向微观分析的转移。威登和格伦斯基总结说,“在过去的25年里(笔者注:1980-2005),阶级分析的目标已经从发展对集体行动、革命和其他宏观水平的结果变量的解释,转移到去解释在个人层次上的生活机会、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异”(Weedenand Grusky,2005a)。他们甚至断言,“陈旧的宏观水平上的议程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Grusky,Weeden andJ.Sorensen,2000;Sorensen,2000)。[3]结合上述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对于现代阶级分析中的三种分析范式,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阶级研究对象的清单,主要包括:(1)阶级结构和阶级流动。即划分当代阶级结构,研究阶级分化的形成过程,阶级位置在代内和代际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以及阶级的跨边界可渗透性等。(2)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主要是宏观层次的研究,既包括以阶级为基础的历史变迁理论,也包括对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阶级形成以及阶级斗争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3)阶级影响。主要是微观层次的研究,即阶级所产生的个人生活机会和生活选择后果,包括阶级对个人的收入、社会态度、生活机会、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等造成的影响(赖特,2004,2006;Goldthorpe,2007b:126-127;Gruskyand Weeden,2001;Grusky and Sorensen,1998;Weeden andGrusky,2005a)。虽然上述三种范式与宏观层次/微观层次的区分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是赖特、戈德索普和格伦斯基的阶级理论在研究对象的具体范围以及侧重点上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戈德索普所代表的新韦伯主义范式集中于对阶级流动和阶级影响的研究,他把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问题看作是应从实证上处理的议题,并且倾向于认为“高水平的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都是历史上的特例而不是常规”(Goldthorpe,2007b)。实际上,戈德索普强烈主张从阶级分析议程中删除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反向地看,戈德索普的阶级分析可以称为“四个没有”理论,即没有历史理论、没有阶级剥削理论、没有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理论、没有政治行动的还原论(Goldthorpeand Marshall,1992;Holton andTurner,1994)。格伦斯基所代表的新涂尔干主义范式与戈德索普的主张针锋相对。格伦斯基特别强调对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行动的研究,认为如果阶级理论家放弃了对阶级的主观维度和阶级行动问题的研究,无异于是拿阶级理论的前途做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豪赌(Gruskyand Weeden,2001;Grusky and Sorensen,1998;Weeden andGrusky,2005a)。赖特在阶级分析对象的选择上则较为传统和均衡,代表了一种温和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

当代三种主要阶级理论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可以总结如下:
| 微观层次 | 宏观层次 | |||
| 生活机会 | 社会态度 | 阶级行动 | 历史变迁 | |
| 戈德索普 | √√ | √√ | × | × |
| 格伦斯基 | √√ | √√ | √√ | × |
| 赖特 | √√ | √√ | √ | √ |
注:表中的符号“√”表示强烈的程度,两个“√”表示强烈,一个“√”表示一般,“×”表示没有。
三、分析思路:集体行动者vs生活条件综合信号不同的阶级分析范式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集中反映在要不要研究阶级形成问题、要不要研究与阶级形成密切相关的阶级行动问题,由此形成了对阶级的社会意义的两种分析思路。(一)“结构-意识-行动”: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
传统的阶级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都把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作为极其重要的研究议题。如果说阶级结构是被客观定义了的社会空间,那么阶级形成就是被集体性地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行动者形成的过程(赖特,2006),实际上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问题。在以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为研究主题的宏观阶级社会学中,阶级形成问题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因为只有阶级成员组织起来,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够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阶级。宏观阶级社会学中一般都包含一种基于阶级的集体行动理论,根据这种集体行动理论,“在阶级结构内占据相似位置的个人,会发展出共同的意识和对其阶级利益的把握;继而,共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会激发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以追求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GoldthorpeandMarshall,1992)。这种理论逻辑可被称为“结构-意识-行动”链条,菲尔把它看作是一种“咒语”(Pahl,1989),认为它具有明显的决定论色彩。在阶级理论复兴的前期,就有大量社会学家重新阐释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问题。例如,吉登斯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从“间接结构化”和“直接结构化”这两个方面来论证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形成(Giddens,1973;GruskyandSorensen,1998);帕金从社会封闭的角度论述了阶级形成和与此相关的阶级行动问题(Parkin,1979)。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的影响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主观方面,有调查表明,人们对阶级的主观感知和身份认同日趋衰落。格伦斯基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艾米森和韦斯特恩1990年对澳大利亚人阶级意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仅有7%的澳大利亚人把他们的社会阶级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身份(转引自Grusky,WeedenandSorensen,2000)。在客观方面,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行动和阶级斗争日益减少,现在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以民族(如各种各样的民族独立甚至民族分裂运动)、性别(如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同性恋权益运动)、人类关怀(如西方的“绿党”和环保主义运动)、群体利益(如拆迁区群众的抗议活动)等为基础的新形式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构成了前文所述以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对阶级分析之批评与攻击的重要基础。正因为如此,西方阶级理论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阶级不行动”问题的解决上。主要的解决方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强调“结构-意识-行动”链条中的各种随机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会对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产生“干扰”或者“阻挠”(Dahrendorf,1959;Tilly,1988;赖特,2006:116—119);第二种是求助于“虚假阶级意识”概念,即认为工人阶级内部出现的一些新阶层“对于他们真实的阶级位置和真实的阶级利益具有一个‘错误的’阶级意识”(Lockwood,1958),从而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团结;第三种是主张重新构建阶级分类图式,以正确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这种理论认为,过时的阶级分类图式无法正确地反映资本主义目前的阶级结构,也因此必然无法正确地捕捉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Weedenand Grusky,2005a,2005b)。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到八九十年代,重新构建阶级分类图式的努力成为很多阶级理论家的重要工作。但是,总的来看,面对“阶级不行动”的批评和攻击,在阶级分析复兴运动中存在着一种“雄心壮志缩减”的趋势,这指的是越来越多的阶级理论家开始放弃宏观层次上的阶级分析(其典型表现就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历史理论以及与这种理论密切相关的阶级形成问题),放弃阶级分析中的“结构—行动模型”,而微观层次的阶级分析(例如阶级对收入水平、社会态度等个人层次结果变量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Grusky,Weedenand Sorensen,2000;Goldthorpe,2002;Weeden andGrusky,2005a)。赖特以及戈德索普的阶级理论都可以被看作是阶级分析家们“雄心壮志缩减”的典型例子。与那些缩减了雄心壮志的阶级理论家们不同,格伦斯基等人认为,如果不研究阶级形成和阶级行动,阶级理论家就无法反驳后现代主义所谓“阶级死亡”的主张。格伦斯基等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回应反阶级分析的论调以及阶级分析家内部“雄心壮志缩减”的举动:第一,阶级利益的形成和阶级行动的发生与“阶级结构化”有着密切关系,阶级结构化促进阶级利益的形成、促进阶级团结,并促成阶级行动。当代社会的技术变迁、组织变迁以及职业协会的变迁等一系列客观事实都表明,阶级结构化的趋势并未减弱(GruskyandSorensen,1998)。第二,社会学家之所以没有捕捉到显著的阶级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使用了错误的阶级分类框架,阶级分析从宏观层次向微观层次的转移并未伴随着阶级图式的相应转移,社会学家还在沿用传统的大阶级聚类图式,而这种聚类图式大大掩盖了阶级关系的“局部结构化”,掩盖了职业层次上的阶级利益、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Gruskyand Sorensen,1998;Weeden andGrusky,2005a)。第三,阶级集体行动已经不是以往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而是在职业群体层次上出现的各种为争夺裁决权(jurisdiction)而展开的职业封闭实践,例如美国眼科大夫和验光配镜师之间围绕谁有权控制眼部矫正手术这一业务而展开的相互斗争(Gruskyand Weeden,2002)。其实,从否认阶级集体行动到强调阶级集体行动之间的分歧并没有那样的绝对,阶级分析的“雄心壮志”更多地是缩减或弱化而不是消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戈德索普和格伦斯基争论大、小聚类阶级的优劣时,戈德索普(Goldthorpe,2002)争辩到,基于大的阶级分类的集体性阶级行动不是不存在了,只是不再表现为革命的“冬宫风暴”模型下所描述的那种行动,而表现为北欧国家的“新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或“社会合作主义”(socialpartnership)等制度,只不过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顺应而非加强阶级冲突。(二)“结构-状况-选择”: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
当阶级分析者从宏观层次的阶级行动转向微观层次的阶级影响时,他们对阶级概念的使用也会同时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就是阶级概念从集体行动者变成了生活条件的综合信号(omnibussignal of life conditions)[4]。微观层次上的阶级影响在目前的阶级分析文献中占据较大比例,格伦斯基甚至指出,这类分析无处不在,“对几乎任何一个个人层次的变量,我们都可以找到一篇完善的研究文献,把这一变量看作是由阶级所决定的”(Weedenand Grusky,2005a)。按照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Pakulski andWaters,1996a)的总结,这些微观层次的现象包括政治偏好、生活方式选择、儿童抚养实践、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机遇、对教育机遇的获得、婚姻模式、职业继承、收入,等等。威登和格伦斯基(WeedenandGrusky,2005a)更系统地把这些“待解释对象”归为三个主题领域,分别是:(1)生活机会,例如收入、教育、工作条件等;(2)生活方式,例如消费实践、制度参与等;(3)文化,例如政治偏好、社会态度等。微观层次的阶级分析,实际上就是将阶级作为客观的结构性位置,研究它是如何影响阶级成员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选择的。与解释集体行动的“结构-意识-行动”链条一样,在对微观层次的现象进行解释时,阶级理论家也都遵循着一条大致类似的链条,即“结构-状况-选择”。这同样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只不过它把社会结构更明确地指定为阶级结构。微观层次的研究就是要确认在“结构-状况-选择”链条上发挥作用的各种因果机制。具体来说,“结构-状况-选择”链条的内容是,“那些拥有类似资源并且因此占据类似的结构性位置的人,将会共享类似的关于‘生活机会’的可能性和约束……因此,他们可能也会被预期以相似的方式行动”(Roseand Pevalin,2003)。事实上,在阶级理论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论证阶级与其他变量——年龄、性别、种族等——相比,到底有无解释上的特权。如霍尔顿和特纳(HoltonandTurner,1994)所说:“对阶级理论之前途的评估(取决于)……与其他寻求解释相同现象的更广泛的理论相比,‘阶级’理论的卓越之处”。换用索伦森(A.Sorensen,1991)的话来说,“当它得出了对流动和获得过程的新的洞察时,阶级分析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如果它产生了一些但并非全部的可以由其他理论提供的洞察时,和/或它很少为富有成效的问题和研究程序提供启发时,阶级分析就不是一个那么有用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阶级分析和各种非阶级分析在分析形式上的区别仅在于:研究者是使用阶级作为自变量,还是选择其他的自变量,例如人口统计学变量、教育、城乡、组织、政策等变量。很多反对阶级分析的批评者认为,人们无法解释阶级效应被再生产时所借助的过程。例如,菲尔(Pahl,1989,1993)指出,阶级概念不再是有用的了,因为阶级和各种结果变量之间的关联“大概混合了许多相当截然不同的(因果)过程,这些过程应该保持分析上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这些过程分别加以分析,而不是把阶级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信号。布瑞恩和罗特曼(BreenandRottman,1995a)也认为,阶级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并且阶级机制一直未被明确指定,因为人们一直忽视了阶级在决定施加于行动上的机会和约束时所采用的方式。研究者需要诸如对纵向数据的定量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来解释“阶级是如何产生它所具有的效应的”这一问题(参见Devine,1998)。所有这些批评都指向了连接阶级和各种结果变量的因果机制。我们下面就转而阐释阶级分析的不同解释逻辑。四、阶级分析中不同的解释逻辑本文所说的解释逻辑,是指构成研究者对社会现象所做解释之基础的那一潜在的行动理论,这种行动理论需要详细阐明行动者所面临的约束、行动者的动机和意向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行动步骤。它实际上是社会学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因果解释中的“解释机制”或者“行动叙述”(actionnarratives)。正如戈德索普(Goldthorpe,1996)所言,社会过程中的因果关系无法从定量分析本身中得以建立,而是在逻辑上依赖于行动叙述。所以,研究者在用自变量解释因变量时,必须从行动理论的角度有逻辑地阐明自变量的作用过程,只有这样,研究者所提出的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解释才是令人信服的。如果研究者只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简单描述和对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简单说明,而没有从机制的角度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这样的研究就会成为所谓的“变量社会学”(赫斯特洛姆,2010)。因此,赖特、戈德索普和格伦斯基都非常注重解释逻辑问题,而他们在解释逻辑上的差异甚至比他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更加鲜明。(一)阶级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
分析三种范式的解释逻辑,首先必须区分作为自变量的阶级和作为因变量的阶级,因为这两个概念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的解释逻辑密切相关。阶级位置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既是决定的(determining)又是被决定的(bedetermined)。换句话说,阶级既是被决定的社会位置,又是决定(他者)的社会结构。因此从分析上来讲,阶级既是一个自变量也是一个因变量。然而实际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划分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例如,当我们用阶级去解释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变迁时,阶级就是一个自变量。但当我们把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时,阶级又是一个因变量,也就是说,此时阶级是被决定的,我们要对决定阶级流动、阶级形成、阶级行动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样地,当我们把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的综合信号,去解释微观层次上的个人生活机会和社会态度时,阶级就是一个自变量。但是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的阶级概念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因变量,例如格伦斯基等人就列举了如下四种阶级作为因变量的传统情形,即阶级再生产和流动、以阶级为基础的选择性交配、以阶级为基础的友谊和网络纽带以及阶级或职业的分割。他们认为,“一个能够提供强烈的生活条件信号的阶级图式能够最好地满足这些研究传统”(Weedenand Grusky,2005a)。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划分与阶级理论的具体解释逻辑密切相关,因为这关涉解释逻辑中的解释物和被解释物(explanans/explanandum)。也就是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划分导致了阶级在解释逻辑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无论研究者在分析中把阶级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在提供解释逻辑时,都必须以某种行动理论作为基础。(二)三种分析范式的解释逻辑
基于不同的理论渊源、研究对象和分析思路上的差异,形成了三种分析范式不同的解释逻辑。赖特的解释逻辑具有典型的结构主义色彩,可称其为“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这一逻辑包含两个基本假设:第一,阶级关系是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第二,阶级关系的对抗性源于各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这种剥削(而非简单地压迫)意味着剥削阶级的物质福利与被剥削阶级的物质生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者依赖于对后者的剥夺(赖特,2006:39,68-93;赖特,2004:12-14)。进而,剥削的客观存在使得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分别形成了榨取劳动果实和保卫劳动果实这两种客观利益。而赖特认为,阶级利益的形成是一切阶级态度和阶级行动的基础。赖特对剥削机制的强调,是其所以能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基础。但他对利益机制的阐释以及他在解释阶级行动时对博弈论和搭便车理论的使用,则不可避免地使其阶级理论蒙上了一层“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这一点从他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埃尔斯特(JonElster),尤其是罗默(JohnRoemer)之间的个人交往和学术借鉴中就可见端倪(赖特,2004;另参见Kirby,2001)。戈德索普同样倾心于理性选择(行动)理论,但是与赖特的剥削和利益机制不同,戈德索普的解释逻辑强调的是“状况逻辑”。“状况逻辑”(logicof the situation)由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Popper)提出,指的是各种政治历史事件既不是由帝王将相决定的,也不是由所谓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而是由事件中的个人根据所处状况而采取的“必须”的反应(波普尔,2009:116-120)。以“状况逻辑”为基础,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发展出了一种理性行动理论的变体。按照这种理性行动理论,在构思关于某种(已发生的)行动的具体解释时,理性从一开始就被假定了,即分析者必须首先假设个人会根据他们发现自身所处的那些状况而适当地或充分地行动,这样,分析者的注意力就能够集中到“状况”上(Goldthorpe,2007a)。换句话说,在这种理性行动理论下,分析者所要做的就是对历史事件进行“理性重建”(rationalreconstruction)。与赖特不同,戈德索普并不假设阶级关系是对抗性的,相反,他主要把阶级看作是一些具有不同约束和机会的位置集合。与赖特的另一个不同是,戈德索普(Goldthorpe,1996)认为阶级分析的任务不是去解释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某种生成性过程”(即阶级形成和阶级瓦解),而是解释阶级关系的稳定性,尤其是解释与阶级相关的生活机会和社会行动模式所展示出来的持续的统计规律性。在戈德索普看来,阶级分析所要做的事情,一个是“去解释为什么处在同一群体中的人会拥有许多共同的属性,包括获得物质成功的相似机会”(BreenandRottman,1995b),即解释生活机会的阶级变异;另一个是解释人们“如何动用他们的资源”行使选择权,即解释生活选择的阶级变异。戈德索普认为,处于不同阶级位置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他们的阶级状况的相当理性的回应”,尽管选择的引入在对个人行动的分析中添加了一种不确定因素,但是对人们来说,(总的)趋势是在相似的境遇中做出相同的选择,所以人们的选择能够表现出统计上的规律性(Goldthorpe,2002;TakWang Chan and Goldthorpe,2007;另参见Devine,1998)。格伦斯基等人强烈批评戈德索普的解释逻辑,认为戈德索普的阶级概念是名义主义的,其解释逻辑过于贫乏。格伦斯基(GruskyandWeeden,2002)认为,首先,戈德索普所建构的阶级“无非就是一堆约束和机会集合”,这样的阶级没有阶级文化,没有阶级团结,没有阶级行动,而且无法明确地界定阶级边界,一言以蔽之,这样的阶级无论是在结构化程度上还是在同质性程度上都非常低,因此,戈德索普的这种名义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戈德索普所构建的阶级可以被称为“条件集合”而不能被称为“阶级”。其次,由于未能把阶级图式建立在职业细类水平上,戈德索普无法发现多种多样的机制,而只能求助于有限的状况逻辑和理性行动理论。威登(WeedenandGrusky,2005a)甚至不无讽刺地挖苦道:“理性行动解释可能是(戈德索普等)‘大阶级理论家’能够打出的最强的一张王牌了,但是,比起‘制度化阶级类别理论家’(即格伦斯基)可利用的那些同质性诱导机制来,他的这张牌就要虚弱得多”。与戈德索普只强调阶级的经济意义,而避免参照阶级文化的作法不同,格伦斯基等人强调阶级是一个“经济文化群体”,阶级的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是阶级概念的两个面,缺一不可。与戈德索普对阶级集体行动及阶级同质性的漠不关心不同,格伦斯基等人一直致力于探索阶级同质性的各种表现以及产生阶级同质性的各种机制,他们在多篇论文中不厌其烦地论述身份认同、阶级意识、社会封闭、职业亚文化、集体行动等阶级同质性现象,但是在某些批评者看来,这些论述没有在阶级同质性的各种表现与产生阶级同质性的各种机制之间作出明确区分(Gruskyand Sorensen,1998;Grusky,Weeden andSorensen,2000)。不过在最近的几篇论文中,格伦斯基等人(Weeden and Grusky,2005a,2005b)明确提出了解释机制问题,并把此前提出的各种机制总括为三大类机制,即:(1)配置机制,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选择机制;(2)社会调节机制,包括技能培训、社会封闭、利益形成和学习的普遍化等四种子机制;(3)条件的制度化机制,指的是相同职业内工作条件的趋同化趋势。格伦斯基等人认为,通过上述三类机制的作用,具有内部同质性的各个阶级得以在职业细类的层次上出现(即“同质化”),而且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阶级得以被转化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群体”(即“结构化”)。基于此,格伦斯基的解释逻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结构化逻辑”或者“同质性逻辑”。不同学者的解释逻辑之所以不同,根源之一在于研究者对社会行动(阶级行动)动因的把握存在分歧。赖特认为,阶级行动必然是一种阶级成员的联合行动(集体行动),这就需要存在对抗性的阶级利益和对这些利益的清晰把握(即阶级意识),而后才能产生阶级的组织(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格伦斯基则不满足于单纯用利益来解释一切,他认为,通过配置、社会调节等机制,某一阶级内部成员的性情倾向、品味、文化等都将趋于同质,而各个阶级之间则趋于异质,这样,阶级内部的行动和各个阶级之间的互动(即原始意义上的阶级行动)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戈德索普的逻辑显然与他们不同。戈德索普首先不认为阶级行动是必然出现或必须被研究的,其次不认为阶级行动是有组织的、集体性的,他所强调的阶级行动的“统计规律性”只承认在统计上能够发现处于同一阶级的成员具有类似的行动或行动倾向。戈德索普认为用状况逻辑和理性行动就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统计规律性,而无需借助共同利益、同质性的阶级文化等概念。在这里,有必要对十分重要但在本文中无法做详细讨论的阶级图式问题做一简单论述,即阶级的解释逻辑与阶级图式构建之间的关系。社会分层图式(阶级图式)是社会学家研究阶级现象的一个“基本工具”,更是研究阶级问题的基础,研究者采用的解释逻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阶级图式的建构和选择。正如威登和格伦斯基(WeedenandGrusky,2005a)指出的,“如果阶级分析的目标是去理解对立的利益如何可能产生阶级对抗,那么围绕一个能定义阶级利益的关键变量(例如财产所有权、权威关系)来构建一个阶级图式,是讲得通的”,而“如果目标是去理解差别化的生活条件”,那么我们就应该在阶级分类图式中尽可能地捕捉各种重要差异,以完整地描绘一副“社会结构的地理图”。五、小结和讨论当代阶级分析理论对分析中国转型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 阶级分析作为分析转型社会的重要概念工具。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国内有关社会结构变革、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研究领域中,近10年来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我们称之为“分析范式转变”的现象,即相对于其他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分析,阶级分析视角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和应用。在国内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中,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阶级分析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性,几乎都把正在经历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作为凸显阶级分析意义的现实前提(仇立平,2006;孙立平,2006;沈原,2006;冯仕政,2008;林宗弘、吴晓刚,2010)。尽管如此,阶级分析范式的引入还是面临着一些质疑和争论(例如,国内有关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和阶级化的争论,参见:陆学艺等,2002;李路路,2003;李强,2008;李培林,2008;孙立平,2008,2009)以及其他分析范式的竞争(例如,等级的或利益群体的分析范式)。除去一些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质疑外,在理论的谱系中,阶级分析从本质上看确实只是分析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众多范式之一。但是,正如本文对阶级分析的理论“硬核”所做的讨论一样,该理论基于社会关系的分化对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分析,在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理论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力度。因此,阶级分析的范式必须清晰地立足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才能够彰显出与其他分析范式的区别及独特价值。第二,多元的分析范式和解释逻辑。这是一个简单但常常被忽视或误解了的“常识”。近年来,中国国内很多研究阶级问题的社会学者都在谈论阶级(或集体)行动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或社会)冲突问题,而且,学界“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其原初动机就是为了解释和分析阶级(集体)行动问题(沈原,2006;仇立平,2006;冯仕政,2008)。即使是竞争性的利益群体分析范式,也是基于对社会行动问题的关注(孙立平,2008;参看李强,2008)。可以理解,这种对行动、矛盾和冲突的关注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和冲突加剧的社会现实使然。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阶级分析理论中多元的分析范式和解释逻辑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阶级结构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影响。关注并清楚地了解这些多元的分析范式和解释逻辑,揭示中国社会中阶级矛盾与冲突的程度和形式,阶级位置对生活条件和社会机会分配的影响(包括职业地位获得、收入、教育、就业、消费模式、社会态度、价值观,等等),以及阶级结构和社会后果之间存在的机制等,不仅有助于提升阶级分析的理论力量,而且有助于阶级分析范式的拓展,彰显其独特的分析价值。阶级分析范式在大量分析领域中的缺失,不能不说是该理论的缺憾。第三,阶级图式的建构。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分层层次,也无论是强调阶级行动还是强调生活条件的综合信号,阶级分析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其现实前提是现实世界中存在较高程度的“阶级形成”(按赖特的理论),或者发生定义阶级边界的“符号过程”(按布迪厄的理论);其理论前提是必须发展出能够抓住基本阶级关系的有效的阶级图式。阶级图式问题在本文中没有专门讨论,但时有涉及,且被赋予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学者逐步重视阶级分类图式的作用,并且也提出了若干分类框架,如陆学艺(2002)、刘欣(2005,2007)、郑杭生、李路路等(郑杭生等,2004)以及林宗弘、吴晓刚(2010)等。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阶级分析理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本身就正在经历一个再形成的过程,这些分类图式在建构逻辑、效度检验及相应的解释逻辑等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阶级分析范式在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有效的、竞争性的阶级图式的建构。我们期望阶级分析理论能够显现出应有的生命力,成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之一。这也是本文想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参考文献(References)
Aron, Raymond. 1964. La lutte de classes: nouvelles leçons sur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Paris: Flammarion et Cie.Baron, James N. and William T. Bielby, 1980. "Bringing theFirms Back in: Stratification, Segment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of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737-765.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Judgement Tast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Press.Breen, R. and D. Rottman. 1995a. "Class Analysis and ClassTheory". Sociology 29:453-473.Breen, R.and D. Rottman. 1995b. Class Stratification. Hemel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Chan, Tak Wing and John H.Goldthorpe. 2007. "Class and Status: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Its Empirical Relevance."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Vol.72.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Dahrendorf, Ralf. 1979. Life Chances:Approaches to Social andPolitic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Devine, Fiona. 1998. "Class Analysis and the Stability ofClass Relations". Sociology, Vol.32, No.1.冯仕政. 2008. 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J].社会学研究(5). [FengShizheng. 2008. “Bring the Class Back In? Paradigm Shift in ChineseSocial Inequality Research.” Sociological Studies (5). (in Chinese)]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and D. J. Treiman.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 1-50.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Goldthorpe, John H. 1982.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Information and Future",in Giddens and G.Mackenize eds., Social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Goldthorpe, John H. 1983.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Formation: On the Renewal of a Tradition in Sociological Inquiry”.Casmin Working Paper 1. Mannheim/Amsterdam.Goldthorpe, John H. 1996. “Class Analysis and theR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 The Case of Persisting Differentials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Sociology,Vol.47, No.3.Goldthorpe, John H. 2000.“Rent, Class Conflict, and ClassStructure: A Commentary on Sørensen”.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 6:1572-1582.Goldthorpe, John H. 2002. “Occupational Sociology, Yes:ClassAnalysis, No:Comment on Grusky and Weeden's ‘Research Agenda’.”Acta Sociologica, Vol.45, No.3.Goldthorpe, John H. 2007a. On Sociology (Vol. 1):Critique andProgra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Goldthorpe, John H. 2007b. On Sociology(Vol.2):Illustrationand Retrospec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Goldthorpe, John H. and Gordon Marshall. 1992. "The PromisingFuture of Class Analysis: 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ques".Sociology,Vol. 26, No. 3.Grusky, David B. and Jesper B. Sorensen. 1998. "Can Class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3):1187-1234.Grusky,David B. and Kim A. Weeden. 2001. "Decompositionwithout Death: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New Class Analysis." ActaSociologica 44(3): 203-218.Grusky,David B. and Kim A. Weeden. 2002."Class Analysis andthe Heavy Weight of Convention." Acta Sociologica45(3):229-236.Grusky,David B., Kim A. Weeden, and Jesper Sorensen. 2000."The Case for Realism in Class Analysis." Political Power andSocial Theory (14): 291-305.赫斯特洛姆. 2010.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Hedstrom. P. 2010.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Holton, Robert, and Bryan Turner. 1994. “Debate andPseudo-Debate in Class Analysis:Some Unpromising Aspects ofGoldthorpe and Marshall's Defence.” Sociology (28):799.Kirby, Mark. 2001. “An Interview with Erik Olin Wright”.Social Science Teacher.Kreckel, Reinhard. 1992. Politische Soziologie der SozialenUngleichheit. Frankfurt/Main:Campus Verlag.拉卡托斯. 1986.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上海译文出版社. [ Lakatos, Imre. 1986.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Shanghai TranslationPublishing House.]Lenski, G. E.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李路路.2003.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J]. 社会学研究(5).[Li Lulu. 2003.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From "indirect re-production" to theco-existing situation of "direct re-production" and "indirectre-production"”. Sociological Studies (5). (inChinese)]李培林. 2008. 现代性与中国经验[J]. 社会(3). [Li Peilin. 2008. “Modernity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Society (3). (in Chinese)]李强,2008.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i Qiang.2008.Ten Lectures onSocial Stratific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Press.]林宗弘、吴晓刚. 2010.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J]. 社会(6). [LinThung-hong and Wu Xiaogang. 2010. “Institutional Changes,Class-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China,1978-2005.” Society(6). (in Chinese)]Lipset, S.M. 1981.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Proletariat?”Encounter (56):18-34.刘放桐,等.编著.1990.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Liu Fangtong etc.1990.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House.]刘欣. 2005.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J]. 社会学研究(5). [Liu Xin. 2005.“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Contemporary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5). (in Chinese)]刘欣.2007.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J]. 社会学研究(6). [Liu Xin. 2007.“Class Structure and the Middle Class Location in Urban China.”Sociological Studies(6). (in Chinese)]Lockwood, David. 1958. The Blackcoated Worker: A Study in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Allen and Unwin.陆学艺, 主编.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u Xueyi. 2002.Report on Social Strata of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SocialScience Academic Press.]马克思、恩格斯.1970.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Karl Marx & FriedrichEngels. 1970.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House.]马克思、恩格斯.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Karl Marx & FriedrichEngels. 1960.The Complete Works of Max and Angles(the Thirdvolum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Ossowski, Stanislaw,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Consciousnes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ahl, R.E. 1989. "Is the Emperor Naked? Some Comments on theAdequacy of Sociological Theory in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3):709-720.Pahl, R.E. 1993. "Does Class Analysis without Class TheoryHave a Promising Future?:A Reply to Goldthorpe and Marshall".Sociology (27):253-258.Pakulski,Jan. and Malcolm Waters. 1996a. "The Reshaping andDissolution of Social Class in Advanced Society". Theory andSociety,Vol.25, No.5.Pakulski,Jan. and Malcolm Waters. 1996b. The Death of Class.London: Sage.Parkin, Frank.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NewYork: Praeger Publishers.Parkin,Frank.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A BourgeoisCritiqu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波普尔. 2009.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Popper, K. 2009. ThePoverty of Historici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House.]Poulantzas, Nicos. 1974.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London:Verso.仇立平. 2006. 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 社会(4). [Qiu Liping. 2006.“Returning to Karl Marx: Retrosp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Stratific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Society(4) .(in Chinese)]Rose, D. and D.J. Pevalin. 2003. A Researcher's Guide to theNational Statistics Socio-Economic Classification. London:Sage.Sewell. W.H.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Skocpol. Theda.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沈原. 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 社会学研究(2). [Shen Yuan. 2006. “The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Chinese Working Class.”Sociological Studies(2). (in Chinese)]Sorensen, Aage B. 1991. "On the Usefulness of Class Analysisin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ActaSociologia, Vol.34, No.2.Sorensen, Aage B.1996.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Social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 1333–1365.Sorensen, Aage B.2000.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1523-1558.孙立平. 2006. 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J]. 中国与世界观察(3). [Sun Liping. 2006.“Alert to Oligarchy of the Upper Class and Populist of the LowerClass.” China and World Affairs(3). (in Chinese)]孙立平. 2008. 利益关系形成与社会结构变迁[J]. 社会(3). [Sun Liping. 2008. “TheFormation of Interest-based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StructureChanges.” Society(3). (in Chinese)]孙立平. 2009.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J]. 南京社会科学(5). [Sun Liping.2009. “The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AnalyticalModel.” Social Science in Nanjing (5). (in Chinese)]Tilly, Charles. 1988. "Solidary Logics: Conclusions". Theoryand Society,Vol.17, No.3.Weeden,Kim A., and David B.Grusky. 2005a. "The Case for a NewClass Ma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 No.1.Weeden,Kim A., and David B.Grusky. 2005b. "Are There AnySocial Classes at All?" in The Shape of Social Inequality:Stratification and Ethnic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David Bill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Vol.22. Amsterdam: Elsevier.William H. Sewell,Jr.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Duality,Agency,and Transform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 (98):1-29.Wright, Erik Olin.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Wright, Erik Olin.1996.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ClassAnalysis." Theory and Society 25:697-716.Wright, Erik Olin.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Wright, Erik Olin.2002. “The Shadow ofExploitation in Weber’s Class Analysis”.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6).赖特. 2004.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Wright, ErikOlin. 2004.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lass Analysis.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赖特. 2006. 阶级[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Wright, Erik Olin. 2006.Classe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郑杭生、李路路,等. 2004.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engHangsheng, Li Lulu etc. 2004.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Urban China.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责任编辑:田青[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评价和检验对象不是单个的命题或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系列,即他所谓的“科学研究纲领”,它是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等四个部分所组成的,其中“硬核”是构成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核心部分,它是坚韧的、不许改变的和不容反驳的。参见刘放桐等编著,1990年,《现代西方哲学》,第800—808页。[2]关于阶级和国家政权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共产党宣言》第23—36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3]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西方阶级理论发生的这种转移其社会背景和环境与当代中国社会截然不同,它只是发生在西方阶级理论中的现实,而不应该成为评判中国社会和阶级理论的标准。[4]此概念见于威登和格伦斯基合写的一篇论文,其具体含义可参考下面这段话:“我们主张,这一……阶级图式的主要目的,是去识别出生产场所中的一些结构性位置,它们提供了最强烈的关于‘生活条件’的可能信号,这指的是定义了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和特征的那些‘境况’(circumstance)的全副甲胄,包括我们控制的经济流和经济资源,我们的制度性的亲密关系和承诺,我们所过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及我们的意见和态度”(Weedenand Grusky,2005a: 141-212)。
资料来源:《社会》2012年第5期 作者:李路路 陈建伟 秦广
 爱华网
爱华网